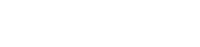次日一大早,停留于新丰的皇长子刘荣,便等来了册立诏书,以及带来诏书的宗正、奉常官员。
懵逼状态下被‘黄袍加身’——被穿上太子独有的深蓝王袍后,刘荣又如同提线木偶般,被礼官们‘操控’着,完成了一场简易版的告庙仪式。
——册立储君太子,本该在太祖刘邦的太祖庙,或者说高皇帝庙,即‘高庙’进行祭祖仪式。
且祭祖告庙以立储君,天子必须在场,太后也得尽可能在场。
刘荣滞留新丰,祭的是新丰栎阳宫的太庙——太上皇的‘太庙’,而非太祖皇帝的‘太庙’;
天子启、窦太后也都不在,只有奉常礼官、宗正吏员指挥着刘荣走流程。
这就意味着这场祭祖告庙仪式,其实并不能算作是正式的‘祭祖告庙’仪式。
等回了长安,还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、无比宏大庄严的仪式,在等着刘荣。
换句话说:新丰这场祭祖,不过是天子启的权宜之计——尽快、就近到随便一座先皇庙,完成祭祖告庙仪式,坐实刘荣储君太子的身份和既定事实!
至于之后的正式祭祖,便等朝堂仔细准备一番,再把该叫的宗亲、藩王都叫上,不用急于一时。
故而,新丰的祭祖仪式也是颇有些‘迅速’——流程能省则省,能快则快;
大概就是刘荣沐浴更衣,走进庙堂跪下身,奉上香火血食;
而后,便是奉常礼官诵读祭文,向太上皇汇报一下:陛下呀~
——您的三儿子:刘季,的四儿子:刘恒,的长子:刘启,的长子刘荣,得立为太子储君啦~
——社稷有后,宗庙有后,特意来跟您老说一声,让您老也高兴高兴~
诵读结束,便把承载祭文的布块扔进火盆里一烧,刘荣再磕几个头,就算完事儿了。
权宜之计嘛!
结束了这颇有些潦草的‘祭祖告庙’仪式,刘荣又被塞进了一辆马车的车厢之内,便径直朝着长安而去。
半日之后,车马驶入长安,于未央宫外止步。
到这时,刘荣已经能感觉到身份的转变,为自己带来的待遇变化了。
——进了长安之后,刘荣的马车,便走上了御道!
虽然那条由孝惠皇帝下令修建的御道,太后的车马能走、天子的御辇能走,寻常百姓也能在太后、天子未出行至此的时候在上面行走;
但能乘车行走在御道之上的人,截止今日清晨,普天之下只有两人。
从今天开始,才有了第三人。
待刘荣下了马车,宫门门洞下、宫墙上,平日里那些目不斜视,甚至隐隐有些倨傲的禁卫们,也都下意识挺直了腰杆。
虽然没有对刘荣见礼,又或是浮夸的单膝跪地之类,但单就是这幅‘正在被领导视察’的作态,也绝对是放眼天下,不超过三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。
在宫门外,由宦者令春陀接替了‘引领者’的角色,刘荣便跟着春陀,沿宫道向宣室殿的方向走去。
路过凤凰殿,却见殿门紧闭;
路过广明、宣明殿,亦然。
倒是绮兰殿,隐约开了一道门缝,不知是谁在门缝后偷窥。
待到了宣室殿外,那数百级长阶下的广场,昂起头,却见殿外的瞭远台内,天子启正居高临下的看向自己。
隔得太远,刘荣也看不清此刻,皇帝老爹是怎样的神态。
只下意识侧过头,看向身旁的春陀……
“陛下早有交代:这长阶,殿下得自己走上去。”
“没人领着,也没人扶着……”
意有所指的一语,只引得刘荣默然点下头。
抬起脚,一阶,一阶——刘荣爬的无比庄严。
——刘荣当然知道,皇帝老爹这是什么意思。
左右不过是想提醒刘荣:这储君之位,是你靠自己一步步爬山来的;
日后,你也得靠自己,一步步稳固自己的位置,一步步向朕——向皇位靠近。
对于封建君权,刘荣向来怀有敬畏。
故而,这几百级长阶,刘荣走的一步一顿,无比庄严。
踏上最后一阶,饶是凛冬冷冽,刘荣的额头,也已是蒙上了一层薄汗。
原以为皇帝老爹,会从瞭远台外侧的护栏前侧转过身,却发现护栏内,不知何时多出了两只摇椅。
天子启也早已在其中一只摇椅上躺下身,优哉游哉的轻晃着摇椅,双眼也微微闭起,手掌在大腿上规律的轻拍着。
“坐。”
待刘荣走上前,天子启只淡然吐出一字,身形却没有丝毫挪动。
仍躺在摇椅上,仍闭着双眼,仍在大腿上规律的拍打着不知名的节奏。
老爹有了指令,刘荣自也只得乖乖上前,半边屁股在摇椅外侧落下,双手扶于膝上——愣是在摇椅上,坐出了‘正襟危坐’的架势;
眼角稍睁开一道缝,见刘荣如此作态,天子启却是摇头一笑,将身子稍坐起来些,接过春陀递来的茶碗,小口小口嘬了起来。
“为了公子的储君太子之位,朕,可是差点血洗长安呐?”
“——至少是险些屠尽窦氏满门。”
垂眸看着手中茶碗,轻轻吹撒茶面上的药渣,天子启语调随和的道出一语;
轻嘬一口茶汤,将茶碗捧回腹前,又悠悠发出一声长叹。
“总算是遂了愿,做了我汉家的太子储君~”
“就没什么想说的?”
嘴上说着,天子启也不忘斜眼撇刘荣一眼,旋即便再度眺望向正前方。
瞭远台外,近处是未央宫内的殿室、楼阙,以及将宫内宫外分割开的宫墙、宫门;
宫墙之外,是不见几道人影的街道、为冰雪所覆盖的民居,以及追逐于街头巷尾的孩童、鸡鸭。
天空中艳阳高照,总算是为这凛冬,带来了些许温暖;
但刘荣此刻,却并没有感觉到照在身上的阳光,为自己带来了丝毫暖意。
——宣室正殿,宛若耸立云端,俯瞰着整座长安城。
坐在宣室正殿外侧的瞭远台,感受着冷冽的寒风,刘荣,只觉高处不胜寒……
“父皇要立太子储君,主要还是为了绝梁王叔的念头。”
沉默了许久,刘荣才终于开口,道出了自己近几个月以来,在未央宫内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同时,也是成为太子储君之后,对天子启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便见天子启闻言,目光仍撒向瞭远台外的远方,只轻轻一翘嘴角。
手中茶碗被送到嘴边,下意识吹吹,又再小嘬一口。
“还有呢?”
听不出悲喜的一问,却惹得刘荣满是别扭的调整起身形,终还是不再挣扎,索性从躺椅上起了身。
走到天子启侧后方一步的位置,双手环抱于腹前,稍弯着腰,语调平稳道:“立了储君太子——尤其还是循惯例、遵祖制立了长,让梁王叔绝了储君太弟的念头,父皇针对吴楚之乱的谋算,才能算是彻底收尾。”
“之后,才是考察儿这个太子储君,究竟能否承担起宗庙、社稷之重。”
“——若儿能,便当真以儿为储;”
“若儿不能,则等梁王叔彻底绝了念头,再也不想,更再也不可能成为储君太弟,父皇亦可易储另立。”
···
“废了儿的储位,父皇仅剩的选择,是小十。”
“所以从今天开始,小十的性命安危,便落在了儿的头上。”
“一旦小十有个三长两短,父皇根本不需要寻找任何证据——闭着眼睛,治儿一个‘残害兄弟手足’的罪,便大抵不会出错。”
“自然,在考察儿能否承宗庙、社稷之重的同时,父皇也会顺带培养小十,以备不测……”
分明是每一句都不该明说的话,刘荣却一股脑尽数道出,天子启也不由得一阵摇头失笑。
仍眺望向前方,手指却伸向刘荣连连虚点,天子启才终是双手撑着摇椅扶手,彻底坐起了身。
将后腰从椅背上抬起,将右手手肘撑在摇椅扶手上,右手虚握成拳撑起下巴;
侧身看向刘荣,似笑非笑的眯起眼角:“为何就这般笃定?”
“——朕为何就不能是真的想要立皇长子,做我汉家的储君太子?”
“要知道废太子,可是会让朝野震荡,乃至宗庙、社稷不稳的啊……”
“此番,为了立公子为储君,朕更是冒着两宫不合,甚至是东宫震荡的风险。”
···
“冒了这么大的风险,却只是以‘立皇长子为储君’为权宜之计,为的,只是绝梁王不轨之念;”
“与此同时,又打着‘实在不行就易储另立’的打算?”
“朕,为何要这么做呢?”
虽是在‘问’,但天子启语调中的玩味和戏谑,却分明是在说:你怎么知道的?
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?
刘荣回答的很干脆:“换做是儿,儿便会这么做。”
“——梁王叔觊觎神圣,说是‘心怀不轨’,也没人能挑出错来。”
“而梁王叔与父皇情同手足,又有皇祖母在东宫盯着,父皇唯一的办法,就是尽快立储。”
“在这个前提下,皇长子合不合格,对父皇而言并不重要。”
“哪怕不合格——甚至哪怕身有残缺,父皇都必须册立皇长子,以此告诉梁王叔:父死子继、立嫡立长,是不可更改的祖制!”
···
“等梁王叔这档子事儿过了,父皇再酌情应对:是授皇长子以帝王之道,还是易储另立——对父皇而言,都并非什么难事。”
“毕竟父皇方才也说了:为了册立儿为储君,父皇,可是险些血洗长安。”
“——为了立储,父皇尚且险些血洗长安,乃至屠尽当朝皇太后满门、肃清窦氏党羽;”
“日后为了易储,再屠一门栗氏外戚,肃清太子党羽,为小十扫除障碍——对父皇而言,也不过是便宜之内罢……”
神情淡然,语调平和的一番话,惹得天子启又是一阵含笑摇头。
又悠然呼出一口气,方面带轻松道:“公子,比朕聪明许多~”
“——至少,比当年的‘太子启’聪明许多……”
···
“想当年,先帝也会时不时,以朝政、社稷之事考校于朕;”
“考校十回,朕却只能答对三两回——还大都是误打误撞蒙对的。”
“答错了,先帝动辄斥责、喝骂,说朕德不配位,还不如早日把储位让出来,免得让先帝在天下人面前蒙羞。”
“——便是答对了,先帝也会追问一句:此话怎讲?”
“朕答不上来,免不得又是被斥骂一通……”
似是自嘲,又莫名带着些追忆的一番话道出口,天子启只含笑望向远方,沉默了许久。
久到刘荣都有些站不住,轻轻将衣襟紧了紧,天子启才深吸一口气,从思绪中回过神来。
抬起小臂,对身后的宦者令春陀轻轻摆手,便再度招呼刘荣在身旁的的摇椅上坐下身。
待刘荣乖乖坐下,又被春陀取来的薄被盖住下半身,天子启才披着另一张薄被,侧身正对向刘荣。
面上神情虽仍是云淡风轻,但语句中,却莫名带上了一股肃然。
“朕,不知道合格的太子储君,应该是什么样的。”
“——朕亲眼见过的唯一一个太子储君,是朕自己。”
“先帝说,朕这个太子并不合格;”
“但朕却做了二十一年太子,最终又做了天子。”
“这天子,朕自认为做的不错。”
“所以,朕唯一能确定的是:朕这样的太子储君,是合格的——至少是勉强合格的。”
莫名严肃的道出一语,天子启面色不由再一正,朝刘荣微一昂头。
“公子这样的太子储君,对宗庙、社稷而言究竟是福是祸,朕不清楚。”
“——一个思绪活泛,机智过人,又友爱手足、恭顺母亲的太子,朕不知道这样的储君,日后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天子。”
“所以,公子方才的话,对,也不对。”
···
“立皇长子为太子储君,确实是朕出于‘绝梁王之念’的目的所为。”
“但考察公子是否合格,朕却并没有具体的标准。”
“——无论是公子还是小十,朕都无法确定孰是孰非、孰优孰劣。”
“朕能遵照的,只有自己的判断。”
许是和刘荣摊了牌,又或许是一桩心事落了地,让天子启肩上的胆子轻了不少;
说起这番话,天子启侃侃而谈,眉宇虽还算严肃,却也无时不刻带着轻松。
刘荣听的很认真。
天子启,却说的更认真。
“在朕看来,公子的优势、劣势,都很明显。”
“年壮即冠,为朕诸子之长,手腕老练,天资卓绝——这都是优势。”
“母栗姬,则是劣势。”
“——甚至可以说,是公子唯一的劣势。”
···
“朕的母亲,还算是个不错——至少是个不太差的太后,尚且能逼得朕为了册立太子储君,粗暴的将北军开入长安。”
“只差那么一点,朕便险些要成为一个暴君,甚至险些蒙上一个‘囚母’的骂名。”
“朕的母亲尚且如此,朕实在想象不到公子的母亲,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太后;”
“又会为我汉家,带来怎样的动荡和灾难。”
“——如果公子年幼丧母,甚至没有母亲、母族作为助力,朕都可能不会考虑小十,只全心培养公子。”
“但公子的母亲,实在是让朕很难对公子放心。”
对于天子启如此坦诚的说出‘你不错,但你妈忒不靠谱’,刘荣惊诧之余,却也莫名感到一阵心安。
别说是汉家的帝王——便是后世的老师,也是一样的道理:愿意说你,说明你还有救;
愿意批评伱,说明你还有希望去改正。
更何况这些话,是天子启前脚刚为刘荣‘抢’来了储君太子之位,后脚便说出口的。
这其中,有几分提点、几分敲打,刘荣,自也了然于胸。
“小十对朕而言,也是万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。”
“除非公子实在不争气,让朕实在无法放心,从而不得不狠心废储另立;”
“否则,朕便不会将我汉家的未来,寄于小十身上。”
正思虑间,天子启笃定的话语再度传入耳中,惹得刘荣再度侧过头。
便见天子启道出此语,又沉沉一点头,面上严肃之色,也随之带上了些许惆怅。
“朕,已经老了……”
“小十,却太过年幼。”
“若果真立了小十,那我汉家日后,必定难逃主少国疑,君权旁落。”
“——朕在,东宫即便偶有不稳,也翻不出什么大浪。”
“但待朕去见了先帝,留一个年不及冠的小十,坐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,那无论小十日后天资、手腕如何,都绝不可能压得住东宫太后。”
“若朕走的急了些,小十要面对的,甚至可能不止一个太后——而是会再多出个太皇太后!”
“这对一个年不及冠的‘儿皇帝’而言,几乎不亚于让一个还没断奶的婴孩,同一头猛虎搏斗……”
言罢,天子启便莫名呆坐在了原地,似是为自己刚说出的这番话,而感到些许愕然。
——刘荣很好,可惜有个叫‘栗姬’的母亲;
而除刘荣外,唯一可供天子启选择的后备人选,是年仅三岁的皇十子刘彘……
“朕很希望公子,能撑到朕合眼的那一天。”
“——很希望朕宫车晏驾时,我汉家的储君太子,是今日册立的皇长子荣,而非日后易储另立的皇十子彘。”
冷不丁到处一语,天子启已是皱起了眉头,望向瞭远台外,神情说不清的凝重。
“但希望归希望,对朕而言最重要的,仍旧是宗庙、社稷的未来。”
“如果公子无法证明自己,能压制自己的母亲——能保证自己的母亲,不会在日后颠覆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……”
“那朕,即便再怎般不愿,也只能咬牙硬撑几年,好让小十再年壮些、再年长些。”
“至于公子,既是做过太子、坐过储君之外,待日后小十得立,便也就断没有苟活的可能。”
“这些,公子都明白?”
言罢,天子启便满带着郑重,望向身侧,已经穿上太子冠服的刘荣。
却见刘荣闻言,只深吸一口气,旋即带着自信的淡笑,对天子启一拱手。
“父皇方才,唤儿什么?”
“——嗯?”
“——公子?”
“请父皇,称太子……”
···
“儿臣,已得东宫太后册封,亦已于新丰太庙祭祖。”
“请父皇,称太子…………”
懵逼状态下被‘黄袍加身’——被穿上太子独有的深蓝王袍后,刘荣又如同提线木偶般,被礼官们‘操控’着,完成了一场简易版的告庙仪式。
——册立储君太子,本该在太祖刘邦的太祖庙,或者说高皇帝庙,即‘高庙’进行祭祖仪式。
且祭祖告庙以立储君,天子必须在场,太后也得尽可能在场。
刘荣滞留新丰,祭的是新丰栎阳宫的太庙——太上皇的‘太庙’,而非太祖皇帝的‘太庙’;
天子启、窦太后也都不在,只有奉常礼官、宗正吏员指挥着刘荣走流程。
这就意味着这场祭祖告庙仪式,其实并不能算作是正式的‘祭祖告庙’仪式。
等回了长安,还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、无比宏大庄严的仪式,在等着刘荣。
换句话说:新丰这场祭祖,不过是天子启的权宜之计——尽快、就近到随便一座先皇庙,完成祭祖告庙仪式,坐实刘荣储君太子的身份和既定事实!
至于之后的正式祭祖,便等朝堂仔细准备一番,再把该叫的宗亲、藩王都叫上,不用急于一时。
故而,新丰的祭祖仪式也是颇有些‘迅速’——流程能省则省,能快则快;
大概就是刘荣沐浴更衣,走进庙堂跪下身,奉上香火血食;
而后,便是奉常礼官诵读祭文,向太上皇汇报一下:陛下呀~
——您的三儿子:刘季,的四儿子:刘恒,的长子:刘启,的长子刘荣,得立为太子储君啦~
——社稷有后,宗庙有后,特意来跟您老说一声,让您老也高兴高兴~
诵读结束,便把承载祭文的布块扔进火盆里一烧,刘荣再磕几个头,就算完事儿了。
权宜之计嘛!
结束了这颇有些潦草的‘祭祖告庙’仪式,刘荣又被塞进了一辆马车的车厢之内,便径直朝着长安而去。
半日之后,车马驶入长安,于未央宫外止步。
到这时,刘荣已经能感觉到身份的转变,为自己带来的待遇变化了。
——进了长安之后,刘荣的马车,便走上了御道!
虽然那条由孝惠皇帝下令修建的御道,太后的车马能走、天子的御辇能走,寻常百姓也能在太后、天子未出行至此的时候在上面行走;
但能乘车行走在御道之上的人,截止今日清晨,普天之下只有两人。
从今天开始,才有了第三人。
待刘荣下了马车,宫门门洞下、宫墙上,平日里那些目不斜视,甚至隐隐有些倨傲的禁卫们,也都下意识挺直了腰杆。
虽然没有对刘荣见礼,又或是浮夸的单膝跪地之类,但单就是这幅‘正在被领导视察’的作态,也绝对是放眼天下,不超过三个人能享受到的待遇。
在宫门外,由宦者令春陀接替了‘引领者’的角色,刘荣便跟着春陀,沿宫道向宣室殿的方向走去。
路过凤凰殿,却见殿门紧闭;
路过广明、宣明殿,亦然。
倒是绮兰殿,隐约开了一道门缝,不知是谁在门缝后偷窥。
待到了宣室殿外,那数百级长阶下的广场,昂起头,却见殿外的瞭远台内,天子启正居高临下的看向自己。
隔得太远,刘荣也看不清此刻,皇帝老爹是怎样的神态。
只下意识侧过头,看向身旁的春陀……
“陛下早有交代:这长阶,殿下得自己走上去。”
“没人领着,也没人扶着……”
意有所指的一语,只引得刘荣默然点下头。
抬起脚,一阶,一阶——刘荣爬的无比庄严。
——刘荣当然知道,皇帝老爹这是什么意思。
左右不过是想提醒刘荣:这储君之位,是你靠自己一步步爬山来的;
日后,你也得靠自己,一步步稳固自己的位置,一步步向朕——向皇位靠近。
对于封建君权,刘荣向来怀有敬畏。
故而,这几百级长阶,刘荣走的一步一顿,无比庄严。
踏上最后一阶,饶是凛冬冷冽,刘荣的额头,也已是蒙上了一层薄汗。
原以为皇帝老爹,会从瞭远台外侧的护栏前侧转过身,却发现护栏内,不知何时多出了两只摇椅。
天子启也早已在其中一只摇椅上躺下身,优哉游哉的轻晃着摇椅,双眼也微微闭起,手掌在大腿上规律的轻拍着。
“坐。”
待刘荣走上前,天子启只淡然吐出一字,身形却没有丝毫挪动。
仍躺在摇椅上,仍闭着双眼,仍在大腿上规律的拍打着不知名的节奏。
老爹有了指令,刘荣自也只得乖乖上前,半边屁股在摇椅外侧落下,双手扶于膝上——愣是在摇椅上,坐出了‘正襟危坐’的架势;
眼角稍睁开一道缝,见刘荣如此作态,天子启却是摇头一笑,将身子稍坐起来些,接过春陀递来的茶碗,小口小口嘬了起来。
“为了公子的储君太子之位,朕,可是差点血洗长安呐?”
“——至少是险些屠尽窦氏满门。”
垂眸看着手中茶碗,轻轻吹撒茶面上的药渣,天子启语调随和的道出一语;
轻嘬一口茶汤,将茶碗捧回腹前,又悠悠发出一声长叹。
“总算是遂了愿,做了我汉家的太子储君~”
“就没什么想说的?”
嘴上说着,天子启也不忘斜眼撇刘荣一眼,旋即便再度眺望向正前方。
瞭远台外,近处是未央宫内的殿室、楼阙,以及将宫内宫外分割开的宫墙、宫门;
宫墙之外,是不见几道人影的街道、为冰雪所覆盖的民居,以及追逐于街头巷尾的孩童、鸡鸭。
天空中艳阳高照,总算是为这凛冬,带来了些许温暖;
但刘荣此刻,却并没有感觉到照在身上的阳光,为自己带来了丝毫暖意。
——宣室正殿,宛若耸立云端,俯瞰着整座长安城。
坐在宣室正殿外侧的瞭远台,感受着冷冽的寒风,刘荣,只觉高处不胜寒……
“父皇要立太子储君,主要还是为了绝梁王叔的念头。”
沉默了许久,刘荣才终于开口,道出了自己近几个月以来,在未央宫内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同时,也是成为太子储君之后,对天子启所说的第一句话。
便见天子启闻言,目光仍撒向瞭远台外的远方,只轻轻一翘嘴角。
手中茶碗被送到嘴边,下意识吹吹,又再小嘬一口。
“还有呢?”
听不出悲喜的一问,却惹得刘荣满是别扭的调整起身形,终还是不再挣扎,索性从躺椅上起了身。
走到天子启侧后方一步的位置,双手环抱于腹前,稍弯着腰,语调平稳道:“立了储君太子——尤其还是循惯例、遵祖制立了长,让梁王叔绝了储君太弟的念头,父皇针对吴楚之乱的谋算,才能算是彻底收尾。”
“之后,才是考察儿这个太子储君,究竟能否承担起宗庙、社稷之重。”
“——若儿能,便当真以儿为储;”
“若儿不能,则等梁王叔彻底绝了念头,再也不想,更再也不可能成为储君太弟,父皇亦可易储另立。”
···
“废了儿的储位,父皇仅剩的选择,是小十。”
“所以从今天开始,小十的性命安危,便落在了儿的头上。”
“一旦小十有个三长两短,父皇根本不需要寻找任何证据——闭着眼睛,治儿一个‘残害兄弟手足’的罪,便大抵不会出错。”
“自然,在考察儿能否承宗庙、社稷之重的同时,父皇也会顺带培养小十,以备不测……”
分明是每一句都不该明说的话,刘荣却一股脑尽数道出,天子启也不由得一阵摇头失笑。
仍眺望向前方,手指却伸向刘荣连连虚点,天子启才终是双手撑着摇椅扶手,彻底坐起了身。
将后腰从椅背上抬起,将右手手肘撑在摇椅扶手上,右手虚握成拳撑起下巴;
侧身看向刘荣,似笑非笑的眯起眼角:“为何就这般笃定?”
“——朕为何就不能是真的想要立皇长子,做我汉家的储君太子?”
“要知道废太子,可是会让朝野震荡,乃至宗庙、社稷不稳的啊……”
“此番,为了立公子为储君,朕更是冒着两宫不合,甚至是东宫震荡的风险。”
···
“冒了这么大的风险,却只是以‘立皇长子为储君’为权宜之计,为的,只是绝梁王不轨之念;”
“与此同时,又打着‘实在不行就易储另立’的打算?”
“朕,为何要这么做呢?”
虽是在‘问’,但天子启语调中的玩味和戏谑,却分明是在说:你怎么知道的?
你怎么知道我是这么想的?
刘荣回答的很干脆:“换做是儿,儿便会这么做。”
“——梁王叔觊觎神圣,说是‘心怀不轨’,也没人能挑出错来。”
“而梁王叔与父皇情同手足,又有皇祖母在东宫盯着,父皇唯一的办法,就是尽快立储。”
“在这个前提下,皇长子合不合格,对父皇而言并不重要。”
“哪怕不合格——甚至哪怕身有残缺,父皇都必须册立皇长子,以此告诉梁王叔:父死子继、立嫡立长,是不可更改的祖制!”
···
“等梁王叔这档子事儿过了,父皇再酌情应对:是授皇长子以帝王之道,还是易储另立——对父皇而言,都并非什么难事。”
“毕竟父皇方才也说了:为了册立儿为储君,父皇,可是险些血洗长安。”
“——为了立储,父皇尚且险些血洗长安,乃至屠尽当朝皇太后满门、肃清窦氏党羽;”
“日后为了易储,再屠一门栗氏外戚,肃清太子党羽,为小十扫除障碍——对父皇而言,也不过是便宜之内罢……”
神情淡然,语调平和的一番话,惹得天子启又是一阵含笑摇头。
又悠然呼出一口气,方面带轻松道:“公子,比朕聪明许多~”
“——至少,比当年的‘太子启’聪明许多……”
···
“想当年,先帝也会时不时,以朝政、社稷之事考校于朕;”
“考校十回,朕却只能答对三两回——还大都是误打误撞蒙对的。”
“答错了,先帝动辄斥责、喝骂,说朕德不配位,还不如早日把储位让出来,免得让先帝在天下人面前蒙羞。”
“——便是答对了,先帝也会追问一句:此话怎讲?”
“朕答不上来,免不得又是被斥骂一通……”
似是自嘲,又莫名带着些追忆的一番话道出口,天子启只含笑望向远方,沉默了许久。
久到刘荣都有些站不住,轻轻将衣襟紧了紧,天子启才深吸一口气,从思绪中回过神来。
抬起小臂,对身后的宦者令春陀轻轻摆手,便再度招呼刘荣在身旁的的摇椅上坐下身。
待刘荣乖乖坐下,又被春陀取来的薄被盖住下半身,天子启才披着另一张薄被,侧身正对向刘荣。
面上神情虽仍是云淡风轻,但语句中,却莫名带上了一股肃然。
“朕,不知道合格的太子储君,应该是什么样的。”
“——朕亲眼见过的唯一一个太子储君,是朕自己。”
“先帝说,朕这个太子并不合格;”
“但朕却做了二十一年太子,最终又做了天子。”
“这天子,朕自认为做的不错。”
“所以,朕唯一能确定的是:朕这样的太子储君,是合格的——至少是勉强合格的。”
莫名严肃的道出一语,天子启面色不由再一正,朝刘荣微一昂头。
“公子这样的太子储君,对宗庙、社稷而言究竟是福是祸,朕不清楚。”
“——一个思绪活泛,机智过人,又友爱手足、恭顺母亲的太子,朕不知道这样的储君,日后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天子。”
“所以,公子方才的话,对,也不对。”
···
“立皇长子为太子储君,确实是朕出于‘绝梁王之念’的目的所为。”
“但考察公子是否合格,朕却并没有具体的标准。”
“——无论是公子还是小十,朕都无法确定孰是孰非、孰优孰劣。”
“朕能遵照的,只有自己的判断。”
许是和刘荣摊了牌,又或许是一桩心事落了地,让天子启肩上的胆子轻了不少;
说起这番话,天子启侃侃而谈,眉宇虽还算严肃,却也无时不刻带着轻松。
刘荣听的很认真。
天子启,却说的更认真。
“在朕看来,公子的优势、劣势,都很明显。”
“年壮即冠,为朕诸子之长,手腕老练,天资卓绝——这都是优势。”
“母栗姬,则是劣势。”
“——甚至可以说,是公子唯一的劣势。”
···
“朕的母亲,还算是个不错——至少是个不太差的太后,尚且能逼得朕为了册立太子储君,粗暴的将北军开入长安。”
“只差那么一点,朕便险些要成为一个暴君,甚至险些蒙上一个‘囚母’的骂名。”
“朕的母亲尚且如此,朕实在想象不到公子的母亲,会成为一个怎样的太后;”
“又会为我汉家,带来怎样的动荡和灾难。”
“——如果公子年幼丧母,甚至没有母亲、母族作为助力,朕都可能不会考虑小十,只全心培养公子。”
“但公子的母亲,实在是让朕很难对公子放心。”
对于天子启如此坦诚的说出‘你不错,但你妈忒不靠谱’,刘荣惊诧之余,却也莫名感到一阵心安。
别说是汉家的帝王——便是后世的老师,也是一样的道理:愿意说你,说明你还有救;
愿意批评伱,说明你还有希望去改正。
更何况这些话,是天子启前脚刚为刘荣‘抢’来了储君太子之位,后脚便说出口的。
这其中,有几分提点、几分敲打,刘荣,自也了然于胸。
“小十对朕而言,也是万不得已之下的权宜之计。”
“除非公子实在不争气,让朕实在无法放心,从而不得不狠心废储另立;”
“否则,朕便不会将我汉家的未来,寄于小十身上。”
正思虑间,天子启笃定的话语再度传入耳中,惹得刘荣再度侧过头。
便见天子启道出此语,又沉沉一点头,面上严肃之色,也随之带上了些许惆怅。
“朕,已经老了……”
“小十,却太过年幼。”
“若果真立了小十,那我汉家日后,必定难逃主少国疑,君权旁落。”
“——朕在,东宫即便偶有不稳,也翻不出什么大浪。”
“但待朕去见了先帝,留一个年不及冠的小十,坐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,那无论小十日后天资、手腕如何,都绝不可能压得住东宫太后。”
“若朕走的急了些,小十要面对的,甚至可能不止一个太后——而是会再多出个太皇太后!”
“这对一个年不及冠的‘儿皇帝’而言,几乎不亚于让一个还没断奶的婴孩,同一头猛虎搏斗……”
言罢,天子启便莫名呆坐在了原地,似是为自己刚说出的这番话,而感到些许愕然。
——刘荣很好,可惜有个叫‘栗姬’的母亲;
而除刘荣外,唯一可供天子启选择的后备人选,是年仅三岁的皇十子刘彘……
“朕很希望公子,能撑到朕合眼的那一天。”
“——很希望朕宫车晏驾时,我汉家的储君太子,是今日册立的皇长子荣,而非日后易储另立的皇十子彘。”
冷不丁到处一语,天子启已是皱起了眉头,望向瞭远台外,神情说不清的凝重。
“但希望归希望,对朕而言最重要的,仍旧是宗庙、社稷的未来。”
“如果公子无法证明自己,能压制自己的母亲——能保证自己的母亲,不会在日后颠覆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……”
“那朕,即便再怎般不愿,也只能咬牙硬撑几年,好让小十再年壮些、再年长些。”
“至于公子,既是做过太子、坐过储君之外,待日后小十得立,便也就断没有苟活的可能。”
“这些,公子都明白?”
言罢,天子启便满带着郑重,望向身侧,已经穿上太子冠服的刘荣。
却见刘荣闻言,只深吸一口气,旋即带着自信的淡笑,对天子启一拱手。
“父皇方才,唤儿什么?”
“——嗯?”
“——公子?”
“请父皇,称太子……”
···
“儿臣,已得东宫太后册封,亦已于新丰太庙祭祖。”
“请父皇,称太子……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