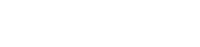儿子,不是太子。
太子,不是儿子。
那个不是太子的儿子,自然是先皇嫡次子:梁王刘武;
至于那‘不是儿子’的太子,自然是先皇嫡长子,汉家如今的皇帝:天子启……
“儿做太子那些年,当真是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”
“——才刚做了几年太子,便冒出来个慎夫人、阿揖母子,愣是惹得母后气急败坏、搞得儿阵脚大乱。”
“总归是阿揖鲁莽,策马疾驰出了事,儿这如无根之萍般的储位,才总算是堪堪坐稳。”
“却也还是难免被先帝斥责、唾骂,更时不时以‘易储另立’之说恐吓……”
···
“母亲还记得当年,梁怀王死后,母亲说了什么吗?”
说着,天子启便笑着低下头,呆愣片刻,索性便在御阶最上方的那一阶上,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原本背负于身后的双手,也被天子启收回身前,左手以掌扶膝,右手以肘撑在腿上,手掌时不时从面前擦过,却是不知在擦些什么。
原本讥讽、清冷的语调,更不知何时,已带上了些许哽咽。
“母亲说:做得好!”
“一定要把手尾收拾干净!”
“而后,母后便背着儿,让阿姊将阿武接去了宫外。”
“——之后不数月,阿武便封王就藩;”
“也是从那以后,儿派去梁国——派去睢阳的每一个人身后,都会多出好几个采风御史随行。”
“便是阿武染了风寒、害了病疾,母后第一个想到的,都是儿这个储君太子……”
天子启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才强压下了语调的起伏,才没让那哽咽,太过清楚地传到母亲耳中。
但在那张被藏在手掌之下的面庞之上,天子启除了嘴角挂着自嘲的笑意,余下的每一寸皮肤,都在诠释何谓‘涕泗横流’。
“在母亲眼里,儿,从来都不是母亲的儿子。”
“——甚至都不是个人?”
“就好像儿生来,就是为了做储君、做皇帝而生;”
“在儿眼里,就好似从不曾有父母双亲、宗亲长辈,更不曾有手足姊弟、血脉之亲。”
“就好似儿,从不需要一个慈爱的父亲、一个怜爱的母亲……”
说到此处,天子启终是再也压不下汹涌而上的泪水,只将双手手肘撑在推上,双手捂在脸前,默默坐在御阶上方流起了泪。
诚然:皇帝的快乐、权柄的滋味,没做过皇帝的人,是想象不到的。
但与之对应的,是同样令人无法想象,甚至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压力,和心力憔悴。
——尤其天子启,更是在先帝那样的‘明君雄主’的注视下,做了足足二十多年的太子储君;
那二十多年有多苦、有多累,只有天子启知道。
对于长子刘荣,天子启虽是一口一个‘荣公子’‘那混账’,但细算起来,还真没怎么苛待。
无论是刘荣偶尔的逾矩,或是三不五时闹出来的热闹,天子启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给予了最大的包容。
这不是因为天子启,是一个心胸多么宽广的君王;
更不是因为皇长子刘荣,就真那般得天子启宠爱。
天子启,仅仅只是自己淋过雨,才本能的想要为雨幕下的儿子刘荣,撑起一把伞。
仅仅只是天子启吃过那电闪雷鸣、大雨倾盆而下的苦,才想要挽弓搭箭,将那雷公电母,乃至兴风布雨的龙王,从九霄之上射下来!
相较于太祖高皇帝、先太宗皇帝,天子启都算不上多么‘贤明’;
顶天了去,也就是比英年早逝的孝惠皇帝好一些。
但天子启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。
知道别人一眼就能看懂的东西,天子启暗下熬个几晚,也终归是能看懂;
旁人一想就能明白,甚至举一反三的东西,天子启反复琢磨几天,也总能想透彻、想清楚。
如此多年,即便天资再怎么‘平庸’,天子启也总算是厚积薄发,走到了今天。
只是天子启再怎么‘年壮’,再怎么‘刻薄寡恩’,甚至冰冷无情的不像是个碳基生物,但天子启,也终究是个肉体凡胎的人。
天子启,不是不食五谷杂粮,也不是没有七情六欲;
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,都将那本能的欲望、情感,皆埋藏于内心深处而已……
“父皇驾崩,儿即皇帝位,要做的第一件事,是削藩。”
“——于私,是要诛灭刘濞那老贼,于公,是为宗庙、社稷,铲除宗亲诸侯尾大不掉的祸患。”
“母亲,是怎么做的呢?”
“我汉家的太后,是怎么做的呢?”
默然垂泪许久,天子启才终于从那无尽的苦楚、哀戚中调整好情绪,语带沙哑的发出一问。
不出意外的,没有等来母亲窦太后的应答,天子启便自顾自往下说道:“为了让母亲支持晁错的《削藩策》,儿答应母亲,将母亲的‘老友’袁盎再度召入朝中,任命为中大夫。”
“为了让母亲,在必要的时候压一下丞相申屠嘉,儿更是下令少府:凡是馆陶公主亲自前去,少府内帑除军械之外的一应财赀,皆任其取用。”
“——很划算。”
“这笔买卖,对我汉家的皇帝而言,真的很划算。”
“但儿,是真的想不通啊?”
“想不通我汉家的太后,为何不是儿这个皇帝的母亲?”
“儿子寻求母亲的帮助,为何还要像做生意一样,给出相应的好处、酬劳?”
说到此处,蹲坐在御阶上方的天子启便转过身;
发现自己和母亲窦太后之间,还当着一方御案,天子启更是撑地而起,满是疑惑的望向御案对侧。
只面上,泪迹未干……
“既然答应了母亲,儿便当真将袁盎,重新召回了朝中;”
“——母亲对《削藩策》的支持呢?”
“不过是噤口不言,默许而已。”
···
“同样答应了母后,儿便也就放任阿姊,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,从少府搬走了数以万万计的钱货;”
“长安坊间人尽皆知:过去这两年,馆陶长公主从少府内帑搬走的物什,足以塞满百八十个堂邑侯府!”
“——申屠嘉反对《削藩策》时,母亲对申屠嘉的压制呢?”
“依旧是噤口不言,坐视而已。”
···
“莫说这生意,是儿在和自己的母亲做——便是和外人做这笔生意,儿,也不至于吃这么大亏啊?”
“便说儿不是汉家的天子,而只是个粗鄙商户,儿也不至于蠢到做这么一笔赔本买卖??”
“哪怕是个妇人、是个稚童,儿吃了这么大亏,也总不该打碎牙齿和血吞,连一个说法都不去要???”
·
静。
极致的宁静。
随着天子启话音落下,硕大的长信殿,便陷入一阵漫长的绝对寂静之中。
御榻之上,窦太后拄杖呆坐,嘴唇几度开合,众未发一眼;
御案外侧,天子启面挂泪痕,目光灼灼,言辞说不尽的恳切。
母子二人之间的御案之上,空无一物。
——原本,是空无一物的……
“母亲,实在是太欺负人了……”
等了不知多久,都终究没能等到母亲的应答,天子启,终还是悠然一声长叹;
而后低下头,满是惆怅的含泪带笑,将腰间,那枚以和氏璧纂刻而成的传国玉玺徐徐解下。
单手拿起,愣愣的看了片刻,旋即便讥笑一声,将那方印轻轻丢到了御案之上。
“母亲要的,不就是这个吗?”
“——母亲想从儿手里讨来,转赠给阿武的,不就是这块破玉,和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吗?”
“儿,给就是了。”
“母亲也不用再拐弯抹角,说什么‘皇帝百年之后’了;”
“出了长乐,儿这便去告庙祭祖,诏行天下,以退位禅让。”
“待阿武位即九五,儿便带着未央宫的姬妾、儿女,直接去阳陵便是……”
阳陵,是天子启继位当年,便正式开始动工的皇陵。
拜太祖高皇帝所赐:汉家的皇帝,都会从自己继位之后不久,便开始兴建属于自己的皇陵。
从继位开始修,一直修到驾崩的那一天。皇陵修的越久、越大,陵邑便也会修的越久、越大;
陵邑修的越大,能迁来陵邑的关东豪强、地头蛇就越多,关东就越安稳,宗庙、社稷,便也越稳固。
在坊间,这被称之为:陵邑之制;
而对于长安朝堂而言,陵邑之制,是与农、孝并列的‘刘汉三大国本’之一:陵。
天子启话说的很直白。
——既然想让梁王留在长安,母亲也别说什么太弟不太弟的了;
——直接就让阿武做了这鸟位,儿也好趁着还没断气儿,带着妻儿往阳陵一埋,也免得日后,连自己的皇陵都进不去……
“阿武……”
“阿武会死的~”
终于,窦太后总算是从漫长的呆愣中回过神。
开口第一句话道出口,便也随之潸然泪下,却不知哭的是哪个儿子。
“生了觊觎储位的心思,又没能做储君——阿武,是会死的啊……”
“将来的储君太子,是不可能放过阿武的啊……”
哀泣着道出此语,窦太后涣散的目光,终是缓缓上抬向天子启上半身的方向。
只片刻之后,窦太后哀痛不能自已的面庞之上,便随之涌现出阵阵惊怒。
“皇帝,是想要杀了我儿子吗?”
“——皇帝,早就想要杀我儿子了?!”
“早在答应与立梁王、与立皇太弟的时候,皇帝就打定主意,要杀我的儿子了吗!!!”
三两句话的功夫,原本还在哀哭的窦太后,便已是勃然大怒!
含怒发出这几声咆哮,又好似泄了气的皮球般,双肩一耸拉,再度哀痛欲绝的哭泣起来。
窦太后这先哀后怒,更冷不丁爆发出的咆哮,却是引得天子启面色一滞;
回味着那几声含怒而发的咆哮中,窦太后对天子启、梁王刘武兄弟二人的称呼,以及侧重点……
“皇帝……”
···
“儿子……”
···
“皇帝,要杀了我儿子?”
···
“皇帝,要杀了我儿子……”
···
“皇帝……”
···
“儿子……”
···
······
天子启愣了许久。
这一句话——这两个称呼,天子启反复呢喃了许久、咀嚼了许久。
从最开始的错愕、呆滞;
到随后的苦涩、自嘲。
再逐渐转变为凄苦、恼怒;
最终,则一点点汇集为冰冷,和决绝……
“太后的儿子,朕,不会杀的。”
毫无征兆冰冷下去的语调——甚至是从不曾有过,哪怕是对旁人,都从不曾有过的冰冷语调,只刺的窦太后心窝一痛!
惊愕的抬起头,便见御案对策,天子启那仍带着泪痕、仍红着眼眶的面庞,已尽带上了决绝;
和狠厉!
沉着脸,俯下身,将双手撑上御案边沿;
直勾勾凝视向窦太后那混浊、黯淡的双眸,一字一句道:“儿,愿意遵从母亲的心愿,将亡父留下的家业,送给老三。”
“——但朕!”
“——绝不允许先皇的基业,被太后送到梁王手中!!!”
毫无征兆的咆哮声,吓得窦太后从御榻之上嗡然起身,满是不敢置信的瞪大双眼!
而在窦太后看不清的那张脸上,只剩下独属于汉天子的威仪,以及专属于天子启的狠辣和阴戾。
咬紧牙槽,瞪着母亲看了好一会儿,天子启便稍低下头;
俯视着御案之上,那枚被自己随手丢出,横躺在案上的传国玉玺,天子启又稍一抬眸。
目光锁定在母亲且惊且怒的面容上,手却已经从案外探出,好似五指山般,重重按在了玉玺上。
“阿武,是母亲的儿子。”
“——也是我汉家的梁王!”
“吴楚兴乱,我汉家的梁王,就该血战睢阳!”
“不是为了母亲,和我这个兄长——更不是为了朕,和我汉家的太后!”
“单就是为了自己的封国、身家性命,作为先帝的子嗣,也该当死战睢阳!”
···
“母亲,是儿的母亲。”
“——也是我汉家的太后!”
“我汉家的太后,就该颁诏册立储君太子,以安宗庙社稷、天下人心!”
“若是连这都做不到,就不配做我汉家的太后!!!”
·
余音绕梁。
天子启这接连几声咆哮,不断回荡在长信殿内,也不断冲击着窦太后的心神。
便见天子启如怒狮般,双手扶案,怒目圆睁的望向对侧的母亲;
良久,方神情冷峻的直起身,顺便将那方传国玉玺收回。
眼睛片刻都不曾从母亲那写有错愕、惊怒的面庞上移开,那方天子印玺,却也是被天子启熟练无比的系回了腰间。
转过身,背对着御案,重新将双手背负于身后,昂首眺望向殿门外。
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似是自言自语道:“荣,已经到新丰了。”
“——都到新丰好几日了。”
“册立太子储君的诏书,母后,也该动笔草拟了。”
丢下这句话,天子启便阴沉着脸,昂首挺胸,拾级而下。
走到殿中央,又止步回过身,对窦太后拱手一礼。
“儿臣,告退。”
这一回,天子启没有再迟疑,抬起脚步,便径直出了长信殿。
走出殿门外好几十步,才终于再度停下脚步,目光仍平视向前方,连一个眼角都不愿给身侧,那道跪在脚边的身影。
“从吴楚叛军大营活着回来,是卿的本事。”
“——既是逃出生天,朕,便不至于容不下一个‘黔首’袁丝。”
“只是卿,恐怕并不甘心就此隐退,又不知何时,被郡县酷吏缉拿?”
···
“朕就在宫门外等着。”
“日暮时分,若还看不到卿,带着太后册立储君的诏书走出宫门……”
言罢,天子启便再度迈开脚步,不顾袁盎那跪地匍匐,瑟瑟发抖的身影,一步不停的出了长乐宫。
天子启当然没有亲自等在宫门外。
但这一日的长安城,暗流涌动。
——长安宵禁!
——两宫戒严!
——武库戒严!
尚冠里南皮侯府、章武侯府,孝里窦府;
还有朝中,那些和窦氏一族藕断丝连的官员、军中,那些同窦氏扯上关系的将官,都被北军禁卒,将府邸围了个水泄不通!
整座长安城,都在等。
等一封诏书,从长乐宫内送出。
等那一封册立储君太子的诏书,能驱散长安这扑鼻的火药味,还长安城又一片白云蓝天。
终于,袁盎的身影,出现在了缓缓打开的宫门之内。
一同出现的,是一封以锦袋装起的懿旨。
于是,北军撤出长安,长安解除宵禁,两宫、武库解除戒严。
几乎是刚被送出长乐,那封懿旨,便被天子启早就备好的使节,快马加鞭送去了新丰。
一同传出未央宫的,是天子启先后颁布,却同时送出宫门的两道诏谕。
——奉太后懿旨,册立皇长子刘荣,为储君太子!
——着奉常、宗正有司即刻启程,于新丰太庙祭祖,以安天下人心惶惶!
至此,这场名为‘谁能做储君’的豪赌,终于等来了收盘的一刻。
皇长子刘荣,众望所归。
至于那第二道诏谕,则是让长安坊间彻底归于沉寂,同时又让东宫窦太后,自此闭上了宫门,以及心门。
——梁王刘武入朝月余,眷恋不去,有违祖制!
——着梁王刘武,即刻离京就藩!
天子启雷厉风行,一切,便也就此尘埃落定……
太子,不是儿子。
那个不是太子的儿子,自然是先皇嫡次子:梁王刘武;
至于那‘不是儿子’的太子,自然是先皇嫡长子,汉家如今的皇帝:天子启……
“儿做太子那些年,当真是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”
“——才刚做了几年太子,便冒出来个慎夫人、阿揖母子,愣是惹得母后气急败坏、搞得儿阵脚大乱。”
“总归是阿揖鲁莽,策马疾驰出了事,儿这如无根之萍般的储位,才总算是堪堪坐稳。”
“却也还是难免被先帝斥责、唾骂,更时不时以‘易储另立’之说恐吓……”
···
“母亲还记得当年,梁怀王死后,母亲说了什么吗?”
说着,天子启便笑着低下头,呆愣片刻,索性便在御阶最上方的那一阶上,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原本背负于身后的双手,也被天子启收回身前,左手以掌扶膝,右手以肘撑在腿上,手掌时不时从面前擦过,却是不知在擦些什么。
原本讥讽、清冷的语调,更不知何时,已带上了些许哽咽。
“母亲说:做得好!”
“一定要把手尾收拾干净!”
“而后,母后便背着儿,让阿姊将阿武接去了宫外。”
“——之后不数月,阿武便封王就藩;”
“也是从那以后,儿派去梁国——派去睢阳的每一个人身后,都会多出好几个采风御史随行。”
“便是阿武染了风寒、害了病疾,母后第一个想到的,都是儿这个储君太子……”
天子启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,才强压下了语调的起伏,才没让那哽咽,太过清楚地传到母亲耳中。
但在那张被藏在手掌之下的面庞之上,天子启除了嘴角挂着自嘲的笑意,余下的每一寸皮肤,都在诠释何谓‘涕泗横流’。
“在母亲眼里,儿,从来都不是母亲的儿子。”
“——甚至都不是个人?”
“就好像儿生来,就是为了做储君、做皇帝而生;”
“在儿眼里,就好似从不曾有父母双亲、宗亲长辈,更不曾有手足姊弟、血脉之亲。”
“就好似儿,从不需要一个慈爱的父亲、一个怜爱的母亲……”
说到此处,天子启终是再也压不下汹涌而上的泪水,只将双手手肘撑在推上,双手捂在脸前,默默坐在御阶上方流起了泪。
诚然:皇帝的快乐、权柄的滋味,没做过皇帝的人,是想象不到的。
但与之对应的,是同样令人无法想象,甚至做梦都不敢梦到的压力,和心力憔悴。
——尤其天子启,更是在先帝那样的‘明君雄主’的注视下,做了足足二十多年的太子储君;
那二十多年有多苦、有多累,只有天子启知道。
对于长子刘荣,天子启虽是一口一个‘荣公子’‘那混账’,但细算起来,还真没怎么苛待。
无论是刘荣偶尔的逾矩,或是三不五时闹出来的热闹,天子启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给予了最大的包容。
这不是因为天子启,是一个心胸多么宽广的君王;
更不是因为皇长子刘荣,就真那般得天子启宠爱。
天子启,仅仅只是自己淋过雨,才本能的想要为雨幕下的儿子刘荣,撑起一把伞。
仅仅只是天子启吃过那电闪雷鸣、大雨倾盆而下的苦,才想要挽弓搭箭,将那雷公电母,乃至兴风布雨的龙王,从九霄之上射下来!
相较于太祖高皇帝、先太宗皇帝,天子启都算不上多么‘贤明’;
顶天了去,也就是比英年早逝的孝惠皇帝好一些。
但天子启知道笨鸟先飞的道理。
知道别人一眼就能看懂的东西,天子启暗下熬个几晚,也终归是能看懂;
旁人一想就能明白,甚至举一反三的东西,天子启反复琢磨几天,也总能想透彻、想清楚。
如此多年,即便天资再怎么‘平庸’,天子启也总算是厚积薄发,走到了今天。
只是天子启再怎么‘年壮’,再怎么‘刻薄寡恩’,甚至冰冷无情的不像是个碳基生物,但天子启,也终究是个肉体凡胎的人。
天子启,不是不食五谷杂粮,也不是没有七情六欲;
只是在绝大多数时候,都将那本能的欲望、情感,皆埋藏于内心深处而已……
“父皇驾崩,儿即皇帝位,要做的第一件事,是削藩。”
“——于私,是要诛灭刘濞那老贼,于公,是为宗庙、社稷,铲除宗亲诸侯尾大不掉的祸患。”
“母亲,是怎么做的呢?”
“我汉家的太后,是怎么做的呢?”
默然垂泪许久,天子启才终于从那无尽的苦楚、哀戚中调整好情绪,语带沙哑的发出一问。
不出意外的,没有等来母亲窦太后的应答,天子启便自顾自往下说道:“为了让母亲支持晁错的《削藩策》,儿答应母亲,将母亲的‘老友’袁盎再度召入朝中,任命为中大夫。”
“为了让母亲,在必要的时候压一下丞相申屠嘉,儿更是下令少府:凡是馆陶公主亲自前去,少府内帑除军械之外的一应财赀,皆任其取用。”
“——很划算。”
“这笔买卖,对我汉家的皇帝而言,真的很划算。”
“但儿,是真的想不通啊?”
“想不通我汉家的太后,为何不是儿这个皇帝的母亲?”
“儿子寻求母亲的帮助,为何还要像做生意一样,给出相应的好处、酬劳?”
说到此处,蹲坐在御阶上方的天子启便转过身;
发现自己和母亲窦太后之间,还当着一方御案,天子启更是撑地而起,满是疑惑的望向御案对侧。
只面上,泪迹未干……
“既然答应了母亲,儿便当真将袁盎,重新召回了朝中;”
“——母亲对《削藩策》的支持呢?”
“不过是噤口不言,默许而已。”
···
“同样答应了母后,儿便也就放任阿姊,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,从少府搬走了数以万万计的钱货;”
“长安坊间人尽皆知:过去这两年,馆陶长公主从少府内帑搬走的物什,足以塞满百八十个堂邑侯府!”
“——申屠嘉反对《削藩策》时,母亲对申屠嘉的压制呢?”
“依旧是噤口不言,坐视而已。”
···
“莫说这生意,是儿在和自己的母亲做——便是和外人做这笔生意,儿,也不至于吃这么大亏啊?”
“便说儿不是汉家的天子,而只是个粗鄙商户,儿也不至于蠢到做这么一笔赔本买卖??”
“哪怕是个妇人、是个稚童,儿吃了这么大亏,也总不该打碎牙齿和血吞,连一个说法都不去要???”
·
静。
极致的宁静。
随着天子启话音落下,硕大的长信殿,便陷入一阵漫长的绝对寂静之中。
御榻之上,窦太后拄杖呆坐,嘴唇几度开合,众未发一眼;
御案外侧,天子启面挂泪痕,目光灼灼,言辞说不尽的恳切。
母子二人之间的御案之上,空无一物。
——原本,是空无一物的……
“母亲,实在是太欺负人了……”
等了不知多久,都终究没能等到母亲的应答,天子启,终还是悠然一声长叹;
而后低下头,满是惆怅的含泪带笑,将腰间,那枚以和氏璧纂刻而成的传国玉玺徐徐解下。
单手拿起,愣愣的看了片刻,旋即便讥笑一声,将那方印轻轻丢到了御案之上。
“母亲要的,不就是这个吗?”
“——母亲想从儿手里讨来,转赠给阿武的,不就是这块破玉,和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吗?”
“儿,给就是了。”
“母亲也不用再拐弯抹角,说什么‘皇帝百年之后’了;”
“出了长乐,儿这便去告庙祭祖,诏行天下,以退位禅让。”
“待阿武位即九五,儿便带着未央宫的姬妾、儿女,直接去阳陵便是……”
阳陵,是天子启继位当年,便正式开始动工的皇陵。
拜太祖高皇帝所赐:汉家的皇帝,都会从自己继位之后不久,便开始兴建属于自己的皇陵。
从继位开始修,一直修到驾崩的那一天。皇陵修的越久、越大,陵邑便也会修的越久、越大;
陵邑修的越大,能迁来陵邑的关东豪强、地头蛇就越多,关东就越安稳,宗庙、社稷,便也越稳固。
在坊间,这被称之为:陵邑之制;
而对于长安朝堂而言,陵邑之制,是与农、孝并列的‘刘汉三大国本’之一:陵。
天子启话说的很直白。
——既然想让梁王留在长安,母亲也别说什么太弟不太弟的了;
——直接就让阿武做了这鸟位,儿也好趁着还没断气儿,带着妻儿往阳陵一埋,也免得日后,连自己的皇陵都进不去……
“阿武……”
“阿武会死的~”
终于,窦太后总算是从漫长的呆愣中回过神。
开口第一句话道出口,便也随之潸然泪下,却不知哭的是哪个儿子。
“生了觊觎储位的心思,又没能做储君——阿武,是会死的啊……”
“将来的储君太子,是不可能放过阿武的啊……”
哀泣着道出此语,窦太后涣散的目光,终是缓缓上抬向天子启上半身的方向。
只片刻之后,窦太后哀痛不能自已的面庞之上,便随之涌现出阵阵惊怒。
“皇帝,是想要杀了我儿子吗?”
“——皇帝,早就想要杀我儿子了?!”
“早在答应与立梁王、与立皇太弟的时候,皇帝就打定主意,要杀我的儿子了吗!!!”
三两句话的功夫,原本还在哀哭的窦太后,便已是勃然大怒!
含怒发出这几声咆哮,又好似泄了气的皮球般,双肩一耸拉,再度哀痛欲绝的哭泣起来。
窦太后这先哀后怒,更冷不丁爆发出的咆哮,却是引得天子启面色一滞;
回味着那几声含怒而发的咆哮中,窦太后对天子启、梁王刘武兄弟二人的称呼,以及侧重点……
“皇帝……”
···
“儿子……”
···
“皇帝,要杀了我儿子?”
···
“皇帝,要杀了我儿子……”
···
“皇帝……”
···
“儿子……”
···
······
天子启愣了许久。
这一句话——这两个称呼,天子启反复呢喃了许久、咀嚼了许久。
从最开始的错愕、呆滞;
到随后的苦涩、自嘲。
再逐渐转变为凄苦、恼怒;
最终,则一点点汇集为冰冷,和决绝……
“太后的儿子,朕,不会杀的。”
毫无征兆冰冷下去的语调——甚至是从不曾有过,哪怕是对旁人,都从不曾有过的冰冷语调,只刺的窦太后心窝一痛!
惊愕的抬起头,便见御案对策,天子启那仍带着泪痕、仍红着眼眶的面庞,已尽带上了决绝;
和狠厉!
沉着脸,俯下身,将双手撑上御案边沿;
直勾勾凝视向窦太后那混浊、黯淡的双眸,一字一句道:“儿,愿意遵从母亲的心愿,将亡父留下的家业,送给老三。”
“——但朕!”
“——绝不允许先皇的基业,被太后送到梁王手中!!!”
毫无征兆的咆哮声,吓得窦太后从御榻之上嗡然起身,满是不敢置信的瞪大双眼!
而在窦太后看不清的那张脸上,只剩下独属于汉天子的威仪,以及专属于天子启的狠辣和阴戾。
咬紧牙槽,瞪着母亲看了好一会儿,天子启便稍低下头;
俯视着御案之上,那枚被自己随手丢出,横躺在案上的传国玉玺,天子启又稍一抬眸。
目光锁定在母亲且惊且怒的面容上,手却已经从案外探出,好似五指山般,重重按在了玉玺上。
“阿武,是母亲的儿子。”
“——也是我汉家的梁王!”
“吴楚兴乱,我汉家的梁王,就该血战睢阳!”
“不是为了母亲,和我这个兄长——更不是为了朕,和我汉家的太后!”
“单就是为了自己的封国、身家性命,作为先帝的子嗣,也该当死战睢阳!”
···
“母亲,是儿的母亲。”
“——也是我汉家的太后!”
“我汉家的太后,就该颁诏册立储君太子,以安宗庙社稷、天下人心!”
“若是连这都做不到,就不配做我汉家的太后!!!”
·
余音绕梁。
天子启这接连几声咆哮,不断回荡在长信殿内,也不断冲击着窦太后的心神。
便见天子启如怒狮般,双手扶案,怒目圆睁的望向对侧的母亲;
良久,方神情冷峻的直起身,顺便将那方传国玉玺收回。
眼睛片刻都不曾从母亲那写有错愕、惊怒的面庞上移开,那方天子印玺,却也是被天子启熟练无比的系回了腰间。
转过身,背对着御案,重新将双手背负于身后,昂首眺望向殿门外。
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似是自言自语道:“荣,已经到新丰了。”
“——都到新丰好几日了。”
“册立太子储君的诏书,母后,也该动笔草拟了。”
丢下这句话,天子启便阴沉着脸,昂首挺胸,拾级而下。
走到殿中央,又止步回过身,对窦太后拱手一礼。
“儿臣,告退。”
这一回,天子启没有再迟疑,抬起脚步,便径直出了长信殿。
走出殿门外好几十步,才终于再度停下脚步,目光仍平视向前方,连一个眼角都不愿给身侧,那道跪在脚边的身影。
“从吴楚叛军大营活着回来,是卿的本事。”
“——既是逃出生天,朕,便不至于容不下一个‘黔首’袁丝。”
“只是卿,恐怕并不甘心就此隐退,又不知何时,被郡县酷吏缉拿?”
···
“朕就在宫门外等着。”
“日暮时分,若还看不到卿,带着太后册立储君的诏书走出宫门……”
言罢,天子启便再度迈开脚步,不顾袁盎那跪地匍匐,瑟瑟发抖的身影,一步不停的出了长乐宫。
天子启当然没有亲自等在宫门外。
但这一日的长安城,暗流涌动。
——长安宵禁!
——两宫戒严!
——武库戒严!
尚冠里南皮侯府、章武侯府,孝里窦府;
还有朝中,那些和窦氏一族藕断丝连的官员、军中,那些同窦氏扯上关系的将官,都被北军禁卒,将府邸围了个水泄不通!
整座长安城,都在等。
等一封诏书,从长乐宫内送出。
等那一封册立储君太子的诏书,能驱散长安这扑鼻的火药味,还长安城又一片白云蓝天。
终于,袁盎的身影,出现在了缓缓打开的宫门之内。
一同出现的,是一封以锦袋装起的懿旨。
于是,北军撤出长安,长安解除宵禁,两宫、武库解除戒严。
几乎是刚被送出长乐,那封懿旨,便被天子启早就备好的使节,快马加鞭送去了新丰。
一同传出未央宫的,是天子启先后颁布,却同时送出宫门的两道诏谕。
——奉太后懿旨,册立皇长子刘荣,为储君太子!
——着奉常、宗正有司即刻启程,于新丰太庙祭祖,以安天下人心惶惶!
至此,这场名为‘谁能做储君’的豪赌,终于等来了收盘的一刻。
皇长子刘荣,众望所归。
至于那第二道诏谕,则是让长安坊间彻底归于沉寂,同时又让东宫窦太后,自此闭上了宫门,以及心门。
——梁王刘武入朝月余,眷恋不去,有违祖制!
——着梁王刘武,即刻离京就藩!
天子启雷厉风行,一切,便也就此尘埃落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