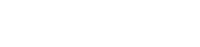近十年来,第一次当着母亲的面发怒,刘荣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但一想到将来,自己会因为老娘犯得傻,而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,刘荣就没由来的一阵烦躁。
原以为这些年来做的一切,都能让母亲有所转变,有所收敛。
直到今天,老娘一如历史时间线,拒绝了刘嫖送上门的亲事,刘荣才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:栗姬,没变。
也变不了。
栗姬,还是那个栗姬。
就好似刘荣无论做什么,都躲不过将来,那差点捅破天的一声‘老狗’……”
“唉~”
“我是做了什么孽啊……”
“上辈子,我也不是什么作恶多端,穷凶极恶的人啊?”
“咋就摊上这么个蠢妈?”
回到后殿,疲惫的躺在摇椅上,刘荣只觉太阳穴一阵突突。
抬手揉了揉,发现并没有什么用,又烦躁起身,一把推开窗户。
远远看向窗外,宫人们行走在宫中的身影,刘荣的心,只一点点沉入谷底……
“大、大哥?”
身后传来少年怯生生的轻呼,却并没有吸引刘荣的目光。
只稍侧过身,眼角撇了眼两个弟弟,又对窗外长呼出一口浊气;
调整好情绪,才回身坐回摇椅之上,随性的朝身侧一摆手。
“坐吧。”
招呼着两个弟弟坐下身,刘荣的目光,便次序从弟弟们身上扫过。
正如刘荣所言:栗姬最幸运的,莫过于以妾室之身,生下当今天子启最大的三個儿子。
老大刘荣,老二刘德,以及老三刘淤。
刘荣自不必多说,作为万众瞩目的皇长子,自是早早养出了皇家独有的贵气,以及温润如玉的随和。
而此刻,坐在刘荣身侧的两个弟弟,老二刘德喜文,整日手不释卷,摇头晃脑,俨然一个小夫子。
却也不得不提:刘德虽年纪不大,名气已然不小,尤其是对《诗》造诣不浅。
至于老三刘淤……
“本就体弱多病,便少用些茶汤,莫再冲撞了药石。”
“去,取碗温蜜水。”
伸手夺过刘淤手上端着的茶碗,又对一旁伺候的宫人招呼一声;
待殿室内,只剩下兄弟三人的身影,刘荣才深吸一口气,将目光投向二弟刘德。
“如何?”
“今日早朝,可有什么变故?”
看出大哥眉宇间隐隐带着的戾气,刘德本能的感到一丝惶恐;
见大哥说起正事,也不由暗下稍松口气,端起茶碗抿下一口,才点头道:“父皇颁诏除了国丧,大哥应该已经知道了。”
“紧接着,宗正启奏:梁王再三请朝长安,以奔父丧。”
“父皇,答允了……”
“——这么早?”
刘德话音未落,便见刘荣才刚松缓些许的眉头,只霎时间再度拧在了一起;
待听到最后那句‘父皇答允了’,更是脱口而出一句:这么早?
“太祖高皇帝制:国丧过后半年之内,诸侯不得朝长安。”
“父皇怎会如此轻易,便允了梁王叔所请?”
话问出口,刘荣便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。
只片刻之后,刘德苦笑着道出一番话,也算是验证了刘荣的猜测。
“说是近几日,皇祖母,绝食了……”
此言一出,殿室内便彻底沉寂下来,就连拿到温蜜水的老三刘淤,也不由自主的将碗从嘴边放下,生怕发出响动。
太祖高皇帝规定国丧期间,诸侯王不得朝觐长安,自然是为了确保政权交接的安稳。
但如今汉家最大,甚至可以说是比天还大的规矩,却是个‘孝’字。
就连皇帝的谥号,前面都要加一个‘孝’字,如‘孝惠皇帝’刘盈,以及刚驾崩不久的‘孝文皇帝’刘恒,便可见一斑。
按照制度,天子启当然不应该允准梁王的请求——哪怕驾崩的先孝文皇帝,也同样是梁王的父亲。
但当母亲窦太后以绝食相逼,即便是在储位上坐了足足二十多年,更太子监国多年、早已羽翼丰满的天子启,也只能乖乖低头。
甚至即便是低了头,天子启也依旧难逃‘忤逆母亲,迫使母亲绝食’的骂名。
“老爷子也不容易啊~”
“这才刚即位,屁股底下的皇位都还没坐热,就被皇祖母狠狠摆了一道。”
终还是刘荣看似随意的一语,打破了殿内的沉寂。
绝食?
或许吧;
或许窦太后真的象征性少吃了几口饭,以宣示自己对皇帝儿子的不满。
但才刚见过祖母窦太后,刘荣很确定自己并未从祖母身上,看出饿了好几天、即将活活饿死的萎靡之色。
——至少当着刘荣的面指桑骂槐,训斥女儿刘嫖的时候,窦太后还中气十足。
皱眉思虑片刻,又抬起手,将拧在一起的眉头揉开些,刘荣才满是疲惫道:“梁王叔请朝长安,本是人之常情。”
“——无论父皇允不允,梁王叔这个‘急于奔父丧’的姿态,都是必须要做,也是一定会做的。”
“按理来说,梁王叔苦苦哀求,父皇忍痛不允——这才符合常态。”
“偏偏皇祖母又横插一脚,假戏做了真,梁王叔还真要朝长安了……”
多年来锻炼出的敏锐嗅觉,以及穿越者的先见之明,让刘荣隐约察觉到一股异常。
又不好和两个弟弟说的太明白,索性直接做下安排。
“梁王叔素来喜好文赋,身边不知养了多少文人墨客。”
“等梁王叔来了长安,就辛苦老二多走动走动,借着交流文赋的幌子,探探梁王叔的口风。”
“——尤其是王叔身边的人,一定要多留意。”
“我总觉得梁王叔身边,似有奸人蛊惑;”
“梁王叔此朝长安,来者不善……”
得到指令,刘德当即拱手领命,暗下思虑起刘荣话中深意。
一旁的刘淤年纪小些,显然没往深处想,只眼巴巴等着自家大哥给自己也安排任务。
“王叔身边有一谋士,曰:韩安国,当已官拜中大夫。”
“试试看能不能在此人身边安插个眼线,或许能探出些什么。”
同样得到任务,老三刘淤喜不自胜,刚要拍胸脯应下,却又悄然皱起了眉头,似乎是在苦恼于任务细节。
对于两个弟弟的内心活动,刘荣自是了然于胸,却也没多管;
交代二弟早做准备,又顺带提了一嘴老三糟糕的身体状况,让老二多照看着些,便从摇椅上起身,负手朝殿外走去。
——殿门外,一寺人含笑而立,远远对刘荣拱了拱手。
于是,刘荣只得拖着疲惫的身体,跟随着寺人的步伐,朝着未央宫最高的那处殿室走去。
但一想到将来,自己会因为老娘犯得傻,而落得个不得好死的下场,刘荣就没由来的一阵烦躁。
原以为这些年来做的一切,都能让母亲有所转变,有所收敛。
直到今天,老娘一如历史时间线,拒绝了刘嫖送上门的亲事,刘荣才终于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:栗姬,没变。
也变不了。
栗姬,还是那个栗姬。
就好似刘荣无论做什么,都躲不过将来,那差点捅破天的一声‘老狗’……”
“唉~”
“我是做了什么孽啊……”
“上辈子,我也不是什么作恶多端,穷凶极恶的人啊?”
“咋就摊上这么个蠢妈?”
回到后殿,疲惫的躺在摇椅上,刘荣只觉太阳穴一阵突突。
抬手揉了揉,发现并没有什么用,又烦躁起身,一把推开窗户。
远远看向窗外,宫人们行走在宫中的身影,刘荣的心,只一点点沉入谷底……
“大、大哥?”
身后传来少年怯生生的轻呼,却并没有吸引刘荣的目光。
只稍侧过身,眼角撇了眼两个弟弟,又对窗外长呼出一口浊气;
调整好情绪,才回身坐回摇椅之上,随性的朝身侧一摆手。
“坐吧。”
招呼着两个弟弟坐下身,刘荣的目光,便次序从弟弟们身上扫过。
正如刘荣所言:栗姬最幸运的,莫过于以妾室之身,生下当今天子启最大的三個儿子。
老大刘荣,老二刘德,以及老三刘淤。
刘荣自不必多说,作为万众瞩目的皇长子,自是早早养出了皇家独有的贵气,以及温润如玉的随和。
而此刻,坐在刘荣身侧的两个弟弟,老二刘德喜文,整日手不释卷,摇头晃脑,俨然一个小夫子。
却也不得不提:刘德虽年纪不大,名气已然不小,尤其是对《诗》造诣不浅。
至于老三刘淤……
“本就体弱多病,便少用些茶汤,莫再冲撞了药石。”
“去,取碗温蜜水。”
伸手夺过刘淤手上端着的茶碗,又对一旁伺候的宫人招呼一声;
待殿室内,只剩下兄弟三人的身影,刘荣才深吸一口气,将目光投向二弟刘德。
“如何?”
“今日早朝,可有什么变故?”
看出大哥眉宇间隐隐带着的戾气,刘德本能的感到一丝惶恐;
见大哥说起正事,也不由暗下稍松口气,端起茶碗抿下一口,才点头道:“父皇颁诏除了国丧,大哥应该已经知道了。”
“紧接着,宗正启奏:梁王再三请朝长安,以奔父丧。”
“父皇,答允了……”
“——这么早?”
刘德话音未落,便见刘荣才刚松缓些许的眉头,只霎时间再度拧在了一起;
待听到最后那句‘父皇答允了’,更是脱口而出一句:这么早?
“太祖高皇帝制:国丧过后半年之内,诸侯不得朝长安。”
“父皇怎会如此轻易,便允了梁王叔所请?”
话问出口,刘荣便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。
只片刻之后,刘德苦笑着道出一番话,也算是验证了刘荣的猜测。
“说是近几日,皇祖母,绝食了……”
此言一出,殿室内便彻底沉寂下来,就连拿到温蜜水的老三刘淤,也不由自主的将碗从嘴边放下,生怕发出响动。
太祖高皇帝规定国丧期间,诸侯王不得朝觐长安,自然是为了确保政权交接的安稳。
但如今汉家最大,甚至可以说是比天还大的规矩,却是个‘孝’字。
就连皇帝的谥号,前面都要加一个‘孝’字,如‘孝惠皇帝’刘盈,以及刚驾崩不久的‘孝文皇帝’刘恒,便可见一斑。
按照制度,天子启当然不应该允准梁王的请求——哪怕驾崩的先孝文皇帝,也同样是梁王的父亲。
但当母亲窦太后以绝食相逼,即便是在储位上坐了足足二十多年,更太子监国多年、早已羽翼丰满的天子启,也只能乖乖低头。
甚至即便是低了头,天子启也依旧难逃‘忤逆母亲,迫使母亲绝食’的骂名。
“老爷子也不容易啊~”
“这才刚即位,屁股底下的皇位都还没坐热,就被皇祖母狠狠摆了一道。”
终还是刘荣看似随意的一语,打破了殿内的沉寂。
绝食?
或许吧;
或许窦太后真的象征性少吃了几口饭,以宣示自己对皇帝儿子的不满。
但才刚见过祖母窦太后,刘荣很确定自己并未从祖母身上,看出饿了好几天、即将活活饿死的萎靡之色。
——至少当着刘荣的面指桑骂槐,训斥女儿刘嫖的时候,窦太后还中气十足。
皱眉思虑片刻,又抬起手,将拧在一起的眉头揉开些,刘荣才满是疲惫道:“梁王叔请朝长安,本是人之常情。”
“——无论父皇允不允,梁王叔这个‘急于奔父丧’的姿态,都是必须要做,也是一定会做的。”
“按理来说,梁王叔苦苦哀求,父皇忍痛不允——这才符合常态。”
“偏偏皇祖母又横插一脚,假戏做了真,梁王叔还真要朝长安了……”
多年来锻炼出的敏锐嗅觉,以及穿越者的先见之明,让刘荣隐约察觉到一股异常。
又不好和两个弟弟说的太明白,索性直接做下安排。
“梁王叔素来喜好文赋,身边不知养了多少文人墨客。”
“等梁王叔来了长安,就辛苦老二多走动走动,借着交流文赋的幌子,探探梁王叔的口风。”
“——尤其是王叔身边的人,一定要多留意。”
“我总觉得梁王叔身边,似有奸人蛊惑;”
“梁王叔此朝长安,来者不善……”
得到指令,刘德当即拱手领命,暗下思虑起刘荣话中深意。
一旁的刘淤年纪小些,显然没往深处想,只眼巴巴等着自家大哥给自己也安排任务。
“王叔身边有一谋士,曰:韩安国,当已官拜中大夫。”
“试试看能不能在此人身边安插个眼线,或许能探出些什么。”
同样得到任务,老三刘淤喜不自胜,刚要拍胸脯应下,却又悄然皱起了眉头,似乎是在苦恼于任务细节。
对于两个弟弟的内心活动,刘荣自是了然于胸,却也没多管;
交代二弟早做准备,又顺带提了一嘴老三糟糕的身体状况,让老二多照看着些,便从摇椅上起身,负手朝殿外走去。
——殿门外,一寺人含笑而立,远远对刘荣拱了拱手。
于是,刘荣只得拖着疲惫的身体,跟随着寺人的步伐,朝着未央宫最高的那处殿室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