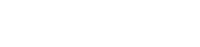汉文帝后元七年秋,长安。
朝阳如墨,挥洒于宫室之上,为古朴厚重的汉家宫廷,蒙上了一层独属于晚秋的橙黄。
巍峨的宫墙之内,宫人们如蚂蚁般,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自己今天的工作:或攀上木梯,或举起长杆,将挂满整座长乐宫的丧灯、丧布依次取下。
——三个月前的今天,太宗孝文皇帝驾崩,国丧。
而今天,恰好是国丧结束的日子。
国丧结束,却并不意味着先帝驾崩的苦楚,便就此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间。
宫墙内外,街头巷尾,仍旧不时响起人们低沉哀婉的啜泣声。
只不过今日,长乐宫长信殿传出的,却并非太后窦氏的哭声;
所哭的,也并非是驾崩的太宗孝文皇帝……
“呜~呜呜……”
“母后~”
“女儿可没脸活啦~”
“呜~~~呜呜呜呜……”
长乐宫,长信殿。
刚住进长乐宫不久的窦太后,此刻身着夫丧、额系孝带,坐在御榻之上;
双手将鸠杖柱于身侧,额头轻轻靠在杖顶,涣散无焦的双眸,透着无尽的哀沉。
在窦太后身侧,妇人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岁的年纪,倒是已脱下了孝衣,抽抽搭搭间,已然哭成了泪人。
若单看这母女二人,如此场景,好似是妇人被坏了清白,找太后母亲来哭诉;
但在这母女二人身前,却还另跪着一道略显稚嫩的身影……
“姑母莫哭,莫哭……”
“千错万错,都是侄儿那母亲不知礼数;”
“姑母可万莫往心里去,再气坏了身子……”
这句话,刘荣今天反反复复,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
只是光看妇人那满脸泪痕就能知道,刘荣百般赔礼告罪,妇人愣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,只委屈巴巴躲在太后母亲身旁抽泣。
见此,刘荣只得侧过身,自宫女手中接过不知道第几块手帕,而后小心翼翼递上前。
一边哄着哭成泪人的姑母刘嫖,心下也一边唏嘘起自己的悲惨命运。
“我这母亲啊……”
掰着指头算下来,穿越到这个时代,也有个十来年了;
在这十来年的穿越生涯中,刘荣深切体会到了一个坑人的老娘,究竟能把儿子迫害到什么程度。
刘荣母何人?
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,甚至力压扁鹊、华佗的青史第一神医,道上人尊称一声:栗姬。
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,再过上個七八年,这位神医便会对弥留之际的皇帝丈夫,含怒喊出一声:老狗!
然后,原本命悬一线,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,出气多进气少的天子刘启,就会被气的硬生生撑过来。
之后的故事,自然是栗姬九族消消乐,已经贵为太子储君的刘荣,也被那声‘老狗’害的废黜储位,封王就藩,不得善终……
意识到自己的身份,以及后半生将要面临的命运后,为了避免那无比悲惨的结局,刘荣不知做了多少努力。
老娘发火了,刘荣哄着;
老娘乏闷了,刘荣陪着;
便是老娘不出任何人所料的闯了祸,刘荣也是任劳任怨的奔走,给老娘擦屁股。
原以为十年如一日的努力,总该取得一些成果;
直到今天,刘荣只能生无可恋的承认:时至今日,自己依旧在过着‘一人血书,跪求傻缺老妈别再闯祸’的悲惨生活。
这不?
稍不留神,便又是好大一桩祸事……
“姑母……”
“姑母?”
哄了半天,又语带祈求的唤了唤,仍不见刘嫖的哭声有丝毫减弱的趋势,刘荣只得将求助的目光,投向一旁的祖母窦太后。
——甭管老太太看不看的见,也无论老太太帮不帮的上忙;
眼下,刘荣也实在是别无他法了……
“好了好了~”
“一把年纪的人了,还当着侄儿的面哭哭啼啼,也不嫌丢人?”
许是眼疾还不太严重,隐约看见刘荣将脑袋转向自己,窦太后终还是开了口,止住了女儿刘嫖的啜泣。
只是虽止住了哭,刘嫖却并未就此消停;
用手帕抹了抹脸上泪水,便带着哭腔诉起苦来。
“女儿、女儿好歹是先帝和太后的独女,皇帝一母同胞的长姊;”
“莫说她栗姬‘夫人’的位分,便是住在椒房殿的皇后,也总该给女儿留三分体面才是?”
“她可倒好,女儿携礼拜访,话都没来得及说上两句,就连打带骂的,把女儿给赶出来了……”
“呜~呜呜……”
“女儿、女儿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啊~”
“呜~~~~~~呜呜呜……”
没两句话的功夫,防空警报再次拉响,刺的殿外宫人直皱眉头,想捂耳朵偏又不敢,便只得挪动着脚步躲远了些。
自知理亏,刘荣自是不敢表露出丝毫不耐,倒是一旁的窦太后,先被女儿没完没了的哭声惹恼了。
“够了!”
“过去这几个月,我听到的哭声还少吗?!”
“非要让我这瞎眼老寡妇,陪你这混账一起哭不成?!!”
毫无征兆的几声沉呵,顿时惊得刘嫖愣在原地,就连那几滴自眼眶滑落的泪,都被吓的停在了刘嫖脸上。
便见窦太后面色阴沉的转过头,皱眉望向面前的长孙刘荣。
“事情的经过,皇长子都知道了?”
清冷一语,吓的刘荣嗡时冷汗直冒,只赶忙一躬身:“孙、孙儿知晓……”
知道归知道,刘荣也是真的没脸提……
“今日早朝,皇帝才颁下国丧结束的诏书,就非得着急忙慌跑去,寻那刁妇找不自在!”
“国丧三月所悼念的,难道不是你父?!!”
“就非得在国丧结束当天,火急火燎为阿娇说亲?!!!”
本就因自家老娘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,又见祖母当着自己的面训斥起刘嫖,刘荣只将头埋的更低,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丢人呐……
“行了。”
“这件事,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“皇长子赔了礼、谢了罪,就算是看在侄儿纯孝的份上,也别再揪着不放了。”
以不容置疑的语气,勒令刘嫖不要再穷究不舍,窦太后便再次将清冷的目光,投向正低头寻找地缝的刘荣。
感受到祖母投向自己的目光,意识到窦太后方才那番话,不单是在为今天的事拍板,同时也是在委婉送客;
刘荣当即便起身,朝面前的两位妇人分别行过礼,并向刘嫖再三保证‘不日登门谢罪’,这才羞愧难当的告退离去。
刘荣抬脚踏出长信殿,刘嫖滔滔不绝的泪水便应声而止,小心翼翼的望向身旁。
“母、母后?”
试探一语,却见窦太后深吸一口气,摸索着站起身:“就此打住。”
“她栗姬瞧不上,阿娇,便不嫁皇长子了。”
“就不信我这张老脸,还不能为阿娇寻得一门好亲事?”
此言一出,刘嫖当下急的变了脸色,赶忙起身扶住窦太后,语气中满是焦急。
“母后~”
“阿娇,那可是母后最宝贝的心头肉啊~”
“若是做不成太子妃,阿娇日后,哪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?”
“母后难道就忍心阿娇……”
“——谁说不嫁皇长子,就做不成太子妃了?”
话音未落,便闻窦太后淡然一语,刘嫖不由又是一愣。
却见窦太后迈开脚步,一边朝着后殿的方向走,嘴上一边还不忘嘟囔着什么。
“栗姬不要阿娇这个儿媳,我这瞎眼老婆子,自是做不了皇长子的主。”
“但我好歹也是皇帝的母亲,已然搬出椒房、住进了长乐;”
“——母仪天下的太后,总不至于连册立储君的事,也做不得主吧?”
“册立储君,可还需我这瞎眼老婆子颁下懿旨,再亲自带着储君,一同祭祖告庙呢……”
朝阳如墨,挥洒于宫室之上,为古朴厚重的汉家宫廷,蒙上了一层独属于晚秋的橙黄。
巍峨的宫墙之内,宫人们如蚂蚁般,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自己今天的工作:或攀上木梯,或举起长杆,将挂满整座长乐宫的丧灯、丧布依次取下。
——三个月前的今天,太宗孝文皇帝驾崩,国丧。
而今天,恰好是国丧结束的日子。
国丧结束,却并不意味着先帝驾崩的苦楚,便就此消失在了这片天地之间。
宫墙内外,街头巷尾,仍旧不时响起人们低沉哀婉的啜泣声。
只不过今日,长乐宫长信殿传出的,却并非太后窦氏的哭声;
所哭的,也并非是驾崩的太宗孝文皇帝……
“呜~呜呜……”
“母后~”
“女儿可没脸活啦~”
“呜~~~呜呜呜呜……”
长乐宫,长信殿。
刚住进长乐宫不久的窦太后,此刻身着夫丧、额系孝带,坐在御榻之上;
双手将鸠杖柱于身侧,额头轻轻靠在杖顶,涣散无焦的双眸,透着无尽的哀沉。
在窦太后身侧,妇人看上去约莫三四十岁的年纪,倒是已脱下了孝衣,抽抽搭搭间,已然哭成了泪人。
若单看这母女二人,如此场景,好似是妇人被坏了清白,找太后母亲来哭诉;
但在这母女二人身前,却还另跪着一道略显稚嫩的身影……
“姑母莫哭,莫哭……”
“千错万错,都是侄儿那母亲不知礼数;”
“姑母可万莫往心里去,再气坏了身子……”
这句话,刘荣今天反反复复,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遍。
只是光看妇人那满脸泪痕就能知道,刘荣百般赔礼告罪,妇人愣是一个字也没听进去,只委屈巴巴躲在太后母亲身旁抽泣。
见此,刘荣只得侧过身,自宫女手中接过不知道第几块手帕,而后小心翼翼递上前。
一边哄着哭成泪人的姑母刘嫖,心下也一边唏嘘起自己的悲惨命运。
“我这母亲啊……”
掰着指头算下来,穿越到这个时代,也有个十来年了;
在这十来年的穿越生涯中,刘荣深切体会到了一个坑人的老娘,究竟能把儿子迫害到什么程度。
刘荣母何人?
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,甚至力压扁鹊、华佗的青史第一神医,道上人尊称一声:栗姬。
按照原本的历史轨迹,再过上個七八年,这位神医便会对弥留之际的皇帝丈夫,含怒喊出一声:老狗!
然后,原本命悬一线,半只脚已经踏进棺材,出气多进气少的天子刘启,就会被气的硬生生撑过来。
之后的故事,自然是栗姬九族消消乐,已经贵为太子储君的刘荣,也被那声‘老狗’害的废黜储位,封王就藩,不得善终……
意识到自己的身份,以及后半生将要面临的命运后,为了避免那无比悲惨的结局,刘荣不知做了多少努力。
老娘发火了,刘荣哄着;
老娘乏闷了,刘荣陪着;
便是老娘不出任何人所料的闯了祸,刘荣也是任劳任怨的奔走,给老娘擦屁股。
原以为十年如一日的努力,总该取得一些成果;
直到今天,刘荣只能生无可恋的承认:时至今日,自己依旧在过着‘一人血书,跪求傻缺老妈别再闯祸’的悲惨生活。
这不?
稍不留神,便又是好大一桩祸事……
“姑母……”
“姑母?”
哄了半天,又语带祈求的唤了唤,仍不见刘嫖的哭声有丝毫减弱的趋势,刘荣只得将求助的目光,投向一旁的祖母窦太后。
——甭管老太太看不看的见,也无论老太太帮不帮的上忙;
眼下,刘荣也实在是别无他法了……
“好了好了~”
“一把年纪的人了,还当着侄儿的面哭哭啼啼,也不嫌丢人?”
许是眼疾还不太严重,隐约看见刘荣将脑袋转向自己,窦太后终还是开了口,止住了女儿刘嫖的啜泣。
只是虽止住了哭,刘嫖却并未就此消停;
用手帕抹了抹脸上泪水,便带着哭腔诉起苦来。
“女儿、女儿好歹是先帝和太后的独女,皇帝一母同胞的长姊;”
“莫说她栗姬‘夫人’的位分,便是住在椒房殿的皇后,也总该给女儿留三分体面才是?”
“她可倒好,女儿携礼拜访,话都没来得及说上两句,就连打带骂的,把女儿给赶出来了……”
“呜~呜呜……”
“女儿、女儿还有什么脸面苟活于世啊~”
“呜~~~~~~呜呜呜……”
没两句话的功夫,防空警报再次拉响,刺的殿外宫人直皱眉头,想捂耳朵偏又不敢,便只得挪动着脚步躲远了些。
自知理亏,刘荣自是不敢表露出丝毫不耐,倒是一旁的窦太后,先被女儿没完没了的哭声惹恼了。
“够了!”
“过去这几个月,我听到的哭声还少吗?!”
“非要让我这瞎眼老寡妇,陪你这混账一起哭不成?!!”
毫无征兆的几声沉呵,顿时惊得刘嫖愣在原地,就连那几滴自眼眶滑落的泪,都被吓的停在了刘嫖脸上。
便见窦太后面色阴沉的转过头,皱眉望向面前的长孙刘荣。
“事情的经过,皇长子都知道了?”
清冷一语,吓的刘荣嗡时冷汗直冒,只赶忙一躬身:“孙、孙儿知晓……”
知道归知道,刘荣也是真的没脸提……
“今日早朝,皇帝才颁下国丧结束的诏书,就非得着急忙慌跑去,寻那刁妇找不自在!”
“国丧三月所悼念的,难道不是你父?!!”
“就非得在国丧结束当天,火急火燎为阿娇说亲?!!!”
本就因自家老娘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,又见祖母当着自己的面训斥起刘嫖,刘荣只将头埋的更低,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丢人呐……
“行了。”
“这件事,就到此为止吧。”
“皇长子赔了礼、谢了罪,就算是看在侄儿纯孝的份上,也别再揪着不放了。”
以不容置疑的语气,勒令刘嫖不要再穷究不舍,窦太后便再次将清冷的目光,投向正低头寻找地缝的刘荣。
感受到祖母投向自己的目光,意识到窦太后方才那番话,不单是在为今天的事拍板,同时也是在委婉送客;
刘荣当即便起身,朝面前的两位妇人分别行过礼,并向刘嫖再三保证‘不日登门谢罪’,这才羞愧难当的告退离去。
刘荣抬脚踏出长信殿,刘嫖滔滔不绝的泪水便应声而止,小心翼翼的望向身旁。
“母、母后?”
试探一语,却见窦太后深吸一口气,摸索着站起身:“就此打住。”
“她栗姬瞧不上,阿娇,便不嫁皇长子了。”
“就不信我这张老脸,还不能为阿娇寻得一门好亲事?”
此言一出,刘嫖当下急的变了脸色,赶忙起身扶住窦太后,语气中满是焦急。
“母后~”
“阿娇,那可是母后最宝贝的心头肉啊~”
“若是做不成太子妃,阿娇日后,哪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?”
“母后难道就忍心阿娇……”
“——谁说不嫁皇长子,就做不成太子妃了?”
话音未落,便闻窦太后淡然一语,刘嫖不由又是一愣。
却见窦太后迈开脚步,一边朝着后殿的方向走,嘴上一边还不忘嘟囔着什么。
“栗姬不要阿娇这个儿媳,我这瞎眼老婆子,自是做不了皇长子的主。”
“但我好歹也是皇帝的母亲,已然搬出椒房、住进了长乐;”
“——母仪天下的太后,总不至于连册立储君的事,也做不得主吧?”
“册立储君,可还需我这瞎眼老婆子颁下懿旨,再亲自带着储君,一同祭祖告庙呢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