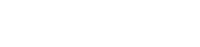马邑战场一片沉寂,战争虽然还没结束,但一切,却似乎已经尘埃落定。
河套战场,则是以河套北部的大河流域为界;
——北侧的高阙,匈奴人一边为河套的丢失而咬牙切齿,焦急地等候着回援的单于庭主力,一边又暗暗胆战,唯恐对岸的汉人不知足,会再度渡过大河,兵临高阙!
南侧,则是战前便以‘对北地进行战后重建’的名义抵达北地,如今也已经踏足河套的少府匠人、官奴,热火朝天的修筑城墙。
在得到河南地之后,汉家除了早早定下‘朔方’的郡名之外,同时也为这座才刚打好地基的临河城池起好了名字。
博望城。
且不提这‘博望’二字,究竟含有怎样的含义,又或是华夏民族的期盼;
单就是当今天子荣曾经的太子私苑:博望苑,就足以说明一切。
对于博望城,汉家——尤其是当今天子荣,抱以极大的期待!
很显然,在河套已经到手的情况下,这极大期待,不可能仅仅只是‘守住河套门户’这么简单……
战事稳步推进,同一时间的长安城,却是一副莫名诡异的安静。
倒不是有人,想要在如此关头浑水摸鱼,搞点见不得人的勾当;
而是战事的紧张,实在是过于顺利、过于出乎长安朝堂内外的预料了。
——那可是河南地!
秦得之,便使游牧之民不敢南下牧马,汉失之,便受战马奇缺之苦凡五十余年,至今都抬不起头的宝地!
如此宝地,匈奴人不说是以举国之力守护,也总该驻扎重兵,并时刻防备汉家的图谋?
但实际情况却是:数百年前的那句‘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’,以及‘好战必亡,忘战必危’,在这场河套战役之后,达到了含金量顶峰。
匈奴人,实在是在河套,过了太久太久的安稳日子;
以至于他们都忘了河套,并不曾被匈奴单于庭滴血认主。
匈奴人,在汉家的再三退让、多年忍辱负重下,过了太多太多年的太平日子。
以至于他们,都忘记了短短几十年前,同样是汉人的另一个王朝,将他们,乃至于另外两大霸主:东胡、月氏,打的根本不敢隔着大幕而难忘,只得龟缩漠北,茹毛饮血。
作为游牧文明政权,匈奴人当然武德昌盛。
但对于汉家、对于华夏民族,匈奴人,早就失去了本该怀有的戒备,以及足够的战略重视。
也是直到这个时候,长安街头巷尾,再也没人说太宗孝文皇帝、先孝景皇帝——乃至更早的太祖高皇帝、吕太后,是对外软弱、没有血性了。
河套,就是汉家历代先皇忍辱负重,不惜以和亲虚与委蛇,逐步麻痹匈奴人的神经,所最终结出的果实。
委屈、谩骂、指责,是由历代先皇承受的;
依次麻痹敌人,并最终一举夺回河套,是当今刘荣一手操办的。
但绝对不会有人说:河套之功,独在当今刘荣。
甚至就连刘荣自己,也同样如此。
至于充斥着长安城上空,乃至朝堂内外的诡异沉寂,刘荣也只是感怀不已,唏嘘不止。
如果说过去这几十年,匈奴人是日子过的太好,以至于忘了有一个名为‘汉人’的强大敌人;
那汉家上下君民,则是在过去这几十年,受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苦难,以至于都忘了自己是天汉贵胄、诸夏子民。
——匈奴胡骑不可力敌,敌来不可出城迎敌的意识,已经深入汉家上下君臣的灵魂深处!
至于主动出塞,主动发起攻击,更是令如今汉家上下官僚贵族、苍生黎庶,都感到骇人听闻的事。
在最开始,天下人都以为此战,和年初的朝那塞一战一样,是一场单纯的马邑保卫战。
守住马邑,就算赢了;
守不住马邑,那就退守楼烦,亦或是更南的平城,也总归不算输太多。
等北地方向传回消息,说汉军西出朝那塞,渡大河、谋河套之时,天下人无不瞠目结舌,语结无措。
什么鬼!
我汉家战马奇缺,骑军遥遥无期,怎能如此兵行险着,主动出塞?!
朝堂之上,更是冒出了不知多少老学究、老顽固,指着刘荣的鼻子,骂一些‘昏君祸国’‘累死三军’之类的脏话。
没人想过此战,汉家真的能打下河套;
大家都觉得这个战略布置,实在是昏聩到了一定程度,无疑是以卵击石,蚍蜉撼树!
绝大多数人都认为,此战最好的结果,是汉军在河套没有遭受太大损失,并顺利退回了朝那塞。
如果可以顺便绘制一些地图,了解一下河套地区的地形地貌,就已经能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。
至于最差的结果,根本没人敢想。
——出塞作战的部队,难道没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吗?
很有可能!
步兵集群,在草原,在开阔地形,被灵活的骑兵骑军咬住,又举目无援,孤军奋战;
怎么看,都怎么像是要被全歼的架势。
甚至就连北地方面军在塞外被全歼,汉家一战而失十数万战卒,都还不是全部损失,还仅仅只是开始!
一旦北地方面军在塞外被全歼,那匈奴人必定会顺势进攻朝那塞!
而后,便大概率是太宗皇帝十四年,那场动摇汉家国本的战争的复刻版。
所有人都这么想。
除了朝堂之上,不到一半的了解内由,又或是知晓兵事、了解汉家目前的军事实力的官员、勋贵——其他所有人,几乎都是这么想的。
朝堂之上,功勋们惴惴不安,官员们牢骚不断;
街头巷尾,闲人懒汉们更是破口大骂,指点江山。
至于关东,才刚安稳下来的宗亲诸侯们,也都纷纷动起了别样的心思。
所有人都觉得主动出击,以步兵去主动进攻骑兵、从边墙主动出塞,跑到游牧之民的地盘打仗,无异于自掘坟墓。
于是,当河套易主,汉家彻底夺回河南地的好消息传回时,所有人都亚麻呆住了。
啊?
啊???
就这么,打下来了?
甚至都没怎么打,就,拿回河南地了?
匈奴人什么时候,变得如此不堪一击?
我汉家,又是何时变得如此强大,居然能如此轻而易举之间,便夺回那片决定着东亚怪物房骑兵战力归属的河南地?
而这种诡异的氛围,便一直持续至今。
直到今日,长安朝堂都草拟好‘于河南地设立朔方郡’的方案,汉家上上下下,依旧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
大家都懵懵的,愣愣的;
好像在做梦。
又怎么都无法从这美妙,却也完全‘不合逻辑’的美梦中转醒。
却也有人,在所有人都被这‘天降惊喜’砸的晕头转向时,一边为此而感到振奋、喜悦,一边又迎来自己原本暗淡无关的人生中,最为重要的一处转折……
“阿姊,近来可好?”
长安尚冠里,平阳侯府。
作为侯府奴生子、歌舞姬,卫子夫原本的住处,是在侯府后院东南角,毗邻茅厕的一处大茅屋。
那茅屋,也并非独属卫子夫,而是住着和卫子夫同等身份的十几二十个妙龄女子。
以中间为道路,两侧砌有矮泥榻的大通铺,二十来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,却如糙汉子般挤在一起住。
而今,卫子夫却住进了一座独属于自己的小瓦房。
不大,但独属于卫子夫一人……
“一切都好。”
···
“可曾去看过母亲了?”
听闻弟弟卫青的问候,卫子夫强挤出一抹笑意,紧接着便提醒起弟弟,也要去看看母亲。
——近些年来,母亲的身体并不很好。
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,早年落下的病根,更是时时刻刻折磨着母亲老迈、残破的身躯。
作为奴仆,母亲从不曾有坐月子、养身子的福分;
偏又一胎接着一胎,从二十来岁一直生育至今,便是在怎办结实的身子骨,也早就被早年的病根,给摧残的不成样子。
作为出生在侯府的奴生子,卫子夫虽然年纪还小,却也懂得了许多人世间的腌臜、龃龉。
在侯府内的待遇突然发生改变,卫子夫也大致能猜测到自己,或许是被某个大人物看中了。
并非侯爷突然通了人性,打算好好对待侯府的下人、奴仆们;
而是侯爷念在那个大人物的颜面,才决定替那位大人物好生养着自己,一直到能嫁人——或者说,是能用肉体取悦那位大人物的年纪。
对于这样的命运,卫子夫并没有感到什么悲哀、唏嘘之类。
——对于自己的命运,卫子夫早有预料。
而如今这条路,甚至可以说是曾经,卫子夫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妙结局。
作为奴生子,能给某个大人物做姬妾——甚至哪怕是一夜承欢,也比在这侯府,成为母亲那样的侍妾,要好上太多太多。
现如今,卫子夫脑子里,已经不怎么想有关自己的事了。
——老老实实在侯府住着,女红的技艺学着,等着长大,被那位大人物接走便是。
真正让卫子夫感到担忧、挂念的,是已经重病卧榻的母亲,以及这些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。
一声‘可能去探望过母亲了?’,却见弟弟卫青略有些羞涩的挠了挠头,卫子夫当即便心下了然。
深吸一口气,叹息间,将弟弟卫青的手轻轻拉过;
而后便是一副苦口婆心的口吻,为弟弟谋划起未来的人生道路。
“姊姊我,许是要有大福气了。”
“再不三五年,便或要被某位君侯接走,为姬为妾。”
“——能让咱们这位平阳侯,都如此小心对待的,怕也不是什么寻常千八百户食邑的闲散君侯。”
“到了那时,阿青若能有些出息,我也好在那位君侯面前引荐一二,好为阿青谋条出路……”
卫子夫当然知道,如今的卫青,不知由于什么缘故,得到了当今天子的接见,并留在了宫中。
但作为这个时代身份最低微、最底层的人——尤其还是女人,卫子夫同样清楚:有些东西,并非是什么身份的人,都能拥有的。
就好比弟弟卫青,十岁出头的年纪,便得了当朝天子赏识;
侯府的仆人们都说,卫子夫如今的待遇,是沾了弟弟的光,平阳侯是看在当今天子对卫青的青睐,才提高了卫子夫这一大家子的待遇。
但卫子夫很清楚:弟弟卫青,且不说有多大本事——就算真有能让当今天子赏识的本事,单一个奴生子的身份,也足以让卫青穷极一生,都看不见未央宫宫门之内的只砖片瓦。
这,是一个讲究血脉、讲究身份地位的时代。
而奴生子之所以卑贱,是因为他们的血脉不被承认,属于‘无祖无后’之人。
所以,卫子夫大致推断:弟弟能得到当今天子召见,大抵是因为皇后的缘故。
许是陛下一时兴起,要找侯府的人问问有关皇后的事之类。
也正是因此,卫子夫同样清楚:弟弟卫青,是不能这样被留在宫里的。
——皇宫里,那可是随便拎一个人出来,就能扯上开国元勋家族,更甚至直接就是刘氏宗亲皇室的地方!
弟弟一介奴生子,如何能待在那样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?
德不配位,反受其害!
与其让弟弟待在那么一与身份不符,且注定无法拥有未来的地方,还不如找个机会出空,攀上某一家功侯,给某位侯爵家的少君侯做亲兵,拿命拼出来一个前程,才来的更实际一些。
对于卫青,乃至所有的兄弟姐妹,卫子夫的期盼都不算太高。
恢复民籍,重新成为‘人’,而非属于他人的财富,已经是卫子夫穷尽想象力,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未来。
只是要想达成这一目标,需要机遇,需要勇气,甚至很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,才能为后代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……
“阿姊……”
“咳咳;”
“阿姊……”
“平阳侯,难道不曾与阿姊说起吗?”
正皱眉思虑间,弟弟卫青面色古怪的一问,只惹得卫子夫眉头陡然一皱。
——莫非,另有变数?!
却见卫青若有所思的低下头,思考片刻,才压低声线道:“平阳侯礼待阿姊,其实,是因为陛下有所交代……”
“陛下还跟我说,我能入宫侍奉于陛下左右,甚至还能看到石渠阁的兵书,也是陛下念在阿姊的面上……”
“陛下还说,弟弟将来,是要做外戚的……”
河套战场,则是以河套北部的大河流域为界;
——北侧的高阙,匈奴人一边为河套的丢失而咬牙切齿,焦急地等候着回援的单于庭主力,一边又暗暗胆战,唯恐对岸的汉人不知足,会再度渡过大河,兵临高阙!
南侧,则是战前便以‘对北地进行战后重建’的名义抵达北地,如今也已经踏足河套的少府匠人、官奴,热火朝天的修筑城墙。
在得到河南地之后,汉家除了早早定下‘朔方’的郡名之外,同时也为这座才刚打好地基的临河城池起好了名字。
博望城。
且不提这‘博望’二字,究竟含有怎样的含义,又或是华夏民族的期盼;
单就是当今天子荣曾经的太子私苑:博望苑,就足以说明一切。
对于博望城,汉家——尤其是当今天子荣,抱以极大的期待!
很显然,在河套已经到手的情况下,这极大期待,不可能仅仅只是‘守住河套门户’这么简单……
战事稳步推进,同一时间的长安城,却是一副莫名诡异的安静。
倒不是有人,想要在如此关头浑水摸鱼,搞点见不得人的勾当;
而是战事的紧张,实在是过于顺利、过于出乎长安朝堂内外的预料了。
——那可是河南地!
秦得之,便使游牧之民不敢南下牧马,汉失之,便受战马奇缺之苦凡五十余年,至今都抬不起头的宝地!
如此宝地,匈奴人不说是以举国之力守护,也总该驻扎重兵,并时刻防备汉家的图谋?
但实际情况却是:数百年前的那句‘生于忧患,死于安乐’,以及‘好战必亡,忘战必危’,在这场河套战役之后,达到了含金量顶峰。
匈奴人,实在是在河套,过了太久太久的安稳日子;
以至于他们都忘了河套,并不曾被匈奴单于庭滴血认主。
匈奴人,在汉家的再三退让、多年忍辱负重下,过了太多太多年的太平日子。
以至于他们,都忘记了短短几十年前,同样是汉人的另一个王朝,将他们,乃至于另外两大霸主:东胡、月氏,打的根本不敢隔着大幕而难忘,只得龟缩漠北,茹毛饮血。
作为游牧文明政权,匈奴人当然武德昌盛。
但对于汉家、对于华夏民族,匈奴人,早就失去了本该怀有的戒备,以及足够的战略重视。
也是直到这个时候,长安街头巷尾,再也没人说太宗孝文皇帝、先孝景皇帝——乃至更早的太祖高皇帝、吕太后,是对外软弱、没有血性了。
河套,就是汉家历代先皇忍辱负重,不惜以和亲虚与委蛇,逐步麻痹匈奴人的神经,所最终结出的果实。
委屈、谩骂、指责,是由历代先皇承受的;
依次麻痹敌人,并最终一举夺回河套,是当今刘荣一手操办的。
但绝对不会有人说:河套之功,独在当今刘荣。
甚至就连刘荣自己,也同样如此。
至于充斥着长安城上空,乃至朝堂内外的诡异沉寂,刘荣也只是感怀不已,唏嘘不止。
如果说过去这几十年,匈奴人是日子过的太好,以至于忘了有一个名为‘汉人’的强大敌人;
那汉家上下君民,则是在过去这几十年,受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苦难,以至于都忘了自己是天汉贵胄、诸夏子民。
——匈奴胡骑不可力敌,敌来不可出城迎敌的意识,已经深入汉家上下君臣的灵魂深处!
至于主动出塞,主动发起攻击,更是令如今汉家上下官僚贵族、苍生黎庶,都感到骇人听闻的事。
在最开始,天下人都以为此战,和年初的朝那塞一战一样,是一场单纯的马邑保卫战。
守住马邑,就算赢了;
守不住马邑,那就退守楼烦,亦或是更南的平城,也总归不算输太多。
等北地方向传回消息,说汉军西出朝那塞,渡大河、谋河套之时,天下人无不瞠目结舌,语结无措。
什么鬼!
我汉家战马奇缺,骑军遥遥无期,怎能如此兵行险着,主动出塞?!
朝堂之上,更是冒出了不知多少老学究、老顽固,指着刘荣的鼻子,骂一些‘昏君祸国’‘累死三军’之类的脏话。
没人想过此战,汉家真的能打下河套;
大家都觉得这个战略布置,实在是昏聩到了一定程度,无疑是以卵击石,蚍蜉撼树!
绝大多数人都认为,此战最好的结果,是汉军在河套没有遭受太大损失,并顺利退回了朝那塞。
如果可以顺便绘制一些地图,了解一下河套地区的地形地貌,就已经能算得上是意外之喜了。
至于最差的结果,根本没人敢想。
——出塞作战的部队,难道没有全军覆没的可能吗?
很有可能!
步兵集群,在草原,在开阔地形,被灵活的骑兵骑军咬住,又举目无援,孤军奋战;
怎么看,都怎么像是要被全歼的架势。
甚至就连北地方面军在塞外被全歼,汉家一战而失十数万战卒,都还不是全部损失,还仅仅只是开始!
一旦北地方面军在塞外被全歼,那匈奴人必定会顺势进攻朝那塞!
而后,便大概率是太宗皇帝十四年,那场动摇汉家国本的战争的复刻版。
所有人都这么想。
除了朝堂之上,不到一半的了解内由,又或是知晓兵事、了解汉家目前的军事实力的官员、勋贵——其他所有人,几乎都是这么想的。
朝堂之上,功勋们惴惴不安,官员们牢骚不断;
街头巷尾,闲人懒汉们更是破口大骂,指点江山。
至于关东,才刚安稳下来的宗亲诸侯们,也都纷纷动起了别样的心思。
所有人都觉得主动出击,以步兵去主动进攻骑兵、从边墙主动出塞,跑到游牧之民的地盘打仗,无异于自掘坟墓。
于是,当河套易主,汉家彻底夺回河南地的好消息传回时,所有人都亚麻呆住了。
啊?
啊???
就这么,打下来了?
甚至都没怎么打,就,拿回河南地了?
匈奴人什么时候,变得如此不堪一击?
我汉家,又是何时变得如此强大,居然能如此轻而易举之间,便夺回那片决定着东亚怪物房骑兵战力归属的河南地?
而这种诡异的氛围,便一直持续至今。
直到今日,长安朝堂都草拟好‘于河南地设立朔方郡’的方案,汉家上上下下,依旧还有些没反应过来。
大家都懵懵的,愣愣的;
好像在做梦。
又怎么都无法从这美妙,却也完全‘不合逻辑’的美梦中转醒。
却也有人,在所有人都被这‘天降惊喜’砸的晕头转向时,一边为此而感到振奋、喜悦,一边又迎来自己原本暗淡无关的人生中,最为重要的一处转折……
“阿姊,近来可好?”
长安尚冠里,平阳侯府。
作为侯府奴生子、歌舞姬,卫子夫原本的住处,是在侯府后院东南角,毗邻茅厕的一处大茅屋。
那茅屋,也并非独属卫子夫,而是住着和卫子夫同等身份的十几二十个妙龄女子。
以中间为道路,两侧砌有矮泥榻的大通铺,二十来个十岁出头的小女孩,却如糙汉子般挤在一起住。
而今,卫子夫却住进了一座独属于自己的小瓦房。
不大,但独属于卫子夫一人……
“一切都好。”
···
“可曾去看过母亲了?”
听闻弟弟卫青的问候,卫子夫强挤出一抹笑意,紧接着便提醒起弟弟,也要去看看母亲。
——近些年来,母亲的身体并不很好。
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,早年落下的病根,更是时时刻刻折磨着母亲老迈、残破的身躯。
作为奴仆,母亲从不曾有坐月子、养身子的福分;
偏又一胎接着一胎,从二十来岁一直生育至今,便是在怎办结实的身子骨,也早就被早年的病根,给摧残的不成样子。
作为出生在侯府的奴生子,卫子夫虽然年纪还小,却也懂得了许多人世间的腌臜、龃龉。
在侯府内的待遇突然发生改变,卫子夫也大致能猜测到自己,或许是被某个大人物看中了。
并非侯爷突然通了人性,打算好好对待侯府的下人、奴仆们;
而是侯爷念在那个大人物的颜面,才决定替那位大人物好生养着自己,一直到能嫁人——或者说,是能用肉体取悦那位大人物的年纪。
对于这样的命运,卫子夫并没有感到什么悲哀、唏嘘之类。
——对于自己的命运,卫子夫早有预料。
而如今这条路,甚至可以说是曾经,卫子夫连想都不敢想的美妙结局。
作为奴生子,能给某个大人物做姬妾——甚至哪怕是一夜承欢,也比在这侯府,成为母亲那样的侍妾,要好上太多太多。
现如今,卫子夫脑子里,已经不怎么想有关自己的事了。
——老老实实在侯府住着,女红的技艺学着,等着长大,被那位大人物接走便是。
真正让卫子夫感到担忧、挂念的,是已经重病卧榻的母亲,以及这些个还没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。
一声‘可能去探望过母亲了?’,却见弟弟卫青略有些羞涩的挠了挠头,卫子夫当即便心下了然。
深吸一口气,叹息间,将弟弟卫青的手轻轻拉过;
而后便是一副苦口婆心的口吻,为弟弟谋划起未来的人生道路。
“姊姊我,许是要有大福气了。”
“再不三五年,便或要被某位君侯接走,为姬为妾。”
“——能让咱们这位平阳侯,都如此小心对待的,怕也不是什么寻常千八百户食邑的闲散君侯。”
“到了那时,阿青若能有些出息,我也好在那位君侯面前引荐一二,好为阿青谋条出路……”
卫子夫当然知道,如今的卫青,不知由于什么缘故,得到了当今天子的接见,并留在了宫中。
但作为这个时代身份最低微、最底层的人——尤其还是女人,卫子夫同样清楚:有些东西,并非是什么身份的人,都能拥有的。
就好比弟弟卫青,十岁出头的年纪,便得了当朝天子赏识;
侯府的仆人们都说,卫子夫如今的待遇,是沾了弟弟的光,平阳侯是看在当今天子对卫青的青睐,才提高了卫子夫这一大家子的待遇。
但卫子夫很清楚:弟弟卫青,且不说有多大本事——就算真有能让当今天子赏识的本事,单一个奴生子的身份,也足以让卫青穷极一生,都看不见未央宫宫门之内的只砖片瓦。
这,是一个讲究血脉、讲究身份地位的时代。
而奴生子之所以卑贱,是因为他们的血脉不被承认,属于‘无祖无后’之人。
所以,卫子夫大致推断:弟弟能得到当今天子召见,大抵是因为皇后的缘故。
许是陛下一时兴起,要找侯府的人问问有关皇后的事之类。
也正是因此,卫子夫同样清楚:弟弟卫青,是不能这样被留在宫里的。
——皇宫里,那可是随便拎一个人出来,就能扯上开国元勋家族,更甚至直接就是刘氏宗亲皇室的地方!
弟弟一介奴生子,如何能待在那样一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?
德不配位,反受其害!
与其让弟弟待在那么一与身份不符,且注定无法拥有未来的地方,还不如找个机会出空,攀上某一家功侯,给某位侯爵家的少君侯做亲兵,拿命拼出来一个前程,才来的更实际一些。
对于卫青,乃至所有的兄弟姐妹,卫子夫的期盼都不算太高。
恢复民籍,重新成为‘人’,而非属于他人的财富,已经是卫子夫穷尽想象力,所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未来。
只是要想达成这一目标,需要机遇,需要勇气,甚至很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,才能为后代争取到这样一个机会……
“阿姊……”
“咳咳;”
“阿姊……”
“平阳侯,难道不曾与阿姊说起吗?”
正皱眉思虑间,弟弟卫青面色古怪的一问,只惹得卫子夫眉头陡然一皱。
——莫非,另有变数?!
却见卫青若有所思的低下头,思考片刻,才压低声线道:“平阳侯礼待阿姊,其实,是因为陛下有所交代……”
“陛下还跟我说,我能入宫侍奉于陛下左右,甚至还能看到石渠阁的兵书,也是陛下念在阿姊的面上……”
“陛下还说,弟弟将来,是要做外戚的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