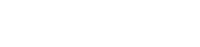北地-河套战场意料之外的进展顺利,却并没能让汉家上下将帅放松心中,一直紧绷着的那根线。
好戏,才刚刚开始。
战役第一步,汉家在马邑牵扯住匈奴单于庭主力,同时奇袭夺去河套地区的战略预案,固然是取得了成功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到这一步,汉家已经就大获全胜了。
——河套的地形、地势,非常独特!
本身地势较高,相较于东侧的汉北地、陇右地区,更是拥有肉眼可见的地势压制!
但在现如今,汉家初步掌控了河套地区之后,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
过去,河套的匈奴部族需要防备的,是东、东南方向的汉室,以及西、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。
前者在过去几十年来,始终处于战略防守姿态,若是来犯,更是从低处向高处、以步兵集群向骑兵集群发起进攻。
所以,自从秦二世而亡,让曾经的匈奴部幸运得以占据河套之后,匈奴人从来都不曾担心过这片塞外明珠,会重新回到汉人手中。
除非匈奴人主动割让,否则,河套几乎不可能被汉人武力夺回。
这也是为什么此番,汉室在河套战场的进展如此顺利——甚至是过分顺利的主要原因。
至于另外一个方向,即河套西、西北侧的河西走廊,就更不想要匈奴人担心了。
——曾经的河西走廊,可是月氏人的地盘!
现如今,月氏人在哪里?
草原有传闻,说月氏人最后残存的余孽,在那场大战之后一路东逃,都逃到极西之地:大宛国以西了!
至于曾属于月氏人的河西地,更是成为了匈奴人毋庸置疑的控制区域,以及河套地区与西域七十二国往来的通道。
所以在过去,匈奴人在河套地区,只需要象征性的防备东、东南方向的汉人;
考虑到汉人在过去几十年来,都一直自顾不暇,连国境线都守不住,这点象征性的防备,其实也多少显得有些没必要了。
但现在,河套易主!
占据河套地区的,成为了曾经最无法让匈奴人提起防备之心的宿敌:汉家!
拥有了河套之后,汉家需要构筑的防线长度、纵深,就不再是曾经,拥有河套的匈奴人那般轻松、惬意,甚至形同叙述了。
——在将河套地区并入大汉版图之后,这片地区与汉家的接壤部分,主要是东、南两个方向。
河套东部,是上郡,以及北地郡的部分郡界;
东南部,则是北地郡的大半郡界,以及部分陇右郡界。
河套正南,则是黄土高坡。
这就意味着在拥有河套之后,汉家需要在河套西侧的河西走廊方向,西北、正被侧的幕南方向,以及东北侧,构筑起一条含盖河套半个周长的防线。
尤其是东北方向,或早或晚——最晚不超过入冬,必将会迎来单于庭主力的拼死反扑!
河套,打是打下来了。
但正所谓:打江山容易,守江山难。
要想将河套实打实吃下来,消化下去,汉家——北地方面军首先要在今年入冬之前,和回援的单于庭主力来过一场!
不同于中原,凡战略要地,多有山、水天险,城防要塞作为依凭——草原上的防御工事,几乎只有硕鼠洞穴,可以作为天然的陷马坑。
除了那条包裹住大半个河套的大河,北地方面军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凭的防御工事。
以几乎全步兵,在一望无际,没有任何掩体、防御工事的草原开阔地,面对数以十万计的骑兵集群……
怎么说呢;
无论是这个时代,还是往后千百年,有胆子敢这么干的,也就是民风彪悍,至刚至烈的汉人了。
河套这边看似是一切顺利,甚至是‘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’,但实际上,真正棘手的事还没来临。
河套战场尚且如此,马邑主战场,情况自然是更好不到哪里去……
“五日了……”
“河南地若果真易主,那距离今日,已经过去了足足五日。”
“早着今明两日,至迟,也不过三两日内——军臣那老儿,便必定会收到消息。”
“紧接着,便是单于庭大军无所不用其极,要从马邑溜走,以回援河南地……”
代北雁门郡,马邑北城墙头。
这场守城战才刚打了五日,马邑的整面北城墙,就已经被双方的鲜血所染红。
——此来马邑,匈奴人,显然并不是装装样子,摆出一副‘我很牛逼’的架子说事儿;
此战,匈奴人是下定了决心,要证明自己真的很牛逼!
下定了决心,要证明年初北地一战,根本无法说明如今的汉匈双方,不再是以匈奴为‘兄长’,汉家为小弟。
虽然是以骑兵为主,确实不擅长攻城,但匈奴人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拿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手段。
什么挖墙脚、挖地道,又或是收买马邑城内的商贾、奸贼,妄图里应外合骗开城门;
又或是不远百十里,大费周折的从远处砍来木材,现场建造云梯、冲车等攻城器械。
若是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这一幕,怕是要以为此番,匈奴人是要拼举国之力,也要攻下小小一座马邑!
好在程不识,还不至于被这点场面给吓到。
想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,吴王刘濞的叛军主力久攻梁都睢阳而不下,便转头攻打起了龟缩下邑的周亚夫所部。
当时的场面,可比这场马邑保卫战大多了!
吴王刘濞一声令下,睢阳以东三百里,凡是能作木工之用的木材,都在数日之内被砍伐殆尽!
情况最严峻的时候,周亚夫驻守,并由程不识前线指挥的下邑城头,那就是梯子挨着梯子——整面城墙外,都被叛军搭出了一张‘梯网’!
至于云梯、箭楼,还有投石机、冲车——乃至于床弩,都在那场下邑保卫战,出现在了下邑外!
相比起那一战,眼前这一幕、这一场以匈奴人作为进攻方的马邑保卫战,看上去是浩浩荡荡几十万人来犯,但实际上,却根本吓不到程不识。
这四五日打下来,程不识应对自如,可谓是如鱼得水;
城外的匈奴人,除了最开始那两日的三板斧,多少还对马邑造成了些许威胁,近两日的攻势,已经是连马邑城头都上不来了。
至于那染红整面马邑北城墙外的血污,多是匈奴人驱赶上前,负责吸引火力的奴隶炮灰,以及马邑城头,偶尔偶尔出现的倒霉蛋,不幸被城外飞来的流矢射中所致。
守一座马邑,对程不识而言不在话下。
至于真正让程不识头疼的点,却是让身后百里开外,率军驻守楼烦县,作为马邑后援的郅都,在战时冒险来到马邑,出现在了北城墙的城头、出现在了程不识的身旁……
“此战,将军守住马邑,已然是无过。”
“便说是略有小功,也没人能挑出理来。”
“至于强留下单于庭主力,给河南地留出足够的时间……”
说着,郅都神情满是凝重的咬紧牙槽,深吸一口气,才面色严肃的抬起头,看向程不识那张略带萧瑟的侧脸。
“将军传令我部,出楼烦西北,于赵长城口内扎营。”
“——将军的打算,我就算不甚知之,却也能猜到一二。”
“只是如此一来,万一……”
“真的值得吗?”
“此战,真的值得将军拼上身家性命,乃至于一生清誉,去赌那么一个可能性吗?”
···
“万一将军猜错了呢?”
“万一,军臣老儿不上当,仍旧执意退兵回援河南地,那将军该当如何?”
“更有甚者,万一军臣老儿破釜沉舟,果真就一路南下,以至于北方糜烂!”
“将军,又如何担待得起?”
言辞颇带恳切的说出这番话,见程不识仍不为所动,仍是一副萧瑟的模样,负手凝望向城墙外,再次入潮水般退去的匈奴人,郅都心头不由又是一沉。
正要开口再劝,却见程不识悠然发出一声长叹,缓缓伸出虚握成拳的手,轻轻砸在了墙垛之上。
良久,方悠悠开口道:“值不值的,没人知道。”
“只有做了,有了结果,才能看出这么做值不值得。”
“——于我个人而言,这么做,风险极大,收益,却几可谓无。”
“但于我汉家而言……”
···
······
心绪重重的止住话头,程不识的目光,不由落在了城墙外,那些正优哉游哉收敛着匈奴兵卒尸体,再顺手牵走无主马匹的匈奴人身上。
就说此刻,若问程不识最想做什么,那无疑是率部冲出城外,将那些尸体的首级阁下、将那些丧主哀鸣的无主之马牵回来!
但程不识不能这么做。
因为一旦这么做了,匈奴人就会得到可乘之机,汉军将士就会失去城墙的庇护,将不得不在旷野平原,与匈奴人的骑兵集群,打一场平原遭遇战。
为了大局。
程不识明明有这个冲动,却不得不按捺下这个冲动,是为了顾全大局。
同样的道理:此战,程不识最原始的冲动,是率部冲出城外,和城外的单于庭主力,甩开膀子来过一场!
以现有的兵力,以及自己的军事才能,程不识有信心,以极大的伤亡为大家,对城外的单于庭主力,也造成无以言表的重大打击!
但程不识不能这么做。
为了顾全大局,程不识必须耐住性子,死守马邑。
麾下将士死了三千、五千,上了成千上万,城外的首级却连一颗都割不回来;
程不识依旧只能忍。
一切,都只为了顾全大局……
“陛下曾说,太祖高皇帝曾托梦于陛下:至多十五年后,我汉家,便将有一兵主降世。”
“再十年,更会有一天之骄子,狭惊世之才,以未冠之年,为我汉家扫平胡虏,马踏龙城,执匈奴单于之君长,以问罪于太、高二庙……”
冷不丁一阵低语,程不识终是缓缓侧过身;
正对向身前的郅都,那张常年看不出表情变化的面摊脸上,竟难得涌现出些许笑容。
只是不同于郅都这一生,从其他人脸上见过的笑容——此刻,挂在程不识面庞之上的笑容,竟是让郅都怎么都看不透。
像是苦涩;
像是渴望;
像是释怀?
又分明,带着些英勇就义般的决绝……
“我意,已决。”
“为保全大局——为了强留单于庭主力,继续滞留于雁门一代,我,必须这么做。”
“也只能这么做……”
···
“如果军臣依旧决意离去,那此战,我部死守马邑的功劳,便会因为我接下来的举动,而被消磨的烟消云散。”
“若军臣中计,那最好的结果,也不过是你我二人,合力将军臣的主力,拦在了赵长城以北。”
“——以丢失一座马邑的代价,为河南地,留出足够的时间。”
“但无论成败——无论军臣是走是留,无论是被我二人成功抵挡,还是被他军臣攻入代地,以至于北墙糜烂;”
“你我二人,都绝无可能有半点功劳……”
说到此处,程不识终是缓缓抬起头,掌心向上,对郅都做了个类似‘请’的手势。
只那双目灼灼,落在郅都依旧满带着凝重的面庞之上,竟不带丝毫迟疑,和摇摆不定……
“我打算做一件大事~”
“这件事,真的很大,很大。”
“——无论成败,都绝对没有人会称赞我们。”
“若成,那你我二人,也不过自此泯然众人;”
“若计不成,更是会为你我二人——乃至于程、郅二氏,留下千古不消之骂名!”
“郅中郎,尚勇武否?”
尚勇武否?
只此一问,便让历经岁月洗礼,饱经宦海沉浮,早已不复年少热血的郅都,回到了梦开始的时候。
——中郎郅都,悍勇无双,若从军,必为战克之将、国之爪牙!
“尚勇武否?”
“尚,勇武否……”
如是呢喃着——反复呢喃着,郅都终是魂不守舍的走下墙头,渐行渐远。
虽然没有答复,但郅都的行动,却给了程不识最通俗易懂的答案。
——天子荣新元元年,秋八月二十六;
雁门太守程不识下令:减兵增灶,徐徐退离马邑!
秋八月二十八,马邑战场的汉军,彻底弃守马邑,放开了赵长城的入口门户!
同一日,满怀不解走入马邑城门的匈奴单于:挛鞮军臣,也终于受到了来自河套的消息。
河套易主;
右贤王本部栖息地:南池,已为汉家饮马之所……
好戏,才刚刚开始。
战役第一步,汉家在马邑牵扯住匈奴单于庭主力,同时奇袭夺去河套地区的战略预案,固然是取得了成功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到这一步,汉家已经就大获全胜了。
——河套的地形、地势,非常独特!
本身地势较高,相较于东侧的汉北地、陇右地区,更是拥有肉眼可见的地势压制!
但在现如今,汉家初步掌控了河套地区之后,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
过去,河套的匈奴部族需要防备的,是东、东南方向的汉室,以及西、西北方向的河西走廊。
前者在过去几十年来,始终处于战略防守姿态,若是来犯,更是从低处向高处、以步兵集群向骑兵集群发起进攻。
所以,自从秦二世而亡,让曾经的匈奴部幸运得以占据河套之后,匈奴人从来都不曾担心过这片塞外明珠,会重新回到汉人手中。
除非匈奴人主动割让,否则,河套几乎不可能被汉人武力夺回。
这也是为什么此番,汉室在河套战场的进展如此顺利——甚至是过分顺利的主要原因。
至于另外一个方向,即河套西、西北侧的河西走廊,就更不想要匈奴人担心了。
——曾经的河西走廊,可是月氏人的地盘!
现如今,月氏人在哪里?
草原有传闻,说月氏人最后残存的余孽,在那场大战之后一路东逃,都逃到极西之地:大宛国以西了!
至于曾属于月氏人的河西地,更是成为了匈奴人毋庸置疑的控制区域,以及河套地区与西域七十二国往来的通道。
所以在过去,匈奴人在河套地区,只需要象征性的防备东、东南方向的汉人;
考虑到汉人在过去几十年来,都一直自顾不暇,连国境线都守不住,这点象征性的防备,其实也多少显得有些没必要了。
但现在,河套易主!
占据河套地区的,成为了曾经最无法让匈奴人提起防备之心的宿敌:汉家!
拥有了河套之后,汉家需要构筑的防线长度、纵深,就不再是曾经,拥有河套的匈奴人那般轻松、惬意,甚至形同叙述了。
——在将河套地区并入大汉版图之后,这片地区与汉家的接壤部分,主要是东、南两个方向。
河套东部,是上郡,以及北地郡的部分郡界;
东南部,则是北地郡的大半郡界,以及部分陇右郡界。
河套正南,则是黄土高坡。
这就意味着在拥有河套之后,汉家需要在河套西侧的河西走廊方向,西北、正被侧的幕南方向,以及东北侧,构筑起一条含盖河套半个周长的防线。
尤其是东北方向,或早或晚——最晚不超过入冬,必将会迎来单于庭主力的拼死反扑!
河套,打是打下来了。
但正所谓:打江山容易,守江山难。
要想将河套实打实吃下来,消化下去,汉家——北地方面军首先要在今年入冬之前,和回援的单于庭主力来过一场!
不同于中原,凡战略要地,多有山、水天险,城防要塞作为依凭——草原上的防御工事,几乎只有硕鼠洞穴,可以作为天然的陷马坑。
除了那条包裹住大半个河套的大河,北地方面军没有其他任何可以依凭的防御工事。
以几乎全步兵,在一望无际,没有任何掩体、防御工事的草原开阔地,面对数以十万计的骑兵集群……
怎么说呢;
无论是这个时代,还是往后千百年,有胆子敢这么干的,也就是民风彪悍,至刚至烈的汉人了。
河套这边看似是一切顺利,甚至是‘已经完成了最重要的任务’,但实际上,真正棘手的事还没来临。
河套战场尚且如此,马邑主战场,情况自然是更好不到哪里去……
“五日了……”
“河南地若果真易主,那距离今日,已经过去了足足五日。”
“早着今明两日,至迟,也不过三两日内——军臣那老儿,便必定会收到消息。”
“紧接着,便是单于庭大军无所不用其极,要从马邑溜走,以回援河南地……”
代北雁门郡,马邑北城墙头。
这场守城战才刚打了五日,马邑的整面北城墙,就已经被双方的鲜血所染红。
——此来马邑,匈奴人,显然并不是装装样子,摆出一副‘我很牛逼’的架子说事儿;
此战,匈奴人是下定了决心,要证明自己真的很牛逼!
下定了决心,要证明年初北地一战,根本无法说明如今的汉匈双方,不再是以匈奴为‘兄长’,汉家为小弟。
虽然是以骑兵为主,确实不擅长攻城,但匈奴人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,拿出了自己能想到的所有手段。
什么挖墙脚、挖地道,又或是收买马邑城内的商贾、奸贼,妄图里应外合骗开城门;
又或是不远百十里,大费周折的从远处砍来木材,现场建造云梯、冲车等攻城器械。
若是不明真相的人看到这一幕,怕是要以为此番,匈奴人是要拼举国之力,也要攻下小小一座马邑!
好在程不识,还不至于被这点场面给吓到。
想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,吴王刘濞的叛军主力久攻梁都睢阳而不下,便转头攻打起了龟缩下邑的周亚夫所部。
当时的场面,可比这场马邑保卫战大多了!
吴王刘濞一声令下,睢阳以东三百里,凡是能作木工之用的木材,都在数日之内被砍伐殆尽!
情况最严峻的时候,周亚夫驻守,并由程不识前线指挥的下邑城头,那就是梯子挨着梯子——整面城墙外,都被叛军搭出了一张‘梯网’!
至于云梯、箭楼,还有投石机、冲车——乃至于床弩,都在那场下邑保卫战,出现在了下邑外!
相比起那一战,眼前这一幕、这一场以匈奴人作为进攻方的马邑保卫战,看上去是浩浩荡荡几十万人来犯,但实际上,却根本吓不到程不识。
这四五日打下来,程不识应对自如,可谓是如鱼得水;
城外的匈奴人,除了最开始那两日的三板斧,多少还对马邑造成了些许威胁,近两日的攻势,已经是连马邑城头都上不来了。
至于那染红整面马邑北城墙外的血污,多是匈奴人驱赶上前,负责吸引火力的奴隶炮灰,以及马邑城头,偶尔偶尔出现的倒霉蛋,不幸被城外飞来的流矢射中所致。
守一座马邑,对程不识而言不在话下。
至于真正让程不识头疼的点,却是让身后百里开外,率军驻守楼烦县,作为马邑后援的郅都,在战时冒险来到马邑,出现在了北城墙的城头、出现在了程不识的身旁……
“此战,将军守住马邑,已然是无过。”
“便说是略有小功,也没人能挑出理来。”
“至于强留下单于庭主力,给河南地留出足够的时间……”
说着,郅都神情满是凝重的咬紧牙槽,深吸一口气,才面色严肃的抬起头,看向程不识那张略带萧瑟的侧脸。
“将军传令我部,出楼烦西北,于赵长城口内扎营。”
“——将军的打算,我就算不甚知之,却也能猜到一二。”
“只是如此一来,万一……”
“真的值得吗?”
“此战,真的值得将军拼上身家性命,乃至于一生清誉,去赌那么一个可能性吗?”
···
“万一将军猜错了呢?”
“万一,军臣老儿不上当,仍旧执意退兵回援河南地,那将军该当如何?”
“更有甚者,万一军臣老儿破釜沉舟,果真就一路南下,以至于北方糜烂!”
“将军,又如何担待得起?”
言辞颇带恳切的说出这番话,见程不识仍不为所动,仍是一副萧瑟的模样,负手凝望向城墙外,再次入潮水般退去的匈奴人,郅都心头不由又是一沉。
正要开口再劝,却见程不识悠然发出一声长叹,缓缓伸出虚握成拳的手,轻轻砸在了墙垛之上。
良久,方悠悠开口道:“值不值的,没人知道。”
“只有做了,有了结果,才能看出这么做值不值得。”
“——于我个人而言,这么做,风险极大,收益,却几可谓无。”
“但于我汉家而言……”
···
······
心绪重重的止住话头,程不识的目光,不由落在了城墙外,那些正优哉游哉收敛着匈奴兵卒尸体,再顺手牵走无主马匹的匈奴人身上。
就说此刻,若问程不识最想做什么,那无疑是率部冲出城外,将那些尸体的首级阁下、将那些丧主哀鸣的无主之马牵回来!
但程不识不能这么做。
因为一旦这么做了,匈奴人就会得到可乘之机,汉军将士就会失去城墙的庇护,将不得不在旷野平原,与匈奴人的骑兵集群,打一场平原遭遇战。
为了大局。
程不识明明有这个冲动,却不得不按捺下这个冲动,是为了顾全大局。
同样的道理:此战,程不识最原始的冲动,是率部冲出城外,和城外的单于庭主力,甩开膀子来过一场!
以现有的兵力,以及自己的军事才能,程不识有信心,以极大的伤亡为大家,对城外的单于庭主力,也造成无以言表的重大打击!
但程不识不能这么做。
为了顾全大局,程不识必须耐住性子,死守马邑。
麾下将士死了三千、五千,上了成千上万,城外的首级却连一颗都割不回来;
程不识依旧只能忍。
一切,都只为了顾全大局……
“陛下曾说,太祖高皇帝曾托梦于陛下:至多十五年后,我汉家,便将有一兵主降世。”
“再十年,更会有一天之骄子,狭惊世之才,以未冠之年,为我汉家扫平胡虏,马踏龙城,执匈奴单于之君长,以问罪于太、高二庙……”
冷不丁一阵低语,程不识终是缓缓侧过身;
正对向身前的郅都,那张常年看不出表情变化的面摊脸上,竟难得涌现出些许笑容。
只是不同于郅都这一生,从其他人脸上见过的笑容——此刻,挂在程不识面庞之上的笑容,竟是让郅都怎么都看不透。
像是苦涩;
像是渴望;
像是释怀?
又分明,带着些英勇就义般的决绝……
“我意,已决。”
“为保全大局——为了强留单于庭主力,继续滞留于雁门一代,我,必须这么做。”
“也只能这么做……”
···
“如果军臣依旧决意离去,那此战,我部死守马邑的功劳,便会因为我接下来的举动,而被消磨的烟消云散。”
“若军臣中计,那最好的结果,也不过是你我二人,合力将军臣的主力,拦在了赵长城以北。”
“——以丢失一座马邑的代价,为河南地,留出足够的时间。”
“但无论成败——无论军臣是走是留,无论是被我二人成功抵挡,还是被他军臣攻入代地,以至于北墙糜烂;”
“你我二人,都绝无可能有半点功劳……”
说到此处,程不识终是缓缓抬起头,掌心向上,对郅都做了个类似‘请’的手势。
只那双目灼灼,落在郅都依旧满带着凝重的面庞之上,竟不带丝毫迟疑,和摇摆不定……
“我打算做一件大事~”
“这件事,真的很大,很大。”
“——无论成败,都绝对没有人会称赞我们。”
“若成,那你我二人,也不过自此泯然众人;”
“若计不成,更是会为你我二人——乃至于程、郅二氏,留下千古不消之骂名!”
“郅中郎,尚勇武否?”
尚勇武否?
只此一问,便让历经岁月洗礼,饱经宦海沉浮,早已不复年少热血的郅都,回到了梦开始的时候。
——中郎郅都,悍勇无双,若从军,必为战克之将、国之爪牙!
“尚勇武否?”
“尚,勇武否……”
如是呢喃着——反复呢喃着,郅都终是魂不守舍的走下墙头,渐行渐远。
虽然没有答复,但郅都的行动,却给了程不识最通俗易懂的答案。
——天子荣新元元年,秋八月二十六;
雁门太守程不识下令:减兵增灶,徐徐退离马邑!
秋八月二十八,马邑战场的汉军,彻底弃守马邑,放开了赵长城的入口门户!
同一日,满怀不解走入马邑城门的匈奴单于:挛鞮军臣,也终于受到了来自河套的消息。
河套易主;
右贤王本部栖息地:南池,已为汉家饮马之所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