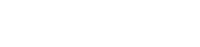在这个时代,黄河还不是‘黄’河,而是华夏民族公认的母亲河:大河。
在黄河——即大河上游,后世的黄土高原,如今尚还是成片的草原,乃至丛林。
大河之水尚还清澈;
与后世的‘黄河’相比,这个时代的大河,可谓是有百般不同。
唯一与后世‘黄河’如出一辙的,是那波涛汹涌的巨大水流,单就是让人听到那水流行动,便不免会生成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。
——怕水,是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类生物,源自于灵魂的本能恐惧。
即便生存离不开水,甚至文明出现后的农耕、畜牧也都离不开水,人类对水资源,都始终怀揣着最高的敬畏。
因为早在远古,乃至原始时期,大自然的残酷便将‘水’的恐怖,纂刻进了人类的灵魂,乃至基因传续之中。
而在这个时代的华夏大地,除去东、南沿海地区,是对海洋怀揣最高敬畏外,长期居住在内陆的人——无论是中原的华夏农耕文明,还是草原上的游牧文明,都是对大河怀着最高的敬畏之心。
在关中东门户:函谷关外,东西流向的大河,让函谷关成为了当今天下,乃至华夏历史数一数二的雄关。
即便到了后世,雄关函谷,也依旧享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美誉。
在辽阔的关东地区,大河的各支脉,更是滋润了那片相较于关中、巴蜀更贫瘠的土地,养活了大半个华夏文明。
甚至于草原。
甚至于游牧民族前后数千年的栖息地:草原,也依旧是靠这条华夏文明的母亲河,才拥有了第一块极度适宜的牧场。
——河套。
也被如今的汉人、被如今的华夏文明称之为:河南地。
其地风景秀丽,虽说不上四季如春,也至少是气候适宜;
即便到了凛冬腊月,也总还能让住在毡帐里的游牧民族,不必担心一觉睡去,便要与世长辞。
时值秋八月下旬,大河依旧波涛汹涌,草原依旧万里青绿。
并未跟随单于庭攻掠马邑,而是负责留守的幕南各部——主要是依附于右贤王,即匈奴八柱‘右四柱’的各部族,也终于忙完了一整日的忙碌。
——或是找友人,亦或是邻居部族的旧相识摔了场跤、打了场猎;
或是同自己帐中,亦或是他人,乃至其他部族的女人,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草皮。
总而言之,又是枯燥、乏味,却又无比充实、愉快的一天过去。
到了晚间,青壮们身着胡袍,腰系胡刀,齐聚于部落营地的中心地带,围坐在篝火边上。
草原今年的状况很不错。
经过去年——乃至过去几年的‘大乱斗’,无数鲜血、骨肉滋养着草原,让今年的水草格外肥美、丰盛。
牛羊都畜够了肥膘,每日挤出来的奶,都够牧民们给奴隶也分出一些!
马匹健硕非凡,撒丫狂奔小半日,都还能有力气在黄昏时分‘伺机而动’,寻个俊俏的小母马共度良宵。
牲畜尚且如此,支配并拥有着这些牲畜,且几乎不需要承担生产、劳作任务的牧民青壮,自然更是容光焕发,精神头十足!
围聚在篝火边,看着部落的女人们围着篝火翩翩起舞,牧民们也慷慨的拿出珍藏许久的肉干,就着头人难得赐下的马奶酒——大口吃肉,大口喝酒,好不快活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这样一幕,和中原农耕文明,于秋收之后大摆宴席,普天同庆是一样的。
都是一派安宁、祥和。
只是没有人注意到:恰恰是在这篝火晚会的氛围愈发热烈,月光也愈发明亮的黑夜;
在河南地与北地郡的分界线:朝那塞以西三十余里的大河东畔——在本该空无一人,亦或是本该有零星小部族扎营的大河东畔,几乎是眨眼的功夫,便不知从何窜出了数以万计的黑影!
和草原上的游牧之民——甚至任何生物都不同:他们直立行走,颇具人形!
可他们又不独自行走,而是大都两两成对,并以一根大腿粗的长木‘连’在一起。
原本应该出现的鸟叫、兽鸣,甚至于人类存在所应该发出的一切响动,都消失在了这一夜的大河东畔。
有的,只是大河水流那震耳欲聋的‘咆哮’声,以及那一道道宛若幽灵的黑影……
“再传三军!”
“——马衔枚,人衔草,任何人不得发出响动!”
“尤其是不得口吐我汉家之言!”
···
“遂营按计划行事!”
“骑甲、乙两部都尉蓄势待发,只等浮桥搭设完成,便迅速渡河!”
分明是郑重其事的军令,却仿若贼人密谋——即便是栾布身边三五步距离的将士们,也只模模糊糊听了个大概。
而后,便是栾布的将令一边口口相传,传到每一位将士耳中,同时,先遣部队:遂营都尉,也已经开始有了动作。
在这个时代,无论上游还是下游,无论是此处的河套、北地交接,还是函谷关外的关中、关东交接,横渡大河,都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事。
原因无他;
除了官方及极少数贵族,拥有足够抵抗激流、滚浪的大型船舶之外,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想要横渡大河,都只能通过羊皮筏。
说是‘筏’,其实不过是一只长宽各不注意丈,以木框为架、羊皮为面——虽可容纳三四人,却只能单人乘坐的方形漂浮物。
即便有了这羊皮筏,也不是说你就能坐进去,而后用双手划木浆划过大河,而是要紧紧握住那条横跨整条大河的绳索,一点点‘摸着绳子过河’。
很显然,大河在河南地以东的这片流域,并没有供人涉水而过的跨河绳索。
就连此刻,大军将士汇集着的地方,也是汉家花费了足足大半个月的时间,才艰难找到的水流稍缓处。
可水流相对较缓,必然就意味着相较于别处,这处的河床——即两岸间距更宽,且水更深。
也只有这样的地方——只有这般更深、更宽的河域,才能将汹涌而下的大河之水稍稍安抚下些许。
选择水流稍缓处,是不得不做的选择。
至于这么做的弊端,也是显而易见……
“禀将军!”
“遂营甲部都尉报:此处,大河两岸间距足近二百步——超过一里!”
耳边传来副官刻意压低音量的禀奏声,栾布只面色凝重的微微点下头,并没做出反应。
河宽超过一里!
足二百步!
这意味着汉军原定的一些计划,不得不做出一些发出巨大响动、极可能影响行动隐蔽性的改动。
只是栾布很清楚:事到如今,弓在弦上……
“按照原定计划,由遂营甲、乙都尉,各遣涉水司马先行渡河!”
“——渡河之后,涉水甲司马留守原地,开始搭设浮桥。”
“乙司马四散巡视,以免走漏风声!”
河宽出乎预料的宽,对于汉军此次行动最大的影响,便是浮桥的搭设工作。
根据汉家原定的行动计划,遂营都尉搭设浮桥的整个过程如下。
先以‘涉水士’,即善水之人游到对岸——游过去多少算多少。
而后,用射程、力量足够的远程武器,如建议投石器,将绑有绳索的石头投到对岸。
等石头投过去,也就等同于两岸之间,有了绳索相连。
再由先前游过去的‘涉水士’,将绑在石头上的绳索解下,并在稍远离河滩处扎下木桩,将一条条接连两岸的绳索固定住,前期工作便算是完成了。
到这一步,后续部分就容易多了。
由后续遂营部队自东岸开始,将一条条长木固定在三条横跨两岸的绳索之上,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朝着对岸铺,一直到浮桥连接两岸位置。
相对先前,游过河、投石器扔绳索等操作,这一步的危险性大大降低,只是稍繁琐了些。
而在原定计划中,负责将绳索的一头投到对岸的投石器,大致射程便是二百步。
——毕竟是建议投石器,而非攻城用的巨型投石器,二百步的射程,已然算是鬼斧神工。
只是这二百步的射程,是单只投射石头的射程。
若是石头上,再被榜上一根二百多步——足四百多米长的粗麻绳,那射程不说减半,也总归是要打些折扣……
“用床弩!”
“将绳索绑在床弩弩箭尾部,直接射到对岸!”
栾布有了决断,其余众人即便是对这一方案发出的响动有所质疑,却也无一人出言表示反对。
——没办法。
原定的投石器,那动静也不算小;
如今投石器不够用,那就用备用方案:动静更大的床弩,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说到底,减小动静,避免被对岸——被河南地沿河地区的匈奴人发觉,是此战‘尽可能去做’的事。
做到了,后续就轻松一些,做不到,后续就麻烦一些、吃力一些。
但搭设浮桥、大军渡河,却是完全没有商量的事。
总不能说怕动静太大、惊动了对岸,就取消了这次行动?
还是那句话。
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
此刻,那一辆辆被将士们合力推上前,其上搭载巨大床弩的二轮人力车,也恰恰正蓄势待发。
没有‘噗通’‘噗通’的突兀响动。
得到行动开始的指令后,涉水士们只悄无声息的在岸边下了水。
至于之后,是自由泳还是潜泳——各凭本事,反正水面上的水流声本就不小。
待游过对岸,并汇集在一起,原本各五百人,共计一千人的两支涉水司马,却只剩下不到七百人。
还没开战,这两部司马便战损超过三成。
但将士们根本没时间神伤,只得抓紧时间,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后续工作。
——分出四百人,朝着周围区域小心查探,看看有没有迷路的匈奴人在附近‘暗中观察’;
剩下三百人,则以火光朝东岸发送了信号,而后便沿着河畔走远了些,以免被即将射响的床弩射烂。
邦邦邦!
邦邦邦!
邦邦邦!!!
一阵密集的巨响,让两岸的汉军将士都下意识屏住呼吸,分明是清凉的秋叶,却不知有多少人额角冒出了汗水。
——动静太大了!
即便是隔着一条大河,将近一里的举例,还有整条河面来作为缓冲,对岸的涉水士们也还是觉得:床弩不是从对岸发出的,而是从自己耳边,或是身后三五步发出。
很快,涉水士们便反应过来,当即也投入到了四下查探、巡视之中。
过了足有两炷香的功夫,对岸才再次亮起一处转瞬即逝的火光。
继续行动!
床弩动静大了大,却也为涉水士们省了不少事,给大军省下了不少时间。
——河套地区的地势,比北地要高!
即便是不到一里的距离,大河两岸的高度,也同样差了足够数丈!
东畔的床弩射出巨矢,即便是以仰角抛射,却也还是在西畔斜扎进了泥土之中。
而且扎的及深!
涉水士们不需要再专门派几十号人拉着绳子,再挖坑、埋桩、固定绳索;
尾部绑着绳索,被床弩深深射入土里的巨矢,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固定桩。
简单检查、补充固定一番,而后便是正式开始搭设浮桥。
一根根浮木出现在河面,并一根根有序排列成平台。
期间,也还是时不时有重物落水的响动。
有时是木;
有时是人。
只是时间紧迫,无论是在河面忙碌的遂营将士,还是在河畔整装待发的作战部队,都只能为那些牺牲者默哀片刻,而后便将哀痛化作愤怒,乃至这一战最原始的勇气来源。
过了足近一个时辰,原本在月光照耀下银装素裹的河面,多出了足足十五条三五丈宽,二百余步长的浮桥。
——这些浮桥很不稳!
人踩上去,桥面会剧烈的上下浮动不说,也没个护栏、扶手之类——就是一面光秃秃的滚木浮桥。
但这,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极限。
在这个古老的时代,趁夜在大河河面,花费不到一个时辰,搭建出这样的建议浮桥,已经是极限,乃至奇迹……
“渡河!”
“骑都尉先渡,而后四散巡视戒备!”
“无论步、骑,皆不得并排而过,而当自桥中速渡!”
“天亮之前,务必在对岸扎下营盘,并完成修整!!!”
在黄河——即大河上游,后世的黄土高原,如今尚还是成片的草原,乃至丛林。
大河之水尚还清澈;
与后世的‘黄河’相比,这个时代的大河,可谓是有百般不同。
唯一与后世‘黄河’如出一辙的,是那波涛汹涌的巨大水流,单就是让人听到那水流行动,便不免会生成一股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。
——怕水,是人类在内的所有灵长类生物,源自于灵魂的本能恐惧。
即便生存离不开水,甚至文明出现后的农耕、畜牧也都离不开水,人类对水资源,都始终怀揣着最高的敬畏。
因为早在远古,乃至原始时期,大自然的残酷便将‘水’的恐怖,纂刻进了人类的灵魂,乃至基因传续之中。
而在这个时代的华夏大地,除去东、南沿海地区,是对海洋怀揣最高敬畏外,长期居住在内陆的人——无论是中原的华夏农耕文明,还是草原上的游牧文明,都是对大河怀着最高的敬畏之心。
在关中东门户:函谷关外,东西流向的大河,让函谷关成为了当今天下,乃至华夏历史数一数二的雄关。
即便到了后世,雄关函谷,也依旧享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美誉。
在辽阔的关东地区,大河的各支脉,更是滋润了那片相较于关中、巴蜀更贫瘠的土地,养活了大半个华夏文明。
甚至于草原。
甚至于游牧民族前后数千年的栖息地:草原,也依旧是靠这条华夏文明的母亲河,才拥有了第一块极度适宜的牧场。
——河套。
也被如今的汉人、被如今的华夏文明称之为:河南地。
其地风景秀丽,虽说不上四季如春,也至少是气候适宜;
即便到了凛冬腊月,也总还能让住在毡帐里的游牧民族,不必担心一觉睡去,便要与世长辞。
时值秋八月下旬,大河依旧波涛汹涌,草原依旧万里青绿。
并未跟随单于庭攻掠马邑,而是负责留守的幕南各部——主要是依附于右贤王,即匈奴八柱‘右四柱’的各部族,也终于忙完了一整日的忙碌。
——或是找友人,亦或是邻居部族的旧相识摔了场跤、打了场猎;
或是同自己帐中,亦或是他人,乃至其他部族的女人,滚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草皮。
总而言之,又是枯燥、乏味,却又无比充实、愉快的一天过去。
到了晚间,青壮们身着胡袍,腰系胡刀,齐聚于部落营地的中心地带,围坐在篝火边上。
草原今年的状况很不错。
经过去年——乃至过去几年的‘大乱斗’,无数鲜血、骨肉滋养着草原,让今年的水草格外肥美、丰盛。
牛羊都畜够了肥膘,每日挤出来的奶,都够牧民们给奴隶也分出一些!
马匹健硕非凡,撒丫狂奔小半日,都还能有力气在黄昏时分‘伺机而动’,寻个俊俏的小母马共度良宵。
牲畜尚且如此,支配并拥有着这些牲畜,且几乎不需要承担生产、劳作任务的牧民青壮,自然更是容光焕发,精神头十足!
围聚在篝火边,看着部落的女人们围着篝火翩翩起舞,牧民们也慷慨的拿出珍藏许久的肉干,就着头人难得赐下的马奶酒——大口吃肉,大口喝酒,好不快活。
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这样一幕,和中原农耕文明,于秋收之后大摆宴席,普天同庆是一样的。
都是一派安宁、祥和。
只是没有人注意到:恰恰是在这篝火晚会的氛围愈发热烈,月光也愈发明亮的黑夜;
在河南地与北地郡的分界线:朝那塞以西三十余里的大河东畔——在本该空无一人,亦或是本该有零星小部族扎营的大河东畔,几乎是眨眼的功夫,便不知从何窜出了数以万计的黑影!
和草原上的游牧之民——甚至任何生物都不同:他们直立行走,颇具人形!
可他们又不独自行走,而是大都两两成对,并以一根大腿粗的长木‘连’在一起。
原本应该出现的鸟叫、兽鸣,甚至于人类存在所应该发出的一切响动,都消失在了这一夜的大河东畔。
有的,只是大河水流那震耳欲聋的‘咆哮’声,以及那一道道宛若幽灵的黑影……
“再传三军!”
“——马衔枚,人衔草,任何人不得发出响动!”
“尤其是不得口吐我汉家之言!”
···
“遂营按计划行事!”
“骑甲、乙两部都尉蓄势待发,只等浮桥搭设完成,便迅速渡河!”
分明是郑重其事的军令,却仿若贼人密谋——即便是栾布身边三五步距离的将士们,也只模模糊糊听了个大概。
而后,便是栾布的将令一边口口相传,传到每一位将士耳中,同时,先遣部队:遂营都尉,也已经开始有了动作。
在这个时代,无论上游还是下游,无论是此处的河套、北地交接,还是函谷关外的关中、关东交接,横渡大河,都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事。
原因无他;
除了官方及极少数贵族,拥有足够抵抗激流、滚浪的大型船舶之外,这个时代绝大多数人想要横渡大河,都只能通过羊皮筏。
说是‘筏’,其实不过是一只长宽各不注意丈,以木框为架、羊皮为面——虽可容纳三四人,却只能单人乘坐的方形漂浮物。
即便有了这羊皮筏,也不是说你就能坐进去,而后用双手划木浆划过大河,而是要紧紧握住那条横跨整条大河的绳索,一点点‘摸着绳子过河’。
很显然,大河在河南地以东的这片流域,并没有供人涉水而过的跨河绳索。
就连此刻,大军将士汇集着的地方,也是汉家花费了足足大半个月的时间,才艰难找到的水流稍缓处。
可水流相对较缓,必然就意味着相较于别处,这处的河床——即两岸间距更宽,且水更深。
也只有这样的地方——只有这般更深、更宽的河域,才能将汹涌而下的大河之水稍稍安抚下些许。
选择水流稍缓处,是不得不做的选择。
至于这么做的弊端,也是显而易见……
“禀将军!”
“遂营甲部都尉报:此处,大河两岸间距足近二百步——超过一里!”
耳边传来副官刻意压低音量的禀奏声,栾布只面色凝重的微微点下头,并没做出反应。
河宽超过一里!
足二百步!
这意味着汉军原定的一些计划,不得不做出一些发出巨大响动、极可能影响行动隐蔽性的改动。
只是栾布很清楚:事到如今,弓在弦上……
“按照原定计划,由遂营甲、乙都尉,各遣涉水司马先行渡河!”
“——渡河之后,涉水甲司马留守原地,开始搭设浮桥。”
“乙司马四散巡视,以免走漏风声!”
河宽出乎预料的宽,对于汉军此次行动最大的影响,便是浮桥的搭设工作。
根据汉家原定的行动计划,遂营都尉搭设浮桥的整个过程如下。
先以‘涉水士’,即善水之人游到对岸——游过去多少算多少。
而后,用射程、力量足够的远程武器,如建议投石器,将绑有绳索的石头投到对岸。
等石头投过去,也就等同于两岸之间,有了绳索相连。
再由先前游过去的‘涉水士’,将绑在石头上的绳索解下,并在稍远离河滩处扎下木桩,将一条条接连两岸的绳索固定住,前期工作便算是完成了。
到这一步,后续部分就容易多了。
由后续遂营部队自东岸开始,将一条条长木固定在三条横跨两岸的绳索之上,一根木头一根木头朝着对岸铺,一直到浮桥连接两岸位置。
相对先前,游过河、投石器扔绳索等操作,这一步的危险性大大降低,只是稍繁琐了些。
而在原定计划中,负责将绳索的一头投到对岸的投石器,大致射程便是二百步。
——毕竟是建议投石器,而非攻城用的巨型投石器,二百步的射程,已然算是鬼斧神工。
只是这二百步的射程,是单只投射石头的射程。
若是石头上,再被榜上一根二百多步——足四百多米长的粗麻绳,那射程不说减半,也总归是要打些折扣……
“用床弩!”
“将绳索绑在床弩弩箭尾部,直接射到对岸!”
栾布有了决断,其余众人即便是对这一方案发出的响动有所质疑,却也无一人出言表示反对。
——没办法。
原定的投石器,那动静也不算小;
如今投石器不够用,那就用备用方案:动静更大的床弩,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说到底,减小动静,避免被对岸——被河南地沿河地区的匈奴人发觉,是此战‘尽可能去做’的事。
做到了,后续就轻松一些,做不到,后续就麻烦一些、吃力一些。
但搭设浮桥、大军渡河,却是完全没有商量的事。
总不能说怕动静太大、惊动了对岸,就取消了这次行动?
还是那句话。
箭在弦上,不得不发。
此刻,那一辆辆被将士们合力推上前,其上搭载巨大床弩的二轮人力车,也恰恰正蓄势待发。
没有‘噗通’‘噗通’的突兀响动。
得到行动开始的指令后,涉水士们只悄无声息的在岸边下了水。
至于之后,是自由泳还是潜泳——各凭本事,反正水面上的水流声本就不小。
待游过对岸,并汇集在一起,原本各五百人,共计一千人的两支涉水司马,却只剩下不到七百人。
还没开战,这两部司马便战损超过三成。
但将士们根本没时间神伤,只得抓紧时间,继续按照计划进行后续工作。
——分出四百人,朝着周围区域小心查探,看看有没有迷路的匈奴人在附近‘暗中观察’;
剩下三百人,则以火光朝东岸发送了信号,而后便沿着河畔走远了些,以免被即将射响的床弩射烂。
邦邦邦!
邦邦邦!
邦邦邦!!!
一阵密集的巨响,让两岸的汉军将士都下意识屏住呼吸,分明是清凉的秋叶,却不知有多少人额角冒出了汗水。
——动静太大了!
即便是隔着一条大河,将近一里的举例,还有整条河面来作为缓冲,对岸的涉水士们也还是觉得:床弩不是从对岸发出的,而是从自己耳边,或是身后三五步发出。
很快,涉水士们便反应过来,当即也投入到了四下查探、巡视之中。
过了足有两炷香的功夫,对岸才再次亮起一处转瞬即逝的火光。
继续行动!
床弩动静大了大,却也为涉水士们省了不少事,给大军省下了不少时间。
——河套地区的地势,比北地要高!
即便是不到一里的距离,大河两岸的高度,也同样差了足够数丈!
东畔的床弩射出巨矢,即便是以仰角抛射,却也还是在西畔斜扎进了泥土之中。
而且扎的及深!
涉水士们不需要再专门派几十号人拉着绳子,再挖坑、埋桩、固定绳索;
尾部绑着绳索,被床弩深深射入土里的巨矢,已经是再好不过的固定桩。
简单检查、补充固定一番,而后便是正式开始搭设浮桥。
一根根浮木出现在河面,并一根根有序排列成平台。
期间,也还是时不时有重物落水的响动。
有时是木;
有时是人。
只是时间紧迫,无论是在河面忙碌的遂营将士,还是在河畔整装待发的作战部队,都只能为那些牺牲者默哀片刻,而后便将哀痛化作愤怒,乃至这一战最原始的勇气来源。
过了足近一个时辰,原本在月光照耀下银装素裹的河面,多出了足足十五条三五丈宽,二百余步长的浮桥。
——这些浮桥很不稳!
人踩上去,桥面会剧烈的上下浮动不说,也没个护栏、扶手之类——就是一面光秃秃的滚木浮桥。
但这,已经是这个时代的极限。
在这个古老的时代,趁夜在大河河面,花费不到一个时辰,搭建出这样的建议浮桥,已经是极限,乃至奇迹……
“渡河!”
“骑都尉先渡,而后四散巡视戒备!”
“无论步、骑,皆不得并排而过,而当自桥中速渡!”
“天亮之前,务必在对岸扎下营盘,并完成修整!!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