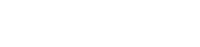举国之力,倾力而为。
话说出口,不过轻描淡写八个字;
但实际操作起来,却是一副又一副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。
——天子荣元年,秋七月初一,朝堂正式颁布政令:以少府内帑领头,相府国库从旁协助,正式在对今年年初,因战火而饱受摧残的北地郡,开启战后重建工作。
为了保证这项工作在秋收后第一时间上马,并在入冬前完成第一阶段任务,少府内帑,可以说是掏出了小半家底。
这很恐怖!
可千万不要觉得‘小半家底’四个字,放在哪里都是不起眼的数量级!
无论是封建王朝,还是后世新时代,任何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大宗货物库存,只要不再以‘百分之几’来计数,而是开始以‘几成’乃至‘小半’来形容,那就等同于海量!
便说此番,少府内帑为了帮助北地郡进行战后重建,单是负责匠工、铸造的官奴,就调了足足五万以上!
这已经是少府名下官奴的至少三成!
为了调出这五万官奴,就连刘荣即将动工开挖的皇陵:霸陵及对应的陵邑,都不得已暂且搁置。
陵邑制度对汉家的重要性——对汉家整合社会资源,降低社会贫富差距,压制地方豪强的意义,可谓不言而喻。
能让刘荣搁置自己的皇陵及陵邑工程,也要把人手调出来去‘建设北地’,只能说:为了此战,刘荣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牺牲,或者说是让步。
——为战争让路!
——自天子以下,凡汉之土、凡汉之民,都在为接下来这一场汉匈大战让路!
除了这五万官奴,及千人以上的工匠队伍之外,少府内帑对北地方向,便也没有了其他动作。
准确的说,是没有了其他明面上的动作。
几乎是在这五万官奴、上千匠人从长安出发,向北地而去的同一时间,长安城的夜晚时分,开始出现长达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。
所谓‘除宵禁’,便是封建王朝的城池,由于某些必要原因,在特定时间内暂时性解除宵禁。
具体到天子荣元年秋七月的长安城,便是每晚夜半时分,长安城四墙的六处城门,都开始出现为时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,即开城门。
一辆又一辆满载未知物资,并由人力驼拉的二轮车,于这每日夜班的两个时辰,从长安连绵不绝的运出。
出了长安城门,再由人力拉出去几里地,才会由老牛、驽马套上车,而后朝着北地而去。
——昼伏夜出!
无论是从长安城启运,还是从长安到北地的整个运送路线,少府内帑都严格遵守了刘荣的交代:昼伏夜出,藏匿行踪!
再加上少府内帑在朝北地‘偷偷调运物资’的同时,也在光明正大的向代北马邑一线,调动战时所需的粮草辎重,此番动作,便也没引起太多人的察觉。
当然了,有心人还是关注到了。
只是长安每晚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,仅仅只针对少府内帑的秘密物资运送车;
至于其他在这两个时辰中走出宅院,走上街头,意图刺探情报的汉奸走狗,则都被暗中盯梢的郎中令周仁部下绣衣卫,给挨个抓了起来。
抓来一审,果不其然:都是匈奴人费尽心机,花费十几二十年——乃至三十多年时间,在长安安插的探子、眼线。
多是被匈奴人设局威逼,而后重金相诱的汉人。
刘荣没多过问,让周仁自己看着办。
不是刘荣仁慈,而是大战在即,刘荣不想被这些人形蛆恶心到,并出现太过剧烈的情绪波动。
——大战在即!
刘荣,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,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、意料之外的状况,并第一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决策。
北地方向半明半暗,马邑方向完全明牌——花费将近半个月的时间,少府内帑针对此战调出的第一批军事物资,便已是基本到位。
第一批后勤物资到位,刘荣当即颁布诏谕:遍征关中良家子二十万,以奔赴马邑!
至此,汉家自秦继承而来,并一直在有意压制的战争机器,才算是正式发出了轰鸣声……
“代北苦寒,马邑城孤!”
“若事有可为,则当机立断,万不可负了天赐良机!”
“贼寇首级,事有可为则取,事不可为,便当已自身性命为首重!”
“须知尔家中,上有老翁兄嫂,下有妻儿女弟……”
长安城北的民户区:何家寨,一位花甲老翁正握住青年的手臂,一脸郑重的传授着宝贵经验。
老翁身后,一妇人泪眼婆娑,却是一句话也没说,只默默抱着整点好的行囊上前,咬牙含泪将行囊系在青年的背上。
妇人身旁,则是亲邻在温声安抚,不只是那老翁口中的‘兄嫂’,还是邻里街坊的婶子。
门框内,一颗怯生生的脑袋探出半边,望向青年的目光有不舍,有担忧;
但更多的,是一抹挥之不去的自豪……
“大人教诲,儿,谨记!”
便见青年整理好身上行囊、腰间佩剑,便对身前的老翁深深一拜!
而后便侧跨出一步,走到那垂泪的妇人身前,面色复杂的低下头;
良久,方轻轻拉起妇人的手,温声交代道:“父亲大人和大郎,便有劳细君了。”
“兄长落了伤残,腿脚不便,兄嫂怕也不能常来家中照看。”
“细君若实在顾不过来,便叫阿霞搭把手。”
···
“若俺殁了,能有几万钱抚恤;”
“真有那万一,把大郎送去兄长家中,全当是继兄长的血脉。”
“再给大郎留下万钱,便带着其余的,寻个好人家嫁了……”
没两句话的功夫,整条街上,都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啜泣、低吟。
——类似的场景,几乎在每家每户门口上演。
有老父老母,向儿子传授经验、见闻的;
有兄弟手足,彼此托付‘万当珍重’的;
也有妇人含泪将孩子的脑袋拉到腹前贴着,一把鼻涕一把泪,提醒丈夫‘不要逞强’的。
和过去一样;
和百十年前的秦时,以及有汉以来的每一场战争一样;
老秦人,再次送出了家中的男丁。
即便是早已熟悉无比的流程,长安城上空,也还是难免被一阵哀伤所充斥。
战争,从来都不存在‘不费一兵一卒’如何如何;
胜了,关中子弟便死少些;
败了,则死的多些。
总归,是要死人的;
总归,是要有人回不来的……
“大人珍重。”
父亲的儿子走了。
“回吧,带着小子,回。”
妻子的丈夫走了。
“大人!”
“万要得胜归来!”
儿子的父亲走了。
走了……
都走了……
……
“唉……”
“足足二十万大军,都堆在小小一座马邑……”
“也不知此番,匈奴贼蛮,又来了多少兵马……”
凡汉之男,全民皆兵。
此刻,望着一张张青涩的面庞,身着军袍,腰系长剑而去,年长者都不由自主的皱起了眉头。
都是带把的,十四五岁的年纪,都在当地受过冬训,二十啷当岁的年纪,也都戍过边、服过兵役。
就算没有见识过匈奴人入侵的景象,老一辈也还是从朝堂的征兵令中,察觉到了一丝严峻。
——二十万大军!
放在关东,足以镇压所有宗亲诸侯!
如今派去边墙,却仅仅只是守一座城……
守一座马邑……
“但愿上苍赐福,先祖庇佑;”
“太祖皇帝、太宗孝文皇帝在天之灵,能保佑我汉家旗开得胜……”
·
·
·
·
·
未央宫,清凉殿后殿。
还是那几乎占据整个殿室地面的巨大拟真沙盘;
只是此刻,刘荣身旁,却再也不见第二道身影。
——曲周侯郦寄,于秋七月十五正式获封为太尉,并于七日后率军开拔,北上代地!
雁门太守程不识,加前将军衔,率雁门兵二万、关中兵三万——合计五万兵马,驻守马邑!
雁门都尉郅都,加后将军衔,率楼烦县兵合关中兵,共五万兵马屯楼烦县,为马邑后援。
以上,即是朝堂对外公布的公开任命,同时也是真实任命。
而剩下的,则是刘荣为了这一战,导出来的一场好戏。
——弓高侯韩颓当,加车骑将军衔,率关中兵五万,随太尉郦寄左右;
实则,韩颓当部五万兵马,却是在行军途中与大部队悄然分离,化整为零,乔装奔赴北地。
——榆侯栾布,加上将军衔,同样是率军五万,同样是‘随太尉左右,帐下听令’,实际动向,却是同韩颓当所部如出一辙。
除此之外,还有江都王刘非——熟悉的配方,熟悉的味道:随先帝诸王一同出长安东去,半路偷偷脱离,目的地依旧是北地。
至此,此战,汉家在马邑、北地一明一暗两个战场的将帅部署,便基本完成。
剩下的,自然是刘荣往将官队伍里掺沙子,塞关系户。
上林苑监栗仓;
谒者仆射汲黯;
还有平阳侯曹氏家族、刘荣的母族栗氏,也都被刘荣塞去了北地。
就连宦者令葵五,刘荣都觉得留在宫中,白瞎了一身腱子肉,便塞给了老好人汲黯,全当是护其周全。
粮草辎重,已经先一步抵达预定战场;
部队,也已经在率军将帅的带领下出发,不日便将抵达。
也是直到这时,刘荣才发现:自己能做的——一个封建帝王,在一场数十万人级别的大型战役当中,所能做到的一切,刘荣都已经做完了。
剩下的,说好听点,就看天时地利人和,看将士们是否悍不畏死,将帅们是否运筹帷幄;
说难听点,便是刘荣现在的直观感受。
“明明是万事俱备,恨不能连将士们的裤衩颜色,都拿到庙算上商讨一番;”
“怎朕,却还是生出了‘听天由命’之感?”
略显呆滞的蹲坐在沙盘边,看着沙盘之上,那一个个立在‘汉家’边墙外的匈奴木马,以及那一个个与木马针锋相对的小木人;
再深深凝望向那片朝思暮想的塞上明珠:河套,刘荣只觉一阵莫敏的孤寂。
“倒是不曾注意朕,居然都有些习惯葵五那憨厮了……”
自言自语着,又盯着沙盘楞了好一会儿,刘荣才终于强迫自己回过神。
淡淡朝身体斜后方瞥一眼,而后便再度看向沙盘,嘴上却含笑道:“怎说,也是做长乐宫大长秋的宫人头子了。”
“见了朕,怎还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模样?”
被刘荣点到名,原本还在扮演塑像的夏雀,也终于如苏醒的老树精般,摇摇晃晃的转过了身。
正对向刘荣,恭恭敬敬拱手一拜,嘴上也不忘答道:“是宦者令指点奴婢:做了长乐宫众宦官之长,便当谨言慎行。”
“——最好是寡言少行。”
“时日久了,便也就习惯不说话了。”
有些年头没关注这个给母亲惊醒挑选的憨货,今日一见,刘荣便知夏雀,还是当年那个夏雀。
——或许如今的夏雀,不用再被宫人欺辱,更或是吃不饱肚子。
但夏雀本心依旧。
依旧还是那个憨态可掬,让人忍俊不禁的憨货……
“陪朕说说话。”
“葵五那憨子不在,朝中功侯、公卿,也都或明或暗出征了大半。”
“朕,苦闷的紧……”
苦笑着道出词语,刘荣当即从沙盘边沿的台阶上站起身,走到靠近殿内墙侧的御榻前,作势便要和夏雀下棋。
不只是对先帝的光荣事迹无从知晓,还是脑子没转过弯——见刘荣清理棋盘,夏雀只板板整整再拱手一礼,得刘荣‘坐’得眼神示意,还真就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只是接下来,夏雀手上的棋子胡乱落下,嘴上,也开始说起一些‘胡言乱语’的话。
“陛下即觉得苦闷,便该去椒房陪陪皇后。”
“宫里的人都说,周公之礼,那是人世间一等一的美事……”
刘荣:……
···
“太皇太后前些日子才说,陛下即立已近一年,再怎么着,也不该再耽误皇陵的事了。”
“最起码,也该先把陵邑建起来,再从关中迁一批地方豪强入关。”
“陛下为太皇太后之孙,总该听听长辈的……”
刘荣:………………
···
“陛下……”
“——有完没完?!”
“——下棋不语真君子懂不懂?!!”
夏雀:“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奴婢,不是君子啊……”
“奴婢,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奴婢而已……”
话说出口,不过轻描淡写八个字;
但实际操作起来,却是一副又一副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观。
——天子荣元年,秋七月初一,朝堂正式颁布政令:以少府内帑领头,相府国库从旁协助,正式在对今年年初,因战火而饱受摧残的北地郡,开启战后重建工作。
为了保证这项工作在秋收后第一时间上马,并在入冬前完成第一阶段任务,少府内帑,可以说是掏出了小半家底。
这很恐怖!
可千万不要觉得‘小半家底’四个字,放在哪里都是不起眼的数量级!
无论是封建王朝,还是后世新时代,任何以国家为主导进行的大宗货物库存,只要不再以‘百分之几’来计数,而是开始以‘几成’乃至‘小半’来形容,那就等同于海量!
便说此番,少府内帑为了帮助北地郡进行战后重建,单是负责匠工、铸造的官奴,就调了足足五万以上!
这已经是少府名下官奴的至少三成!
为了调出这五万官奴,就连刘荣即将动工开挖的皇陵:霸陵及对应的陵邑,都不得已暂且搁置。
陵邑制度对汉家的重要性——对汉家整合社会资源,降低社会贫富差距,压制地方豪强的意义,可谓不言而喻。
能让刘荣搁置自己的皇陵及陵邑工程,也要把人手调出来去‘建设北地’,只能说:为了此战,刘荣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牺牲,或者说是让步。
——为战争让路!
——自天子以下,凡汉之土、凡汉之民,都在为接下来这一场汉匈大战让路!
除了这五万官奴,及千人以上的工匠队伍之外,少府内帑对北地方向,便也没有了其他动作。
准确的说,是没有了其他明面上的动作。
几乎是在这五万官奴、上千匠人从长安出发,向北地而去的同一时间,长安城的夜晚时分,开始出现长达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。
所谓‘除宵禁’,便是封建王朝的城池,由于某些必要原因,在特定时间内暂时性解除宵禁。
具体到天子荣元年秋七月的长安城,便是每晚夜半时分,长安城四墙的六处城门,都开始出现为时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,即开城门。
一辆又一辆满载未知物资,并由人力驼拉的二轮车,于这每日夜班的两个时辰,从长安连绵不绝的运出。
出了长安城门,再由人力拉出去几里地,才会由老牛、驽马套上车,而后朝着北地而去。
——昼伏夜出!
无论是从长安城启运,还是从长安到北地的整个运送路线,少府内帑都严格遵守了刘荣的交代:昼伏夜出,藏匿行踪!
再加上少府内帑在朝北地‘偷偷调运物资’的同时,也在光明正大的向代北马邑一线,调动战时所需的粮草辎重,此番动作,便也没引起太多人的察觉。
当然了,有心人还是关注到了。
只是长安每晚两个时辰的‘除宵禁’,仅仅只针对少府内帑的秘密物资运送车;
至于其他在这两个时辰中走出宅院,走上街头,意图刺探情报的汉奸走狗,则都被暗中盯梢的郎中令周仁部下绣衣卫,给挨个抓了起来。
抓来一审,果不其然:都是匈奴人费尽心机,花费十几二十年——乃至三十多年时间,在长安安插的探子、眼线。
多是被匈奴人设局威逼,而后重金相诱的汉人。
刘荣没多过问,让周仁自己看着办。
不是刘荣仁慈,而是大战在即,刘荣不想被这些人形蛆恶心到,并出现太过剧烈的情绪波动。
——大战在即!
刘荣,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,来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、意料之外的状况,并第一时间做出最准确的决策。
北地方向半明半暗,马邑方向完全明牌——花费将近半个月的时间,少府内帑针对此战调出的第一批军事物资,便已是基本到位。
第一批后勤物资到位,刘荣当即颁布诏谕:遍征关中良家子二十万,以奔赴马邑!
至此,汉家自秦继承而来,并一直在有意压制的战争机器,才算是正式发出了轰鸣声……
“代北苦寒,马邑城孤!”
“若事有可为,则当机立断,万不可负了天赐良机!”
“贼寇首级,事有可为则取,事不可为,便当已自身性命为首重!”
“须知尔家中,上有老翁兄嫂,下有妻儿女弟……”
长安城北的民户区:何家寨,一位花甲老翁正握住青年的手臂,一脸郑重的传授着宝贵经验。
老翁身后,一妇人泪眼婆娑,却是一句话也没说,只默默抱着整点好的行囊上前,咬牙含泪将行囊系在青年的背上。
妇人身旁,则是亲邻在温声安抚,不只是那老翁口中的‘兄嫂’,还是邻里街坊的婶子。
门框内,一颗怯生生的脑袋探出半边,望向青年的目光有不舍,有担忧;
但更多的,是一抹挥之不去的自豪……
“大人教诲,儿,谨记!”
便见青年整理好身上行囊、腰间佩剑,便对身前的老翁深深一拜!
而后便侧跨出一步,走到那垂泪的妇人身前,面色复杂的低下头;
良久,方轻轻拉起妇人的手,温声交代道:“父亲大人和大郎,便有劳细君了。”
“兄长落了伤残,腿脚不便,兄嫂怕也不能常来家中照看。”
“细君若实在顾不过来,便叫阿霞搭把手。”
···
“若俺殁了,能有几万钱抚恤;”
“真有那万一,把大郎送去兄长家中,全当是继兄长的血脉。”
“再给大郎留下万钱,便带着其余的,寻个好人家嫁了……”
没两句话的功夫,整条街上,都响起一阵此起彼伏的啜泣、低吟。
——类似的场景,几乎在每家每户门口上演。
有老父老母,向儿子传授经验、见闻的;
有兄弟手足,彼此托付‘万当珍重’的;
也有妇人含泪将孩子的脑袋拉到腹前贴着,一把鼻涕一把泪,提醒丈夫‘不要逞强’的。
和过去一样;
和百十年前的秦时,以及有汉以来的每一场战争一样;
老秦人,再次送出了家中的男丁。
即便是早已熟悉无比的流程,长安城上空,也还是难免被一阵哀伤所充斥。
战争,从来都不存在‘不费一兵一卒’如何如何;
胜了,关中子弟便死少些;
败了,则死的多些。
总归,是要死人的;
总归,是要有人回不来的……
“大人珍重。”
父亲的儿子走了。
“回吧,带着小子,回。”
妻子的丈夫走了。
“大人!”
“万要得胜归来!”
儿子的父亲走了。
走了……
都走了……
……
“唉……”
“足足二十万大军,都堆在小小一座马邑……”
“也不知此番,匈奴贼蛮,又来了多少兵马……”
凡汉之男,全民皆兵。
此刻,望着一张张青涩的面庞,身着军袍,腰系长剑而去,年长者都不由自主的皱起了眉头。
都是带把的,十四五岁的年纪,都在当地受过冬训,二十啷当岁的年纪,也都戍过边、服过兵役。
就算没有见识过匈奴人入侵的景象,老一辈也还是从朝堂的征兵令中,察觉到了一丝严峻。
——二十万大军!
放在关东,足以镇压所有宗亲诸侯!
如今派去边墙,却仅仅只是守一座城……
守一座马邑……
“但愿上苍赐福,先祖庇佑;”
“太祖皇帝、太宗孝文皇帝在天之灵,能保佑我汉家旗开得胜……”
·
·
·
·
·
未央宫,清凉殿后殿。
还是那几乎占据整个殿室地面的巨大拟真沙盘;
只是此刻,刘荣身旁,却再也不见第二道身影。
——曲周侯郦寄,于秋七月十五正式获封为太尉,并于七日后率军开拔,北上代地!
雁门太守程不识,加前将军衔,率雁门兵二万、关中兵三万——合计五万兵马,驻守马邑!
雁门都尉郅都,加后将军衔,率楼烦县兵合关中兵,共五万兵马屯楼烦县,为马邑后援。
以上,即是朝堂对外公布的公开任命,同时也是真实任命。
而剩下的,则是刘荣为了这一战,导出来的一场好戏。
——弓高侯韩颓当,加车骑将军衔,率关中兵五万,随太尉郦寄左右;
实则,韩颓当部五万兵马,却是在行军途中与大部队悄然分离,化整为零,乔装奔赴北地。
——榆侯栾布,加上将军衔,同样是率军五万,同样是‘随太尉左右,帐下听令’,实际动向,却是同韩颓当所部如出一辙。
除此之外,还有江都王刘非——熟悉的配方,熟悉的味道:随先帝诸王一同出长安东去,半路偷偷脱离,目的地依旧是北地。
至此,此战,汉家在马邑、北地一明一暗两个战场的将帅部署,便基本完成。
剩下的,自然是刘荣往将官队伍里掺沙子,塞关系户。
上林苑监栗仓;
谒者仆射汲黯;
还有平阳侯曹氏家族、刘荣的母族栗氏,也都被刘荣塞去了北地。
就连宦者令葵五,刘荣都觉得留在宫中,白瞎了一身腱子肉,便塞给了老好人汲黯,全当是护其周全。
粮草辎重,已经先一步抵达预定战场;
部队,也已经在率军将帅的带领下出发,不日便将抵达。
也是直到这时,刘荣才发现:自己能做的——一个封建帝王,在一场数十万人级别的大型战役当中,所能做到的一切,刘荣都已经做完了。
剩下的,说好听点,就看天时地利人和,看将士们是否悍不畏死,将帅们是否运筹帷幄;
说难听点,便是刘荣现在的直观感受。
“明明是万事俱备,恨不能连将士们的裤衩颜色,都拿到庙算上商讨一番;”
“怎朕,却还是生出了‘听天由命’之感?”
略显呆滞的蹲坐在沙盘边,看着沙盘之上,那一个个立在‘汉家’边墙外的匈奴木马,以及那一个个与木马针锋相对的小木人;
再深深凝望向那片朝思暮想的塞上明珠:河套,刘荣只觉一阵莫敏的孤寂。
“倒是不曾注意朕,居然都有些习惯葵五那憨厮了……”
自言自语着,又盯着沙盘楞了好一会儿,刘荣才终于强迫自己回过神。
淡淡朝身体斜后方瞥一眼,而后便再度看向沙盘,嘴上却含笑道:“怎说,也是做长乐宫大长秋的宫人头子了。”
“见了朕,怎还是一副沉默寡言的模样?”
被刘荣点到名,原本还在扮演塑像的夏雀,也终于如苏醒的老树精般,摇摇晃晃的转过了身。
正对向刘荣,恭恭敬敬拱手一拜,嘴上也不忘答道:“是宦者令指点奴婢:做了长乐宫众宦官之长,便当谨言慎行。”
“——最好是寡言少行。”
“时日久了,便也就习惯不说话了。”
有些年头没关注这个给母亲惊醒挑选的憨货,今日一见,刘荣便知夏雀,还是当年那个夏雀。
——或许如今的夏雀,不用再被宫人欺辱,更或是吃不饱肚子。
但夏雀本心依旧。
依旧还是那个憨态可掬,让人忍俊不禁的憨货……
“陪朕说说话。”
“葵五那憨子不在,朝中功侯、公卿,也都或明或暗出征了大半。”
“朕,苦闷的紧……”
苦笑着道出词语,刘荣当即从沙盘边沿的台阶上站起身,走到靠近殿内墙侧的御榻前,作势便要和夏雀下棋。
不只是对先帝的光荣事迹无从知晓,还是脑子没转过弯——见刘荣清理棋盘,夏雀只板板整整再拱手一礼,得刘荣‘坐’得眼神示意,还真就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只是接下来,夏雀手上的棋子胡乱落下,嘴上,也开始说起一些‘胡言乱语’的话。
“陛下即觉得苦闷,便该去椒房陪陪皇后。”
“宫里的人都说,周公之礼,那是人世间一等一的美事……”
刘荣:……
···
“太皇太后前些日子才说,陛下即立已近一年,再怎么着,也不该再耽误皇陵的事了。”
“最起码,也该先把陵邑建起来,再从关中迁一批地方豪强入关。”
“陛下为太皇太后之孙,总该听听长辈的……”
刘荣:………………
···
“陛下……”
“——有完没完?!”
“——下棋不语真君子懂不懂?!!”
夏雀:“可是……”
“可是奴婢,不是君子啊……”
“奴婢,只是……”
“只是奴婢而已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