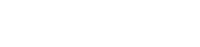“哟?!”
“短短三年,朕的江都,居然便已有了如此感悟?”
刘非话音刚落,便见御榻之上的刘荣兴致大发!
当即便提了提袖子,大刀阔斧的一手反撑着大腿,一手以手肘落在腿上,兴致勃勃的对刘非一昂首。
“说说。”
“怎么就国家兴亡,百姓皆苦了?”
刘荣很惊喜!
因为在过去,刘荣对这个五弟唯一的印象,便是少年慕武,志向远大!
当然,这里的志向远大,并非是说有什么野心,而是身为含着金汤勺出身的皇子,刘非毕生之愿,却尽在行伍之间、战阵之中。
这很难得;
对于任何一位出身不菲,家族背景深厚的贵族子弟,这份觉悟都很难得。
但除此之外,刘荣并不曾觉得五弟刘非,和傻乎乎的三弟刘淤有什么其他区别。
说得再直白一些,便是在刘荣看来,五弟江都王刘非,便是武力值加满的三弟临江王刘淤plus。
刘荣对三弟刘淤是个什么看法,从刘荣这几年对刘淤‘活着就行,不死就行’的超低期望值,便可见一斑。
也就难怪刘非今日,说出这样一番与人设严重不符的话时,刘荣会感到惊喜,甚至是惊奇了。
看出刘荣望向自己的目光灼灼,刘非第一时间,便本能的看向了身旁的兄长刘余。
待刘余淡笑着轻一点头,刘非才深吸一口气,顺着自己刚才那一声感慨,剖析起了自己过往三年,诸侯生涯的成长。
“嗯……”
“便拿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来说吧。”
···
“当年,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举兵谋逆,赵王刘遂紧随其后,齐系、淮南系也蠢蠢欲动,蓄势待发。”
“彼时,寡人只想着这是天赐良机,便兴奋不已的请命于皇兄、先帝,以挂印出征。”
“——朝堂内外,甚至全天下的人都在说:皇五子不惜以身报国,效于战阵,可堪丈夫!”
“寡人也因此而沾沾自喜,更以此,作为寡人拼死血战的缘由。”
“唉~”
“年轻啊……”
说到一半,刘非自顾自的苦笑着摇了摇头,再悠然发出一声长叹。
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从思绪中回过神,继续道:“当年,寡人听令于曲周侯郦寄、榆侯栾布账下。”
“寡人所在偏师,共有将士十万。”
“另太尉条侯周亚夫二十万、大将军魏其侯窦婴二十万。”
“——五十万大军呐~”
“当年只道是兵峰所盛,无可匹敌;”
“却不知,这五十万大军,单就是军粮,每月便是百万石之巨……”
···
“丞相秩禄万石,实俸四千石——这百万石军粮,可是够我汉家,给丞相发二百五十年的俸禄啊?”
“二百五十年的丞相俸禄,却只需一个月,便要尽被平叛大军吃入肚中……”
“——吴楚之乱三月而平,战前整备一月,战后班师、遣散,便又是二月有余。”
“一场吴楚之乱,长安朝堂所耗费的军粮,竟然够我汉家,给丞相发一千五百年的俸禄!”
wшw. t tka n. co
“这数百万石军粮——这一千五百年的丞相俸禄,从何而来?”
“还不是关中百姓民,户得田百亩,岁得米粮三百石,又以三十税一之比,每户十石缴上国库,以数十万户百姓民一年的农税,十石十石凑出来的?”
略带苦涩,甚至还隐隐带着些义愤填膺的话,顿时惹得兄弟众人——包括刘荣在内,都纷纷面带惊奇的挑起了眉角。
嘿!
江都这三年,刘非这是铁定没在王宫里头醉生梦死啊!
从小就在深宫里头,自幼连钱都没用上几回的公子哥,居然都感悟到人间疾苦了?
“江都王太傅……”
“是谁来着?”
“教的可~以啊?”
如是想着,暗暗将‘查查江都王太傅’的事记下,刘荣便含笑点下头;
见刘非一副说上了头,缓过神来又有些尴尬的模样,也颇为贴心的接过了话头。
“确实如此。”
“当年,一场吴楚七国之乱,相府国库、少府内帑加在一起,花费了粮食上千万石,又各式财货价值数十万万钱,才堪堪得以平定。”
“——朕还记得当时,是建陵侯为少府;”
“几乎每一日,少府都会在宣室殿外向先帝哭诉,说太宗孝文皇帝二十多年的积蓄,一场吴楚之乱,便去了将近一成……”
···
“叛乱平定之后,少府内帑存粮消耗过半,更有关中粮商米谷狼狈为奸,伙同朝中功侯贵戚哄抬粮价,以食民之肉、饮民之血。”
“先帝震怒,遂以朕掌关中粮价平抑事,以免关中生灵涂炭,百姓民不聊生……”
“当年,朕主平关中粮价,河间、临将,又江都、常山诸王,那也都是曾帮衬于朕左右的。”
刘荣此言一出,刘德、刘余两个聪明人本能的一对视,而后默契的选择继续沉默。
当年这件事,至今都还流传于关东宗亲诸侯之间。
至于原因,则是因为当年,刚获封为太子储君的当今刘荣,和姑母馆陶主第一次正面对上。
最终结果,是刘荣完胜。
但在关东宗亲诸侯——在老刘家的亲戚们看来,刘荣这样对自己的姑母,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了。
刘德、刘余二人虽然不这么认为,但也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。
最关键的是:馆陶公主刘嫖对刘荣——或者说是对皇后之位、椒房之主的图谋,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结束。
兄弟众人常年在外,没道理平白无故得罪刘嫖。
毕竟馆陶主刘嫖,除了一向为人称道,如今却已经不怎么好使的职业道德之外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便是那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的特性。
“王在江都这些年,长进不少。”
短暂的沉默之后,刘荣略带严肃的一语,算是认可了刘非这几年的成长。
对于汉家的宗亲诸侯,刘荣的要求不敢。
准确的说,汉家的历代天子,对这些亲戚们的要求都不高。
——闲着没事儿能少惹点祸,就算惹祸也尽量别霍霍百姓;
尽可能用外出打猎、宴请,在宫里玩儿女人、打孩子充实枯燥乏味的贵族生活,更是再好不过。
至于国政——长安朝堂自然会派去一整套的行政班子,从负责教导、约束诸侯王的太傅,主掌国政的诸侯国相,以及相应的中尉、内史等等。
从刘非这看似不起眼的‘国家兴亡,百姓皆苦’的表态,刘荣能看到的,却是一个对底层民众生存现状有一定了解,并报以适当怜悯的诸侯王。
这很好。
至少在将来,刘非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打错了,想要做点子王的时候,这份怜悯能为江都国的百姓,争取到些许聊胜于无的生存空间。
华夏民族,尤其是华夏底层群众,从来都是最能吃苦、最能忍耐的人。
如果说华夏底层群众是羊,那他们要的,往往只是一口能吃饱肚子的草。
只要草管够,那羊毛就随便你薅。
这便是刘荣对刘非感到惊喜、欣赏的点。
——刘非,已经具备了‘尽量让羊都吃上足够的草’的认知。
而这一认知,足够让刘非的下限,达到刘荣对宗亲诸侯——尤其是对手足兄弟的忍受界限之上。
“既然有了如此长进,那~”
“还想打仗吗?”
“还想要挂印领兵,挥斥方遒,肆意驰骋于战场之上吗?”
刘荣此问一出,刘非只当是刘荣仍在考校自己,便本能的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不敢了。”
“臣弟,再也不敢将战争,当做供臣弟一展宏图大志的玩物了。”
···
“在就藩之后,臣弟同王相、内史,以及中尉计较过。”
“——如果臣弟想要发兵南下,攻略岭南,那没有个三五万军队,是根本无法威胁到赵佗老儿的。”
“但臣弟的江都国,取自曾经的吴国江陵郡。”
“——一无可采之铜山,二无临海之盐池。”
“若是兴兵,每月至少十万石的军粮,又数以倍计的抚恤、耗费,都需要国中子民承担。”
“如果打一场耗时三个月,发兵五万的战争,那我江都国的花费,便当在六千万钱上下。”
“而今,我江都国,百姓民不过一十九万户,不足百万口。”
“让每户农人出钱三百,供臣弟同那南越赵佗,打上一场无伤大雅,更无法伤及其分毫的、无意义的战争……”
“臣弟,甚不取也……”
言罢,刘非苦笑着摇摇头,又暗含落寞的低下头去。
刘非真的不想打仗、真的不想做将军了?
当然不是。
儿时的梦想,尤其还是毕生志向,怎么可能如此轻易便破碎?
但就藩三年,认识到江都国的实际状况之后,即便再怎么不愿、不甘,刘非最终,也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。
虽然早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不久,刘非便已经知道:曾经帮助吴王刘濞强大起来,甚至强大到有底气和长安朝堂中央叫板的两条腿:钱、盐,不大可能再被某位宗亲诸侯所掌控;
但在就藩江都,真真切切认识到江都国的状况之后,刘非也还是难免发起了牢骚。
——先孝景皇帝对吴国的肢解,实在是太过彻底……
原本的吴地三郡,一郡开山铸钱,一郡煮海制盐——如今都已经废为郡县,并由长安朝堂直辖!
唯独剩下一个啥啥没有、啥啥都缺的江都郡,被分封给刘非作为江都国。
刘非确实想过:只要条件允许,那就争取成为汉家的南方边境的戍边王,建功立业,以赫赫战功,震四海八荒!
但在认识到江都国的实际状况之后,刘非只得承认:就算是想带一两万人,去南越和赵佗小小切磋一下,刘非这个江都王,也得省吃俭用三五年,才能凑出足够的军费。
这还没有考虑战果!
打赢了还好说;
虽然长安朝堂或许会有人叽叽歪歪,说江都王私调兵马,无诏灭国之类,但终归是功大于过,赏重于罚;
可万一打输了——甚至仅仅只是打了个平手,刘非也当即便要坐蜡。
考虑到此间种种,刘非纠结许久,才终于做出决断。
——寡人这辈子,也就这样了……
老老实实在国都的王宫带着,传延子嗣,延续香火;
至于过剩的男性荷尔蒙,就在猎场发泄发泄得了。
南越赵佗,是没这个福气,能一睹孝景皇五子的无上英姿……
“早些年,孝景皇帝以江都之事相问,朕答:江都好武而不能持重,封,则不可往北墙为王。”
正当刘非独自唉声叹气的时候,刘非悠悠一语,将兄弟众人各自飞散的心绪重新拉回眼前。
意识到刘荣说了什么,刘非先是稍有些诧异的抬起头,略有些无辜的望向御榻之上;
片刻之后,又释然的点了点头,算是承认了刘荣当年,对当年的自己的评价。
——当时的自己,可不就是满脑子打打杀杀,除了打仗啥都不感兴趣嘛?
真要是被封去了北墙,鬼知道这几年,要和匈奴人打出几斤狗脑子。
刘荣曾劝先帝‘不要封五弟为背景戍边王’,刘非有些幽怨;
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讲,刘非也承认刘荣这个做法,是有道理的。
“陛下明见万里,臣弟,谨谢……”
“——但朕现在觉得,如今的江都,不再是那个只知打打杀杀,却不明于治国之道的莽夫了。”
刘非话音未落,刘荣冷不丁又是一个毫无征兆的转折,险些没闪了兄弟众人的腰。
便见刘荣缓缓从榻上站起身,目光直勾勾凝望向刘非眼眸深处。
良久,方沉声问道:“对战争没有敬畏之心的人,不可以掌握一场战争的走向。”
“曾经,朕的五弟对战争毫无敬畏,朕不敢用。”
“如今,我汉家的江都王,终于明白了何为敬畏、何为战争。”
“朕,或许便可用江都,为我刘氏之矛、为我汉家之盾了……”
···
“今岁秋后,北蛮匈奴必当再度南下,以攻掠代、上。”
“——朕!欲将计就计,图谋河南地!”
“待朕重取河南,移封宗藩以镇游牧之民,江都,可愿为我汉家之蒙王,为朕驻守河南养马之所,北戒匈奴、西望河西;”
“世世代代,为我汉家北墙之屏障?”
“短短三年,朕的江都,居然便已有了如此感悟?”
刘非话音刚落,便见御榻之上的刘荣兴致大发!
当即便提了提袖子,大刀阔斧的一手反撑着大腿,一手以手肘落在腿上,兴致勃勃的对刘非一昂首。
“说说。”
“怎么就国家兴亡,百姓皆苦了?”
刘荣很惊喜!
因为在过去,刘荣对这个五弟唯一的印象,便是少年慕武,志向远大!
当然,这里的志向远大,并非是说有什么野心,而是身为含着金汤勺出身的皇子,刘非毕生之愿,却尽在行伍之间、战阵之中。
这很难得;
对于任何一位出身不菲,家族背景深厚的贵族子弟,这份觉悟都很难得。
但除此之外,刘荣并不曾觉得五弟刘非,和傻乎乎的三弟刘淤有什么其他区别。
说得再直白一些,便是在刘荣看来,五弟江都王刘非,便是武力值加满的三弟临江王刘淤plus。
刘荣对三弟刘淤是个什么看法,从刘荣这几年对刘淤‘活着就行,不死就行’的超低期望值,便可见一斑。
也就难怪刘非今日,说出这样一番与人设严重不符的话时,刘荣会感到惊喜,甚至是惊奇了。
看出刘荣望向自己的目光灼灼,刘非第一时间,便本能的看向了身旁的兄长刘余。
待刘余淡笑着轻一点头,刘非才深吸一口气,顺着自己刚才那一声感慨,剖析起了自己过往三年,诸侯生涯的成长。
“嗯……”
“便拿当年,吴楚七国之乱来说吧。”
···
“当年,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举兵谋逆,赵王刘遂紧随其后,齐系、淮南系也蠢蠢欲动,蓄势待发。”
“彼时,寡人只想着这是天赐良机,便兴奋不已的请命于皇兄、先帝,以挂印出征。”
“——朝堂内外,甚至全天下的人都在说:皇五子不惜以身报国,效于战阵,可堪丈夫!”
“寡人也因此而沾沾自喜,更以此,作为寡人拼死血战的缘由。”
“唉~”
“年轻啊……”
说到一半,刘非自顾自的苦笑着摇了摇头,再悠然发出一声长叹。
沉默了好一会儿,才从思绪中回过神,继续道:“当年,寡人听令于曲周侯郦寄、榆侯栾布账下。”
“寡人所在偏师,共有将士十万。”
“另太尉条侯周亚夫二十万、大将军魏其侯窦婴二十万。”
“——五十万大军呐~”
“当年只道是兵峰所盛,无可匹敌;”
“却不知,这五十万大军,单就是军粮,每月便是百万石之巨……”
···
“丞相秩禄万石,实俸四千石——这百万石军粮,可是够我汉家,给丞相发二百五十年的俸禄啊?”
“二百五十年的丞相俸禄,却只需一个月,便要尽被平叛大军吃入肚中……”
“——吴楚之乱三月而平,战前整备一月,战后班师、遣散,便又是二月有余。”
“一场吴楚之乱,长安朝堂所耗费的军粮,竟然够我汉家,给丞相发一千五百年的俸禄!”
wшw. t tka n. co
“这数百万石军粮——这一千五百年的丞相俸禄,从何而来?”
“还不是关中百姓民,户得田百亩,岁得米粮三百石,又以三十税一之比,每户十石缴上国库,以数十万户百姓民一年的农税,十石十石凑出来的?”
略带苦涩,甚至还隐隐带着些义愤填膺的话,顿时惹得兄弟众人——包括刘荣在内,都纷纷面带惊奇的挑起了眉角。
嘿!
江都这三年,刘非这是铁定没在王宫里头醉生梦死啊!
从小就在深宫里头,自幼连钱都没用上几回的公子哥,居然都感悟到人间疾苦了?
“江都王太傅……”
“是谁来着?”
“教的可~以啊?”
如是想着,暗暗将‘查查江都王太傅’的事记下,刘荣便含笑点下头;
见刘非一副说上了头,缓过神来又有些尴尬的模样,也颇为贴心的接过了话头。
“确实如此。”
“当年,一场吴楚七国之乱,相府国库、少府内帑加在一起,花费了粮食上千万石,又各式财货价值数十万万钱,才堪堪得以平定。”
“——朕还记得当时,是建陵侯为少府;”
“几乎每一日,少府都会在宣室殿外向先帝哭诉,说太宗孝文皇帝二十多年的积蓄,一场吴楚之乱,便去了将近一成……”
···
“叛乱平定之后,少府内帑存粮消耗过半,更有关中粮商米谷狼狈为奸,伙同朝中功侯贵戚哄抬粮价,以食民之肉、饮民之血。”
“先帝震怒,遂以朕掌关中粮价平抑事,以免关中生灵涂炭,百姓民不聊生……”
“当年,朕主平关中粮价,河间、临将,又江都、常山诸王,那也都是曾帮衬于朕左右的。”
刘荣此言一出,刘德、刘余两个聪明人本能的一对视,而后默契的选择继续沉默。
当年这件事,至今都还流传于关东宗亲诸侯之间。
至于原因,则是因为当年,刚获封为太子储君的当今刘荣,和姑母馆陶主第一次正面对上。
最终结果,是刘荣完胜。
但在关东宗亲诸侯——在老刘家的亲戚们看来,刘荣这样对自己的姑母,多少有些不近人情了。
刘德、刘余二人虽然不这么认为,但也不敢在这个话题上多说什么。
最关键的是:馆陶公主刘嫖对刘荣——或者说是对皇后之位、椒房之主的图谋,至今都还没有完全结束。
兄弟众人常年在外,没道理平白无故得罪刘嫖。
毕竟馆陶主刘嫖,除了一向为人称道,如今却已经不怎么好使的职业道德之外,最令人印象深刻的,便是那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的特性。
“王在江都这些年,长进不少。”
短暂的沉默之后,刘荣略带严肃的一语,算是认可了刘非这几年的成长。
对于汉家的宗亲诸侯,刘荣的要求不敢。
准确的说,汉家的历代天子,对这些亲戚们的要求都不高。
——闲着没事儿能少惹点祸,就算惹祸也尽量别霍霍百姓;
尽可能用外出打猎、宴请,在宫里玩儿女人、打孩子充实枯燥乏味的贵族生活,更是再好不过。
至于国政——长安朝堂自然会派去一整套的行政班子,从负责教导、约束诸侯王的太傅,主掌国政的诸侯国相,以及相应的中尉、内史等等。
从刘非这看似不起眼的‘国家兴亡,百姓皆苦’的表态,刘荣能看到的,却是一个对底层民众生存现状有一定了解,并报以适当怜悯的诸侯王。
这很好。
至少在将来,刘非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打错了,想要做点子王的时候,这份怜悯能为江都国的百姓,争取到些许聊胜于无的生存空间。
华夏民族,尤其是华夏底层群众,从来都是最能吃苦、最能忍耐的人。
如果说华夏底层群众是羊,那他们要的,往往只是一口能吃饱肚子的草。
只要草管够,那羊毛就随便你薅。
这便是刘荣对刘非感到惊喜、欣赏的点。
——刘非,已经具备了‘尽量让羊都吃上足够的草’的认知。
而这一认知,足够让刘非的下限,达到刘荣对宗亲诸侯——尤其是对手足兄弟的忍受界限之上。
“既然有了如此长进,那~”
“还想打仗吗?”
“还想要挂印领兵,挥斥方遒,肆意驰骋于战场之上吗?”
刘荣此问一出,刘非只当是刘荣仍在考校自己,便本能的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“不敢了。”
“臣弟,再也不敢将战争,当做供臣弟一展宏图大志的玩物了。”
···
“在就藩之后,臣弟同王相、内史,以及中尉计较过。”
“——如果臣弟想要发兵南下,攻略岭南,那没有个三五万军队,是根本无法威胁到赵佗老儿的。”
“但臣弟的江都国,取自曾经的吴国江陵郡。”
“——一无可采之铜山,二无临海之盐池。”
“若是兴兵,每月至少十万石的军粮,又数以倍计的抚恤、耗费,都需要国中子民承担。”
“如果打一场耗时三个月,发兵五万的战争,那我江都国的花费,便当在六千万钱上下。”
“而今,我江都国,百姓民不过一十九万户,不足百万口。”
“让每户农人出钱三百,供臣弟同那南越赵佗,打上一场无伤大雅,更无法伤及其分毫的、无意义的战争……”
“臣弟,甚不取也……”
言罢,刘非苦笑着摇摇头,又暗含落寞的低下头去。
刘非真的不想打仗、真的不想做将军了?
当然不是。
儿时的梦想,尤其还是毕生志向,怎么可能如此轻易便破碎?
但就藩三年,认识到江都国的实际状况之后,即便再怎么不愿、不甘,刘非最终,也还是不得不接受现实。
虽然早在吴楚之乱平定之后不久,刘非便已经知道:曾经帮助吴王刘濞强大起来,甚至强大到有底气和长安朝堂中央叫板的两条腿:钱、盐,不大可能再被某位宗亲诸侯所掌控;
但在就藩江都,真真切切认识到江都国的状况之后,刘非也还是难免发起了牢骚。
——先孝景皇帝对吴国的肢解,实在是太过彻底……
原本的吴地三郡,一郡开山铸钱,一郡煮海制盐——如今都已经废为郡县,并由长安朝堂直辖!
唯独剩下一个啥啥没有、啥啥都缺的江都郡,被分封给刘非作为江都国。
刘非确实想过:只要条件允许,那就争取成为汉家的南方边境的戍边王,建功立业,以赫赫战功,震四海八荒!
但在认识到江都国的实际状况之后,刘非只得承认:就算是想带一两万人,去南越和赵佗小小切磋一下,刘非这个江都王,也得省吃俭用三五年,才能凑出足够的军费。
这还没有考虑战果!
打赢了还好说;
虽然长安朝堂或许会有人叽叽歪歪,说江都王私调兵马,无诏灭国之类,但终归是功大于过,赏重于罚;
可万一打输了——甚至仅仅只是打了个平手,刘非也当即便要坐蜡。
考虑到此间种种,刘非纠结许久,才终于做出决断。
——寡人这辈子,也就这样了……
老老实实在国都的王宫带着,传延子嗣,延续香火;
至于过剩的男性荷尔蒙,就在猎场发泄发泄得了。
南越赵佗,是没这个福气,能一睹孝景皇五子的无上英姿……
“早些年,孝景皇帝以江都之事相问,朕答:江都好武而不能持重,封,则不可往北墙为王。”
正当刘非独自唉声叹气的时候,刘非悠悠一语,将兄弟众人各自飞散的心绪重新拉回眼前。
意识到刘荣说了什么,刘非先是稍有些诧异的抬起头,略有些无辜的望向御榻之上;
片刻之后,又释然的点了点头,算是承认了刘荣当年,对当年的自己的评价。
——当时的自己,可不就是满脑子打打杀杀,除了打仗啥都不感兴趣嘛?
真要是被封去了北墙,鬼知道这几年,要和匈奴人打出几斤狗脑子。
刘荣曾劝先帝‘不要封五弟为背景戍边王’,刘非有些幽怨;
但从客观角度上来讲,刘非也承认刘荣这个做法,是有道理的。
“陛下明见万里,臣弟,谨谢……”
“——但朕现在觉得,如今的江都,不再是那个只知打打杀杀,却不明于治国之道的莽夫了。”
刘非话音未落,刘荣冷不丁又是一个毫无征兆的转折,险些没闪了兄弟众人的腰。
便见刘荣缓缓从榻上站起身,目光直勾勾凝望向刘非眼眸深处。
良久,方沉声问道:“对战争没有敬畏之心的人,不可以掌握一场战争的走向。”
“曾经,朕的五弟对战争毫无敬畏,朕不敢用。”
“如今,我汉家的江都王,终于明白了何为敬畏、何为战争。”
“朕,或许便可用江都,为我刘氏之矛、为我汉家之盾了……”
···
“今岁秋后,北蛮匈奴必当再度南下,以攻掠代、上。”
“——朕!欲将计就计,图谋河南地!”
“待朕重取河南,移封宗藩以镇游牧之民,江都,可愿为我汉家之蒙王,为朕驻守河南养马之所,北戒匈奴、西望河西;”
“世世代代,为我汉家北墙之屏障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