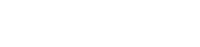作为二世祖——或者说是三世祖,许九当然也幻想过有朝一日,自己可以得到天子赏识,以重铸,甚至是超越先祖荣光。
贵族生活,实在是无趣的很。
后世有一句话:人类的物质欲望,是无穷无尽的。
但很少有人想到,物质欲望,并非无穷无尽;
而是说出‘物资欲望无穷无尽’这句话的人,没有,也必定无法达到那个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顶尖层面。
——物质欲望,是有尽头的。
当你拥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物质时,你的物质欲望就会彻底得到满足。
紧随其后的,便是索然无味的贤者时间。
之后,对物质的欲望,就会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权力,以及对地位的渴望。
许九是贵族;
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,许九便几乎能得到世上所存在的一切。
但作为贵族后人,或者说是即将落魄的贵族,许九在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,却根本无法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。
地位是有的;
但也只是虚尊,而且还是靠父祖的威名,和许九本身并无关系。
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,许九当然渴望得到认可。
无论是大众由衷的钦佩、同阶级的贵族由衷的敬服,又或是‘顶头上司’——天子的赞赏,都是许九这个生活枯燥而又乏味的贵族所渴望的。
但理想和现实,却总是背道而驰。
许九想过策马奔腾,于战场上建功立业;
结果直到三年前,大行皇帝三年那场吴楚七国之乱,许九才终于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耗资数以千万,大张旗鼓的装备起百十家兵,雄赳赳气昂昂上了战场!
在战场上走了一圈下来——精锐亲卫死伤大半不说,武勋更是压根儿没捞到多少。
满共就十几颗叛军首级,堪堪达到许九的kpi,只得了个口头嘉奖,外加下一代宋子侯不必降爵的赏赐。
——汉家的爵位,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世袭,而是世代累降。
或者应该说,是原则上,每一个人从父亲处承袭的爵位,都会比父亲的原爵位低一级。
你爹是彻侯,你就该袭爵关内侯;
你爹是大上造,你袭爵就是少上造。
你爹是最低一级的公士,那好吧,伱也是公士——实在没有再往下降的空间了。
之所以说是‘原则上’,是因为这世代累降爵位的规定,是有避免方式的。
就好比许九的祖父,作为开国元勋,被太祖高皇帝敕封为彻侯;
按理来说,到了许九的父亲这一辈,宋子侯国就该被降为关内侯。
但许九的祖父在得封之后,按照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,自掏腰包组织兵马,随朝堂大军参加了几场异姓诸侯叛乱的平定。
kpi达成,侯世子——也就是许九的父亲,才得以承袭宋子侯国的彻侯爵位,而非关内侯爵位。
一样的道理:到了许九这一代,宋子侯国,原本也还是该降爵为关内侯。
但许九的父亲运气很好,在那场匈奴人兵峰直至长安的动荡中,捞了个偏将军的将印,斩获了几颗匈奴先锋首级。
虽然并非亲自斩获,而是麾下将士所得,但许九的父亲也就借此完成了kpi,成功避免了爵位累降。
但在亲自上过战场之后,许九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军事天赋。
——花了几千万钱,恨不能把那百来个家丁武装到牙齿,结果捞回来的武勋,才堪堪够保住下一代宋子侯的彻侯爵位?
那得砸多少钱,才能真正建功立业,甚至是得到溢封食邑的赏赐?
许九算了算,一场吴楚七国之乱,自己投入了侯国将近十五年的产出;
于是,许九很快便得出结论:这种砸钱买‘不降爵名额’的蠢事儿,每代人干一回,确保下一代不丢掉彻侯爵位就够了。
但凡多来一两回,就算保住了彻侯爵位,怕也是要穷的叮当响,根本维持不住彻侯的威仪。
军事不行,许九又想到了宦途。
汉家的贵族,并非不能做官。
——如今汉家,甚至至今都还保留着‘非彻侯不能为相’的政治潜规则。
彻侯身份,能为许九带来很大的政治助力,起点也会很高;
但凡做出点成绩——甚至但凡能在一个位置上,稳稳坐几年不犯大错,就基本能往九卿的方向靠拢了。
只可惜,在尝试性了解过官场之后,许九再次选择了放弃。
太难了……
做官,实在是太难了……
尤其如今汉家每年一小计,三年一大计;
郡县官员干的每一件事,无论好坏,都要在审计时公之于众。
许九堂堂彻侯之身,万一在任上做了什么错事,在审计时被丞相——更或直接就是天子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个狗血淋头,以后在贵族伙伴们面前,还如何抬得起头?
文也不行,武也不行,许九万念俱灰之下,便只得考虑起行商。
当然,如今汉室,对商人的鄙视依旧十分严重。
所以许九,又或是其他的功侯贵族们做生意,也都并非亲自下场,而是扶持一家商户,并为这双手套提供一定的便利、扶持。
许九的商业天赋还不错。
至少胆子够大。
而在这个时代,单就是一个胆子够大,就让许九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只是归根结底:行商,得到的依旧还是钱,满足的依旧只是物质欲望。
——所以许九很空虚。
酒肉再好,也总有吃腻的一天;
女人再美,也总有腿软的一天。
但凡自己能得到的,许九都已经得到了;
没得到的,许九也已经确定自己无法得到。
于是,许九就没有欲望了。
没有欲望,又闲来无事,许九剩下的人生,自然就只剩下消磨时间。
小说,是消遣时间极好的方式。
尤其是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将一个个人物塑造成形,跃然纸上,更是会让人生出莫名的成就感!
再听到旁人说起自己的作品,更甚是对自己赞不绝口……
在写小说之后,许九终于得到了认可。
终于得到了单纯针对自己,和父祖余荫、彻侯身份没有丝毫关系的由衷拜服。
原以为这一世,自己大概就是这样了——彻侯爵位保证地位,万贯家财保证生活,外加小说消遣时光,丰富精神世界;
这辈子,也就这样了。
却不料自己最喜爱,却又最拿不出手的爱好,竟然反倒引起了天子的注意……
“唉~”
“陛下,这是要编排太后啊……”
“连陛下都能凭《汉宫密录》查到我的头上,那日后,太后自也能查到。”
“要是因此惹恼了太后……”
回到家中,按照过去这些年的习惯,第一时间将空白竹简摊开;
看着竹简旁的砚台,许久却一时陷入纠结之中。
用小说映射某人、某物,对许九而言不在话下。
但事关当朝太皇太后——尤其还是活着的太皇太后,许久就算胆子再大,也还没作死到这种地步。
可这件事,是才刚即位的新君刘荣所交代;
从方才的状况来看,这位新君,手里怕也是捏着许九不少把柄。
从了,会让太后恼怒;
不从,会惹天子发火,更甚是名正言顺的治罪。
“唉……”
“好端端的,祖孙二人怎还较上劲了呢……”
“较劲就较劲吧,还都做的这么绝?”
“做祖母的要临朝,做孙子的,更是要编排自己的祖母……”
想到这里,许九无比庆幸当年,自己没有继续坚持走官场这条路。
——丫的没一个是东西!
只是眼下,究竟该怎么办呢……
许久思考了很久。
最终,得出了一个满朝公卿大臣,都基本一致的结论。
太皇太后再势大,也已经老了;
新君刘荣再势弱,也总还年轻。
更何况眼下,祖孙二人分明是分庭抗礼,谁也没比谁差到哪儿去。
结合此间种种,跟谁,已经不是选择题了。
而是对错判断题……
·
·
·
·
许久动作很快;
几乎只是三两日的功夫,长安街头巷尾的闲人懒汉们,便成了各茶馆、酒肆的‘座上宾’。
以至于长安城内,一度出现人们但凡见到个闲人懒汉坐在路边,便不由自主上前攀谈两句的诡异场景。
在过去,这是无法想象的。
——闲人懒汉,大都是不事生产的游侠众。
这些侠儿,心情好了能劫富济贫,心情不好也照样能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;
对于这个群体,寻常百姓普遍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
只是眼下,那个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老故事,却让长安城内的侠儿们成了香饽饽。
只要有侠儿讲故事,茶馆、酒肆就能围满好几圈人!
生意这么好,老板们自也是乐呵呵的数钱,懂事点的还不忘给‘说书先生’,也就是侠儿们免单。
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,自然是许九这位小说行业祖师爷,着实是有两把刷子……
“便说那巨阴人嫪毐,生的八尺二寸,甚是雄壮!”
“容貌那也是浓眉大眼,十里八乡的小细君、嫩寡妇,那就没一个不倾心的;”
“你说个头伟岸,容貌端正,那也就罢了——这样的公子哥说多不多,但一朝帝都咸阳城,也总还是有些贵公子的。”
“可偏这嫪毐,还有一门绝学!”
“便是凭这门绝学,嫪毐才得了个‘巨阴人’的诨号……”
长安北城,东市外的一间茶馆,此刻已经坐满了人。
本就不甚宽敞的茶馆,满共八方餐案,却是每张案几都围坐了七八个人!
没位置坐的也不恼,直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,又或是歇身倚在立柱,聚精会神的望向茶馆中央。
而在众人目光所集,一个约莫三十来岁,衣衫破旧,腰系长剑的男子就好像是一盘菜——直接盘腿坐在了案几上,眉飞色舞的讲起故事。
说到关键处,男子也不忘小小卖个关子,趁机接过掌柜含笑递上的水碗,砸吧着嘴灌下一口。
润好了嗓子,才神采奕奕的将上半身一俯,声线也陡然压下;
而后神秘兮兮道:“诸君可知这巨阴人,说的是个什么本事?”
聚精会神的听着,众人自然是配合着摇了摇头,即便偶有几人隐约猜到了什么,也同样是知趣的没有打断。
便见那大汉贱兮兮一笑,再将声线下压了些。
“嫪毐这人,能用那家伙事儿,把一只车轮举起来!”
“非但能举起来,还能一边走,一边让车轮在家伙事儿上转!”
“——呐,巨!阴!人!这么来的;”
“那家伙事儿,啧啧……”
说着,大汉啧啧称奇的摇了摇头,同时故作随意的抬手,捏了捏另一只手的手腕。
围观众人当即心领神会,纷纷看向大汉的手腕,再比划着大汉手腕的粗细,看向了各自的下身……
“嘶~~~!”
“这般粗大?”
“——还能转轮子!”
“那得有多……”
“咳咳咳咳咳……”
···
“这、这般粗大……”
“那不,咳咳,不得出啥事儿?”
很显然,这句话指的是这个作案工具太过危险,很可能伤到人。
却见那大汉猛地直起身,愤愤不平的拍了把大腿。
“可不就出事儿了嘛!”
“那家伙事儿,便是挂在牛身上,那也能把小母牛给弄迷糊;”
“挂人身上,那还了得?”
说完这句话,大汉飞快的昂起头,在茶馆外象征性的扫了一圈;
而后又飞速俯下身,对周围的人招招手,示意众人附耳过来。
“说是秦王政的母亲赵太后,听说嫪毐那转轮绝学,当即就坐不住啦……”
“不惜重金把嫪毐请去了咸阳宫,见过嫪毐那家伙事儿,那也顾不上什么太不太后、威不威仪的啦……”
“自那以后……咳咳…”
“自那以后,嫪毐就不转轮子啦……”
“改转太后啦………”
噗嗤!
再怎么说,也好歹是秦太后,长安又位于老秦根据地:关中;
听到嫪毐‘改转太后’,众人自是本能的不敢放声大笑,只噗嗤噗嗤憋笑破功。
至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,却是没什么人怀疑。
——嫪毐发动宫变,企图推翻当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嬴政,不过是发生在大几十年前的事。
而长安,又距离当时的事发地:咸阳城并不远。
单是凭着祖辈口口相传,这个故事也能传到现在。
更何况自那时传到现在的,不单是‘嫪毐宫变’四个大字;
还有嫪毐和赵太后生下的两个孽种,以及自那以后,赵太后终身都被始皇嬴政监禁。
而‘巨阴人’嫪毐,也落得个车裂的下场……
“唉~”
“也不能怪秦王政不孝顺亲母啊……”
“母亲做出这样的事,将亡父,乃至国家的脸都给丢尽了!”
“——就算出于孝道,不能伤及母亲性命,也总要把母亲给关起来;”
“免得什么时候,再来个巨阴人引诱太后……”
故事讲完,围观众人自然就进入了延伸讨论阶段。
毕竟是关中老秦人众所周知的真事儿,大家伙讨论起来,自也就没了太多顾及。
——太宗皇帝除诽谤令,便是本朝的事,农户黔首也能说上一说;
更何况还是享‘暴秦’之名的前秦?
见众人讨论起秦王政是否孝顺——尤其是有人站出来,表示秦王政再怎么样,也不能囚禁自己的母亲,大汉的嘴角之上,却是露出一个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笑意。
“如此,便算是使命完成了吧?”
“嘿嘿嘿……”
“不过半日,这就到手一千钱……”
如是想着,大汉只嘿笑着摇摇头,耐人寻味的看向那几个出口反驳众人,指责秦王政不孝的老顽固。
“秦王政囚禁其母,或许是不孝。”
“但你二人可知秦王政,为何要这么做?”
“又可知,嫪毐区区一伪宦——半个阉人,如何能调兵发起宫变?”
“更甚是和赵太后诞下野种二人,却瞒了秦王足足数年之久?”
大汉这话一出,开口反驳的那两位老者当即默然。
还能是为何?
左右不过是傍上了太后的大腿,掌握了太后的力量呗……
那赵太后也真不要脸;
好端端一个寡妇,不顾太后尊仪乱搞也就罢了,还和那巨阴人嫪毐诞下了子嗣;
非但诞了子嗣,而且还是两个!
一个能说是意外,两个,那可就是猖狂至极了……
单只是如此,都还则罢了;
到头来,居然还借兵给奸夫嫪毐,帮嫪毐发动宫变,险些推翻了自己和先王的儿子,也就是后来的始皇帝陛下……
“赵太后有意废除秦王政,那是由来已久的事!”
“秦王政十二岁即位,先王临终时遗诏:太后及相国吕不韦暂代朝政,待秦王政加冠成人,再还政于王。”
“但等秦王及了冠,赵太后和吕不韦却是百般推脱,就是不远给秦王政行冠礼——生怕秦王加了冠,就要夺走赵太后和吕不韦手里的大权!”
···
“都拖到秦王政二十二岁,眼看着再也拖不下去了,赵太后才不情不愿的下令:给秦王政行冠礼。”
“但终归是心有不甘,便借兵给了嫪毐,让嫪毐刺王杀驾,扶赵太后和嫪毐的子嗣即秦王之位……”
神秘兮兮的丢下这番话,让在场众人都陷入沉思,大汉只暗下一笑;
洒然灌下一口水,朝身旁的掌柜甩去几枚铜钱,便昂首挺胸的走出了茶馆。
而在大汉离开之后,众人却是久久都没能回过神。
“这……”
···
“这天底下,当真有这么狠心的母亲?”
“做母亲的,如何能这般狠心呢……”
贵族生活,实在是无趣的很。
后世有一句话:人类的物质欲望,是无穷无尽的。
但很少有人想到,物质欲望,并非无穷无尽;
而是说出‘物资欲望无穷无尽’这句话的人,没有,也必定无法达到那个极少数人才能达到的顶尖层面。
——物质欲望,是有尽头的。
当你拥有你所能想象到的一切物质时,你的物质欲望就会彻底得到满足。
紧随其后的,便是索然无味的贤者时间。
之后,对物质的欲望,就会自然而然的转化为对权力,以及对地位的渴望。
许九是贵族;
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,许九便几乎能得到世上所存在的一切。
但作为贵族后人,或者说是即将落魄的贵族,许九在物质欲望得到满足之后,却根本无法满足自己对权力的欲望。
地位是有的;
但也只是虚尊,而且还是靠父祖的威名,和许九本身并无关系。
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,许九当然渴望得到认可。
无论是大众由衷的钦佩、同阶级的贵族由衷的敬服,又或是‘顶头上司’——天子的赞赏,都是许九这个生活枯燥而又乏味的贵族所渴望的。
但理想和现实,却总是背道而驰。
许九想过策马奔腾,于战场上建功立业;
结果直到三年前,大行皇帝三年那场吴楚七国之乱,许九才终于得到建功立业的机会。
耗资数以千万,大张旗鼓的装备起百十家兵,雄赳赳气昂昂上了战场!
在战场上走了一圈下来——精锐亲卫死伤大半不说,武勋更是压根儿没捞到多少。
满共就十几颗叛军首级,堪堪达到许九的kpi,只得了个口头嘉奖,外加下一代宋子侯不必降爵的赏赐。
——汉家的爵位,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世袭,而是世代累降。
或者应该说,是原则上,每一个人从父亲处承袭的爵位,都会比父亲的原爵位低一级。
你爹是彻侯,你就该袭爵关内侯;
你爹是大上造,你袭爵就是少上造。
你爹是最低一级的公士,那好吧,伱也是公士——实在没有再往下降的空间了。
之所以说是‘原则上’,是因为这世代累降爵位的规定,是有避免方式的。
就好比许九的祖父,作为开国元勋,被太祖高皇帝敕封为彻侯;
按理来说,到了许九的父亲这一辈,宋子侯国就该被降为关内侯。
但许九的祖父在得封之后,按照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,自掏腰包组织兵马,随朝堂大军参加了几场异姓诸侯叛乱的平定。
kpi达成,侯世子——也就是许九的父亲,才得以承袭宋子侯国的彻侯爵位,而非关内侯爵位。
一样的道理:到了许九这一代,宋子侯国,原本也还是该降爵为关内侯。
但许九的父亲运气很好,在那场匈奴人兵峰直至长安的动荡中,捞了个偏将军的将印,斩获了几颗匈奴先锋首级。
虽然并非亲自斩获,而是麾下将士所得,但许九的父亲也就借此完成了kpi,成功避免了爵位累降。
但在亲自上过战场之后,许九却发现自己并没有军事天赋。
——花了几千万钱,恨不能把那百来个家丁武装到牙齿,结果捞回来的武勋,才堪堪够保住下一代宋子侯的彻侯爵位?
那得砸多少钱,才能真正建功立业,甚至是得到溢封食邑的赏赐?
许九算了算,一场吴楚七国之乱,自己投入了侯国将近十五年的产出;
于是,许九很快便得出结论:这种砸钱买‘不降爵名额’的蠢事儿,每代人干一回,确保下一代不丢掉彻侯爵位就够了。
但凡多来一两回,就算保住了彻侯爵位,怕也是要穷的叮当响,根本维持不住彻侯的威仪。
军事不行,许九又想到了宦途。
汉家的贵族,并非不能做官。
——如今汉家,甚至至今都还保留着‘非彻侯不能为相’的政治潜规则。
彻侯身份,能为许九带来很大的政治助力,起点也会很高;
但凡做出点成绩——甚至但凡能在一个位置上,稳稳坐几年不犯大错,就基本能往九卿的方向靠拢了。
只可惜,在尝试性了解过官场之后,许九再次选择了放弃。
太难了……
做官,实在是太难了……
尤其如今汉家每年一小计,三年一大计;
郡县官员干的每一件事,无论好坏,都要在审计时公之于众。
许九堂堂彻侯之身,万一在任上做了什么错事,在审计时被丞相——更或直接就是天子,当着满朝文武的面骂个狗血淋头,以后在贵族伙伴们面前,还如何抬得起头?
文也不行,武也不行,许九万念俱灰之下,便只得考虑起行商。
当然,如今汉室,对商人的鄙视依旧十分严重。
所以许九,又或是其他的功侯贵族们做生意,也都并非亲自下场,而是扶持一家商户,并为这双手套提供一定的便利、扶持。
许九的商业天赋还不错。
至少胆子够大。
而在这个时代,单就是一个胆子够大,就让许九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只是归根结底:行商,得到的依旧还是钱,满足的依旧只是物质欲望。
——所以许九很空虚。
酒肉再好,也总有吃腻的一天;
女人再美,也总有腿软的一天。
但凡自己能得到的,许九都已经得到了;
没得到的,许九也已经确定自己无法得到。
于是,许九就没有欲望了。
没有欲望,又闲来无事,许九剩下的人生,自然就只剩下消磨时间。
小说,是消遣时间极好的方式。
尤其是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,将一个个人物塑造成形,跃然纸上,更是会让人生出莫名的成就感!
再听到旁人说起自己的作品,更甚是对自己赞不绝口……
在写小说之后,许九终于得到了认可。
终于得到了单纯针对自己,和父祖余荫、彻侯身份没有丝毫关系的由衷拜服。
原以为这一世,自己大概就是这样了——彻侯爵位保证地位,万贯家财保证生活,外加小说消遣时光,丰富精神世界;
这辈子,也就这样了。
却不料自己最喜爱,却又最拿不出手的爱好,竟然反倒引起了天子的注意……
“唉~”
“陛下,这是要编排太后啊……”
“连陛下都能凭《汉宫密录》查到我的头上,那日后,太后自也能查到。”
“要是因此惹恼了太后……”
回到家中,按照过去这些年的习惯,第一时间将空白竹简摊开;
看着竹简旁的砚台,许久却一时陷入纠结之中。
用小说映射某人、某物,对许九而言不在话下。
但事关当朝太皇太后——尤其还是活着的太皇太后,许久就算胆子再大,也还没作死到这种地步。
可这件事,是才刚即位的新君刘荣所交代;
从方才的状况来看,这位新君,手里怕也是捏着许九不少把柄。
从了,会让太后恼怒;
不从,会惹天子发火,更甚是名正言顺的治罪。
“唉……”
“好端端的,祖孙二人怎还较上劲了呢……”
“较劲就较劲吧,还都做的这么绝?”
“做祖母的要临朝,做孙子的,更是要编排自己的祖母……”
想到这里,许九无比庆幸当年,自己没有继续坚持走官场这条路。
——丫的没一个是东西!
只是眼下,究竟该怎么办呢……
许久思考了很久。
最终,得出了一个满朝公卿大臣,都基本一致的结论。
太皇太后再势大,也已经老了;
新君刘荣再势弱,也总还年轻。
更何况眼下,祖孙二人分明是分庭抗礼,谁也没比谁差到哪儿去。
结合此间种种,跟谁,已经不是选择题了。
而是对错判断题……
·
·
·
·
许久动作很快;
几乎只是三两日的功夫,长安街头巷尾的闲人懒汉们,便成了各茶馆、酒肆的‘座上宾’。
以至于长安城内,一度出现人们但凡见到个闲人懒汉坐在路边,便不由自主上前攀谈两句的诡异场景。
在过去,这是无法想象的。
——闲人懒汉,大都是不事生产的游侠众。
这些侠儿,心情好了能劫富济贫,心情不好也照样能杀人放火,无恶不作;
对于这个群体,寻常百姓普遍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。
只是眼下,那个流传于街头巷尾的老故事,却让长安城内的侠儿们成了香饽饽。
只要有侠儿讲故事,茶馆、酒肆就能围满好几圈人!
生意这么好,老板们自也是乐呵呵的数钱,懂事点的还不忘给‘说书先生’,也就是侠儿们免单。
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,自然是许九这位小说行业祖师爷,着实是有两把刷子……
“便说那巨阴人嫪毐,生的八尺二寸,甚是雄壮!”
“容貌那也是浓眉大眼,十里八乡的小细君、嫩寡妇,那就没一个不倾心的;”
“你说个头伟岸,容貌端正,那也就罢了——这样的公子哥说多不多,但一朝帝都咸阳城,也总还是有些贵公子的。”
“可偏这嫪毐,还有一门绝学!”
“便是凭这门绝学,嫪毐才得了个‘巨阴人’的诨号……”
长安北城,东市外的一间茶馆,此刻已经坐满了人。
本就不甚宽敞的茶馆,满共八方餐案,却是每张案几都围坐了七八个人!
没位置坐的也不恼,直接就一屁股坐在地上,又或是歇身倚在立柱,聚精会神的望向茶馆中央。
而在众人目光所集,一个约莫三十来岁,衣衫破旧,腰系长剑的男子就好像是一盘菜——直接盘腿坐在了案几上,眉飞色舞的讲起故事。
说到关键处,男子也不忘小小卖个关子,趁机接过掌柜含笑递上的水碗,砸吧着嘴灌下一口。
润好了嗓子,才神采奕奕的将上半身一俯,声线也陡然压下;
而后神秘兮兮道:“诸君可知这巨阴人,说的是个什么本事?”
聚精会神的听着,众人自然是配合着摇了摇头,即便偶有几人隐约猜到了什么,也同样是知趣的没有打断。
便见那大汉贱兮兮一笑,再将声线下压了些。
“嫪毐这人,能用那家伙事儿,把一只车轮举起来!”
“非但能举起来,还能一边走,一边让车轮在家伙事儿上转!”
“——呐,巨!阴!人!这么来的;”
“那家伙事儿,啧啧……”
说着,大汉啧啧称奇的摇了摇头,同时故作随意的抬手,捏了捏另一只手的手腕。
围观众人当即心领神会,纷纷看向大汉的手腕,再比划着大汉手腕的粗细,看向了各自的下身……
“嘶~~~!”
“这般粗大?”
“——还能转轮子!”
“那得有多……”
“咳咳咳咳咳……”
···
“这、这般粗大……”
“那不,咳咳,不得出啥事儿?”
很显然,这句话指的是这个作案工具太过危险,很可能伤到人。
却见那大汉猛地直起身,愤愤不平的拍了把大腿。
“可不就出事儿了嘛!”
“那家伙事儿,便是挂在牛身上,那也能把小母牛给弄迷糊;”
“挂人身上,那还了得?”
说完这句话,大汉飞快的昂起头,在茶馆外象征性的扫了一圈;
而后又飞速俯下身,对周围的人招招手,示意众人附耳过来。
“说是秦王政的母亲赵太后,听说嫪毐那转轮绝学,当即就坐不住啦……”
“不惜重金把嫪毐请去了咸阳宫,见过嫪毐那家伙事儿,那也顾不上什么太不太后、威不威仪的啦……”
“自那以后……咳咳…”
“自那以后,嫪毐就不转轮子啦……”
“改转太后啦………”
噗嗤!
再怎么说,也好歹是秦太后,长安又位于老秦根据地:关中;
听到嫪毐‘改转太后’,众人自是本能的不敢放声大笑,只噗嗤噗嗤憋笑破功。
至于这个故事的可信度,却是没什么人怀疑。
——嫪毐发动宫变,企图推翻当时还是秦王的始皇嬴政,不过是发生在大几十年前的事。
而长安,又距离当时的事发地:咸阳城并不远。
单是凭着祖辈口口相传,这个故事也能传到现在。
更何况自那时传到现在的,不单是‘嫪毐宫变’四个大字;
还有嫪毐和赵太后生下的两个孽种,以及自那以后,赵太后终身都被始皇嬴政监禁。
而‘巨阴人’嫪毐,也落得个车裂的下场……
“唉~”
“也不能怪秦王政不孝顺亲母啊……”
“母亲做出这样的事,将亡父,乃至国家的脸都给丢尽了!”
“——就算出于孝道,不能伤及母亲性命,也总要把母亲给关起来;”
“免得什么时候,再来个巨阴人引诱太后……”
故事讲完,围观众人自然就进入了延伸讨论阶段。
毕竟是关中老秦人众所周知的真事儿,大家伙讨论起来,自也就没了太多顾及。
——太宗皇帝除诽谤令,便是本朝的事,农户黔首也能说上一说;
更何况还是享‘暴秦’之名的前秦?
见众人讨论起秦王政是否孝顺——尤其是有人站出来,表示秦王政再怎么样,也不能囚禁自己的母亲,大汉的嘴角之上,却是露出一个不易为人所察觉的笑意。
“如此,便算是使命完成了吧?”
“嘿嘿嘿……”
“不过半日,这就到手一千钱……”
如是想着,大汉只嘿笑着摇摇头,耐人寻味的看向那几个出口反驳众人,指责秦王政不孝的老顽固。
“秦王政囚禁其母,或许是不孝。”
“但你二人可知秦王政,为何要这么做?”
“又可知,嫪毐区区一伪宦——半个阉人,如何能调兵发起宫变?”
“更甚是和赵太后诞下野种二人,却瞒了秦王足足数年之久?”
大汉这话一出,开口反驳的那两位老者当即默然。
还能是为何?
左右不过是傍上了太后的大腿,掌握了太后的力量呗……
那赵太后也真不要脸;
好端端一个寡妇,不顾太后尊仪乱搞也就罢了,还和那巨阴人嫪毐诞下了子嗣;
非但诞了子嗣,而且还是两个!
一个能说是意外,两个,那可就是猖狂至极了……
单只是如此,都还则罢了;
到头来,居然还借兵给奸夫嫪毐,帮嫪毐发动宫变,险些推翻了自己和先王的儿子,也就是后来的始皇帝陛下……
“赵太后有意废除秦王政,那是由来已久的事!”
“秦王政十二岁即位,先王临终时遗诏:太后及相国吕不韦暂代朝政,待秦王政加冠成人,再还政于王。”
“但等秦王及了冠,赵太后和吕不韦却是百般推脱,就是不远给秦王政行冠礼——生怕秦王加了冠,就要夺走赵太后和吕不韦手里的大权!”
···
“都拖到秦王政二十二岁,眼看着再也拖不下去了,赵太后才不情不愿的下令:给秦王政行冠礼。”
“但终归是心有不甘,便借兵给了嫪毐,让嫪毐刺王杀驾,扶赵太后和嫪毐的子嗣即秦王之位……”
神秘兮兮的丢下这番话,让在场众人都陷入沉思,大汉只暗下一笑;
洒然灌下一口水,朝身旁的掌柜甩去几枚铜钱,便昂首挺胸的走出了茶馆。
而在大汉离开之后,众人却是久久都没能回过神。
“这……”
···
“这天底下,当真有这么狠心的母亲?”
“做母亲的,如何能这般狠心呢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