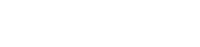第203章 谁知道~呢
从天子启新元三年的秋收日开始,类似的事,在关中大地层出不穷。
——百姓民农获,缴税,而后卖粮。
结果卖粮的时候,发现了自家粮食被税吏动了手脚,称出来的数目不对。
民不与官斗;
就算意识到不对劲,憨厚老实的农户,也大都不敢和官府作对。
但在这种时候,汉家‘以孝治国’的另一政治果实:乡三老群体站了出来,并充分发挥出了主观能动性。
基本都是类似的状况;
农户们发现不对劲,便找上那位德高望重,享誉十里八村儿,年纪足有七老八十的乡三老一告!
而后,便是一个又一个老大爷拄着鸠杖,像植物大战僵尸里,被打破报纸的僵尸大爷一样,怒气冲冲的追着本县税吏一顿猛捶。
——一时间,关中大地鸡飞狗跳,官不聊生。
偏偏地方郡县还不敢往上告!
怎么告?
说本县税吏中饱私囊,被乡三老发现了;
于是便被挥着先太宗皇帝,乃至太祖高皇帝亲自赐下的鸠杖的乡三老,从南天门追到了蓬莱东路,一路追一路砸,眼皮都没眨一下?
真要有人敢这么往上告,且不说头顶上的乌纱帽还保不保得住;
就算真告到了如今汉家的掌舵人——监国太子刘荣的面前,按照这位储君的脾性,怕是只会戏谑的问上一句:乡三老们一大把年纪,追那么远一段路都没眨眼皮,眼睛会不会干啊……
往上告不行,往下压,也同样行不通。
——那可是乡三老!
按照汉家现有的法律规定,受赐几杖/鸠杖,年过八十的乡三老,那是连见了皇帝,都不用拜的!
不是不用跪,而是不用拜!
躬身拱手都不用——只要有那个魄力,哪怕双手背在身后,昂首挺胸的对皇帝冷哼两声,也完全挑不出法律层面的毛病。
非但不用拜,反而是皇帝要主动上前,虚扶一把、问候一番,再象征性的听一听老同志,对国家大事的指导意见。
如果真发生乡三老见皇帝而不拜,甚至明显表露出对皇帝的恼怒、厌恶时,皇帝还要老老实实走上前去,谦逊的问:朕是做了什么错事,让老丈如此大动肝火啊?
···
至于乡三老手中,那人手一杆的几杖,即鸠杖,更是不亚于后世小说读物中,诸如‘尚方宝剑’之类的大杀器!
对于鸠杖,汉家虽然没有类似‘上打昏君,下揍奸臣’之类的明文规定,但只需要说一点,便足以说明这个东西的厉害。
——汉太后手里,拿的也是鸠杖!
从法理角度上来说,若汉太后想要对皇帝进行体罚,如打板子之类,那唯一合法、合规的方式,便是用手中的鸠杖打!
因为太后的鸠杖,往往也同样是先皇所赐。
一如先皇驾崩时,会留遗诏指定继承人一样——在那封遗诏中,先帝同样会留下‘尊太子母:皇后某氏为太后,赐鸠杖’的安排。
所以,太后用自己的鸠杖打皇帝,是扯着先帝的虎皮,替死去先帝教训不肖子孙。
这么说来,问题就一目了然了。
——太后一介妇人,拿着一杆先帝赐下的鸠杖,就能肆无忌惮的往皇帝身上招呼;
俺老汉虽是农户,手里的鸠杖,却也是先帝所赐!
虽是不敢学太后,把这鸠杖往皇帝身上招呼,但你一個千八百石的官儿,俺老汉总还是打的得吧?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根据汉家现存的,关于乡三老这一特殊特权阶级的规定,乡三老见官、面圣不拜(理论上是面圣不拜,实际上是面圣不跪,却也还是要给皇帝留点面子,拱手弯腰意思意思的);
凡郡县有司属衙畅通无阻——想进就进,想走就走,根本没人能拦,也没人敢拦。
非但进出自由,畅通无阻,郡县主管得知三老上门拜会,甚至还要亲自奉茶招待!
到了朝堂三公九卿有司,虽然稍差些,但理论上也还是进出自由,实际上只需要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,便可以自由进出。
甚至就连皇宫,也不是完全去不得!
只需要走到宫门外,让宫门处的禁卫通传一声:某郡某县某乡三老某某,请朝天子;
大多数情况下,只要皇帝不是忙的饭都顾不上吃,就都会见上一面。
哪怕这个手持鸠杖的老爷子没啥正事儿,就是想单纯见自己一面,也同样如此。
毫不夸张的说:乡三老,便是汉家在‘以孝治国’的主体国策之上延伸而来,且不需要支付俸禄的编外纪检委!
只是这个群体,往往都是由长寿——而且是过度长寿的退役军人、退休官僚群体充任;
平日里,地方郡县只要别做的太过火,别闹到天怒人怨的地步,这些‘过来人’便往往都会睁只眼闭只眼,不会太为难郡县父母官。
——大家都是当过官儿的,谁还不知道汉官不易?
但这一次,刘荣出于宏观调控、稳定粮食价格的考虑,而临时设置的治粟都尉,却意外捅破了这层官僚群体心照不宣的政治潜规则。
而这意外捅出来的马蜂窝,却也是为刘荣监国期间的汉家,带来了一笔相当不菲的政治成果……
·
·
·
·
“平日里,老大人不怎见客;”
“孤也是前脚刚获立为储,粮食的事儿都还没忙完,便又得了监国大权。”
“——忙啊~”
“实在是抽不出闲暇,亲自登门拜会老大人……”
上林苑,猎场行宫外,一处偏僻清雅的府邸之中,刘荣终于时隔多年,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表叔祖:章武侯窦广国。
刘荣约莫记得:上一次见到这位的时候,都得追溯到薄太皇太后的葬礼。
事实上,自打当年,在丞相大位的角逐竞争中,输给了前丞相、现太子太师申屠嘉,窦广国便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。
——不心灰意冷也没办法啊!
一个外戚的身份,让到手的丞相之位都飞走了,除了宅在家里修仙,窦广国还能怎么办?
只是这修仙,也不是谁都能修的明白的。
想当年,太祖高皇帝在位时,留侯张良修仙,修的那叫一个仙风道骨,鹤发童颜;
若非拿不出腾云驾雾之类的真本事,那活脱脱就是个神仙在世!
再看看窦广国——看看此刻,正在含笑招待刘荣的窦广国,面颊内陷,眼圈发黑,皮肤外层甚至透着一抹极不自然的紫!
都不用仪器检测,刘荣就能直接给出诊断:妥妥的重金属中毒。
只是知道归知道,刘荣也没办法去劝,便只得自说自话般,同这位表叔祖打开了话匣。
今日,刘荣的目的只有一个:见窦广国一面,好让朝野内外,乃至天下人都看到自己这个太子,是怎么对自己的盟友的——是怎么对待‘落难’的政治盟友的。
至于具体和窦广国聊些什么,却是没什么重要的了。
——问候一阵,寒暄一番,联络联络感情,巩固巩固窦氏和太子宫的盟友关系,也就差不多了。
但稍有些出乎刘荣预料的是:在世人认知中,早已经‘不食五谷杂粮’,深陷修仙之道无法自拔的章武侯窦广国,却似乎十分珍惜这次机会。
“家上言重,言重……”
“刘氏的男儿,那都是肩负宗庙、社稷,系天下安危于己身的。”
“——尤其家上,还是我汉家的太子储君,是宗庙、社稷日后的指望。”
“今更肩负监国之责,莫说是抽不出闲暇——便是抽得出,老臣,也万不敢因私事,而对家上多行叨扰……”
不卑不亢的一番话,算是给足了刘荣面子,也顺带展现出了窦氏外戚一族,当代话事人的精神风貌。
——说这么一段话,能脸不红气不喘的说下来,这对过去的窦广国而言,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
既然眼下做到了……
“老大人龙精虎猛,这是~”
“断药了?”
略有些冒犯的一问,却引得窦广国颇有些感慨的笑着摇摇头,又面带唏嘘的长叹一口气。
“唉~”
“这些年,为了替兄长,再向天借几年命书,老臣,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……”
“——明知那寻仙问道,是冥冥之中不可触碰、凡人之躯所不可得之物;”
“明知就连秦王政,都不曾得偿所愿,却也还是不愿放弃这或有或无得机会……”
···
“炼丹数年,不知靡费了多少钱物,更以身试丹药,身子也吃成了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。”
“最终,却也还是没能将兄长,再多留在这人世间几年……”
“——偏偏东宫,近几年又实在不大太平;”
“兄长撒手人寰,去见了先帝,老臣独木难支,也实在是难有作为……”
窦广国唏嘘一语,刘荣却是随之默然。
窦广国这番话,无疑是隐晦的指出:自己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尽可能把东宫窦太后往正道上引;
就连寻仙问道、炼丹试药,都是窦广国怕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,才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,为兄长窦长君多赚几年寿数。
结果功败垂成,窦长君还是走了,侯世子窦彭祖袭爵,做了刘荣的太子家令。
窦氏一族上上下下,自此便都要指望窦广国一人不说,就连东宫——连三不五时脑子抽抽的窦太后,都得窦广国独自想办法去搞定。
从客观角度而言,这些年,窦氏一族在‘规劝窦太后’这件事上所做的努力,成效几乎约等于零。
无论是最开始储君太弟,还是后来的一系列动荡——一系列因窦太后而引发的动荡,窦氏外戚一族,都没能起到哪怕丝毫‘规劝’的作用。
但有些时候,没做到,却并不意味着没意义。
尤其是对于刘荣——对于封建君主而言,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,做没做,往往比‘做没做成’更重要。
什么我不问过程,只要结果,那都是言情小说里霸道总裁的人生格言;
封建君主要的,是既要做成,也要办的漂亮!
就算没办成,过程也得漂亮。
用更直白的话来说:成功与否,取决于能力,努力与否,则取决于态度。
对于窦氏这么一门外戚,尤其还是太后家的外戚而言,有个态度,往往便足矣。
至于能力?
刘荣恨不能汉家的外戚,都是空有态度,没有能力的机器人。
吕氏有能力吧?
薄氏——薄昭有能力吧?
再往后说,霍光总是有能力的吧?
你问问古往今来,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:谁想要自家的王朝出个诸吕,出个薄昭,更或是直接出个霍光?
“老大人心系宗庙、社稷,孤,谨谢。”
“只人力有时穷——东宫太后母仪天下,纵是父皇,也偏只能哄着、劝着;”
“若说要劝,过去倒是有个袁盎,能时不时劝进去几句。”
“只日后……”
如是说着,刘荣也不由得一阵摇头唏嘘,似是为袁盎的死,而感到无比的遗憾。
但事实上,朝野内外心里都跟个明镜似的。
——袁盎一条命,换来梁王刘武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,要说这天底下谁最高兴,还就是如今的监国太子刘荣!
若不是袁盎以身殉国,为刘荣踢开了梁王刘武这个威胁者?
呵;
眼下,刘荣别说是太子监国了,怕不是还盘算着该怎么应对东宫窦太后、怎么应对那句‘储君皇太弟’。
见刘荣只简单地肯定自己——肯定了窦氏一族,在‘劝阻太后’一事上的努力,又明确指出希望不大,窦广国也不由得默然。
隐约感觉到刘荣不愿意多聊有关东宫太后的事,窦广国便也顺着话头,将话题不着痕迹的一转。
“说是梁王奉诏,随陛下去了上林游猎?”
闻言,刘荣只稍一颔首。
“是。”
“——梁王私逃那段时日,父皇和皇祖母,闹得很不愉快。”
“就算梁王找回来了,皇祖母也还是紧闭长乐宫门,不愿见人。”
···
“唉~”
“父皇也不容易啊~”
“平白受了冤屈不说,人都找回来了,还得再屈尊降贵的哄着,以求老太后能再展笑颜。”
“——父皇,当真是这天底下,最孝顺不过的人了。”
“换做谁,碰上父皇那档子糟心事,怕是都不会做到父皇那个份儿上。”
刘荣脸不红心不跳,直言不讳的拍起了皇帝老爹的马屁;
而在对座,窦广国却是眼中稍闪过一抹精光,似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新闻。
——梁王!
刘荣,居然直呼梁王刘武为‘梁王’!
不是且君臣、且叔侄的‘王叔’,而是只论君臣,不论亲缘的‘梁王’!
“嘶……”
“陛下,难道有心要置梁王于死地?”
“若不然,太子为何会如此这般……”
···
“也不对啊?”
“若陛下要治死梁王,又何必大费周折,又是赐宴、又是邀约同猎?”
“更何况太后那边……”
刘荣大咧咧一句话,甚至是极不起眼的一声‘梁王’,却是惹得窦广国心绪百转,眨眼的功夫,脑子都不知道转了几个来回。
始终不明白其中关键,便稍带着狐疑,小心试探道:“此番入朝,梁王当是不会再像过去那般,坏祖宗规矩了吧?”
“闹出这么多事端来,便是太后,怕是也不好再留梁王了?”
正悠然品着茶,突闻窦广国这没由来的一问,刘荣心下也随即了然。
——梁王刘武‘坏祖宗规矩’,不外乎太祖刘邦当年,定下的诸侯入朝长安,最多只能留一个月的规矩。
而梁王刘武自打封王就藩,虽然满共也就来了长安十来回,却是没有哪怕一次,是没有‘坏祖宗规矩’的。
先帝时还好些,留够一个月,再找东宫薄太后、椒房殿窦皇后哭一哭,也顶多多留个十天半个月;
到了当今天子启这一朝,那可就是彻底放浪形骸了——没个三五月,朝堂内外递给天子启,指责梁王刘武‘眷恋不去’的奏疏,就别想翻出什么浪!
尤其是吴楚之乱爆发前的一年,梁王刘武一来长安,那就是留了足足七八个月!
算上来回路途,都快留了一年了!
如此特权——如此明目张胆的特权,自然是东宫窦太后无底线的纵容,外加天子启的推波助澜,以及那段特殊的岁月,梁王刘武在汉家的特殊政治地位。
而此刻,窦广国毫无征兆的问起此番,梁王刘武还会不会像以往那般眷恋不去,在长安一留就是小半年,其目的,也是不言而喻……
“谁又说的准呢~”
“若是皇祖母还讲点道理,当是不会再容许梁王坏规矩的。”
“但皇祖母不讲道理,那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“万一皇祖母要闹,父皇怕也只能由着梁王吧……”
语带愁苦的道出此语,刘荣便再度端起茶碗,做出一个‘我好气,但我也没办法’的憋闷之态。
见刘荣如此反应,窦广国只不着痕迹的垂下眸;
心下有了数,便也不再多问,转而和刘荣聊起窦婴、窦彭祖二人。
一番交谈下来,也算是宾主尽欢,双方各自达成了目的,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。
只是刘荣离开之后,窦广国却是紧紧皱起了眉头,坐在客堂内,小半个时辰都没能回过神。
“太子……”
“陛下……”
“梁王………”
···
“唉~”
“阿姊,已是……”
“唉……”
···
“只求阿姊,万莫要一错再错吧……”
“若不然,待太子即了大位……”
(本章完)
从天子启新元三年的秋收日开始,类似的事,在关中大地层出不穷。
——百姓民农获,缴税,而后卖粮。
结果卖粮的时候,发现了自家粮食被税吏动了手脚,称出来的数目不对。
民不与官斗;
就算意识到不对劲,憨厚老实的农户,也大都不敢和官府作对。
但在这种时候,汉家‘以孝治国’的另一政治果实:乡三老群体站了出来,并充分发挥出了主观能动性。
基本都是类似的状况;
农户们发现不对劲,便找上那位德高望重,享誉十里八村儿,年纪足有七老八十的乡三老一告!
而后,便是一个又一个老大爷拄着鸠杖,像植物大战僵尸里,被打破报纸的僵尸大爷一样,怒气冲冲的追着本县税吏一顿猛捶。
——一时间,关中大地鸡飞狗跳,官不聊生。
偏偏地方郡县还不敢往上告!
怎么告?
说本县税吏中饱私囊,被乡三老发现了;
于是便被挥着先太宗皇帝,乃至太祖高皇帝亲自赐下的鸠杖的乡三老,从南天门追到了蓬莱东路,一路追一路砸,眼皮都没眨一下?
真要有人敢这么往上告,且不说头顶上的乌纱帽还保不保得住;
就算真告到了如今汉家的掌舵人——监国太子刘荣的面前,按照这位储君的脾性,怕是只会戏谑的问上一句:乡三老们一大把年纪,追那么远一段路都没眨眼皮,眼睛会不会干啊……
往上告不行,往下压,也同样行不通。
——那可是乡三老!
按照汉家现有的法律规定,受赐几杖/鸠杖,年过八十的乡三老,那是连见了皇帝,都不用拜的!
不是不用跪,而是不用拜!
躬身拱手都不用——只要有那个魄力,哪怕双手背在身后,昂首挺胸的对皇帝冷哼两声,也完全挑不出法律层面的毛病。
非但不用拜,反而是皇帝要主动上前,虚扶一把、问候一番,再象征性的听一听老同志,对国家大事的指导意见。
如果真发生乡三老见皇帝而不拜,甚至明显表露出对皇帝的恼怒、厌恶时,皇帝还要老老实实走上前去,谦逊的问:朕是做了什么错事,让老丈如此大动肝火啊?
···
至于乡三老手中,那人手一杆的几杖,即鸠杖,更是不亚于后世小说读物中,诸如‘尚方宝剑’之类的大杀器!
对于鸠杖,汉家虽然没有类似‘上打昏君,下揍奸臣’之类的明文规定,但只需要说一点,便足以说明这个东西的厉害。
——汉太后手里,拿的也是鸠杖!
从法理角度上来说,若汉太后想要对皇帝进行体罚,如打板子之类,那唯一合法、合规的方式,便是用手中的鸠杖打!
因为太后的鸠杖,往往也同样是先皇所赐。
一如先皇驾崩时,会留遗诏指定继承人一样——在那封遗诏中,先帝同样会留下‘尊太子母:皇后某氏为太后,赐鸠杖’的安排。
所以,太后用自己的鸠杖打皇帝,是扯着先帝的虎皮,替死去先帝教训不肖子孙。
这么说来,问题就一目了然了。
——太后一介妇人,拿着一杆先帝赐下的鸠杖,就能肆无忌惮的往皇帝身上招呼;
俺老汉虽是农户,手里的鸠杖,却也是先帝所赐!
虽是不敢学太后,把这鸠杖往皇帝身上招呼,但你一個千八百石的官儿,俺老汉总还是打的得吧?
事实也确实如此。
根据汉家现存的,关于乡三老这一特殊特权阶级的规定,乡三老见官、面圣不拜(理论上是面圣不拜,实际上是面圣不跪,却也还是要给皇帝留点面子,拱手弯腰意思意思的);
凡郡县有司属衙畅通无阻——想进就进,想走就走,根本没人能拦,也没人敢拦。
非但进出自由,畅通无阻,郡县主管得知三老上门拜会,甚至还要亲自奉茶招待!
到了朝堂三公九卿有司,虽然稍差些,但理论上也还是进出自由,实际上只需要给出个说得过去的理由,便可以自由进出。
甚至就连皇宫,也不是完全去不得!
只需要走到宫门外,让宫门处的禁卫通传一声:某郡某县某乡三老某某,请朝天子;
大多数情况下,只要皇帝不是忙的饭都顾不上吃,就都会见上一面。
哪怕这个手持鸠杖的老爷子没啥正事儿,就是想单纯见自己一面,也同样如此。
毫不夸张的说:乡三老,便是汉家在‘以孝治国’的主体国策之上延伸而来,且不需要支付俸禄的编外纪检委!
只是这个群体,往往都是由长寿——而且是过度长寿的退役军人、退休官僚群体充任;
平日里,地方郡县只要别做的太过火,别闹到天怒人怨的地步,这些‘过来人’便往往都会睁只眼闭只眼,不会太为难郡县父母官。
——大家都是当过官儿的,谁还不知道汉官不易?
但这一次,刘荣出于宏观调控、稳定粮食价格的考虑,而临时设置的治粟都尉,却意外捅破了这层官僚群体心照不宣的政治潜规则。
而这意外捅出来的马蜂窝,却也是为刘荣监国期间的汉家,带来了一笔相当不菲的政治成果……
·
·
·
·
“平日里,老大人不怎见客;”
“孤也是前脚刚获立为储,粮食的事儿都还没忙完,便又得了监国大权。”
“——忙啊~”
“实在是抽不出闲暇,亲自登门拜会老大人……”
上林苑,猎场行宫外,一处偏僻清雅的府邸之中,刘荣终于时隔多年,再次见到了自己的表叔祖:章武侯窦广国。
刘荣约莫记得:上一次见到这位的时候,都得追溯到薄太皇太后的葬礼。
事实上,自打当年,在丞相大位的角逐竞争中,输给了前丞相、现太子太师申屠嘉,窦广国便已经有些心灰意冷了。
——不心灰意冷也没办法啊!
一个外戚的身份,让到手的丞相之位都飞走了,除了宅在家里修仙,窦广国还能怎么办?
只是这修仙,也不是谁都能修的明白的。
想当年,太祖高皇帝在位时,留侯张良修仙,修的那叫一个仙风道骨,鹤发童颜;
若非拿不出腾云驾雾之类的真本事,那活脱脱就是个神仙在世!
再看看窦广国——看看此刻,正在含笑招待刘荣的窦广国,面颊内陷,眼圈发黑,皮肤外层甚至透着一抹极不自然的紫!
都不用仪器检测,刘荣就能直接给出诊断:妥妥的重金属中毒。
只是知道归知道,刘荣也没办法去劝,便只得自说自话般,同这位表叔祖打开了话匣。
今日,刘荣的目的只有一个:见窦广国一面,好让朝野内外,乃至天下人都看到自己这个太子,是怎么对自己的盟友的——是怎么对待‘落难’的政治盟友的。
至于具体和窦广国聊些什么,却是没什么重要的了。
——问候一阵,寒暄一番,联络联络感情,巩固巩固窦氏和太子宫的盟友关系,也就差不多了。
但稍有些出乎刘荣预料的是:在世人认知中,早已经‘不食五谷杂粮’,深陷修仙之道无法自拔的章武侯窦广国,却似乎十分珍惜这次机会。
“家上言重,言重……”
“刘氏的男儿,那都是肩负宗庙、社稷,系天下安危于己身的。”
“——尤其家上,还是我汉家的太子储君,是宗庙、社稷日后的指望。”
“今更肩负监国之责,莫说是抽不出闲暇——便是抽得出,老臣,也万不敢因私事,而对家上多行叨扰……”
不卑不亢的一番话,算是给足了刘荣面子,也顺带展现出了窦氏外戚一族,当代话事人的精神风貌。
——说这么一段话,能脸不红气不喘的说下来,这对过去的窦广国而言,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事。
既然眼下做到了……
“老大人龙精虎猛,这是~”
“断药了?”
略有些冒犯的一问,却引得窦广国颇有些感慨的笑着摇摇头,又面带唏嘘的长叹一口气。
“唉~”
“这些年,为了替兄长,再向天借几年命书,老臣,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……”
“——明知那寻仙问道,是冥冥之中不可触碰、凡人之躯所不可得之物;”
“明知就连秦王政,都不曾得偿所愿,却也还是不愿放弃这或有或无得机会……”
···
“炼丹数年,不知靡费了多少钱物,更以身试丹药,身子也吃成了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。”
“最终,却也还是没能将兄长,再多留在这人世间几年……”
“——偏偏东宫,近几年又实在不大太平;”
“兄长撒手人寰,去见了先帝,老臣独木难支,也实在是难有作为……”
窦广国唏嘘一语,刘荣却是随之默然。
窦广国这番话,无疑是隐晦的指出:自己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尽可能把东宫窦太后往正道上引;
就连寻仙问道、炼丹试药,都是窦广国怕自己一个人应付不过来,才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,为兄长窦长君多赚几年寿数。
结果功败垂成,窦长君还是走了,侯世子窦彭祖袭爵,做了刘荣的太子家令。
窦氏一族上上下下,自此便都要指望窦广国一人不说,就连东宫——连三不五时脑子抽抽的窦太后,都得窦广国独自想办法去搞定。
从客观角度而言,这些年,窦氏一族在‘规劝窦太后’这件事上所做的努力,成效几乎约等于零。
无论是最开始储君太弟,还是后来的一系列动荡——一系列因窦太后而引发的动荡,窦氏外戚一族,都没能起到哪怕丝毫‘规劝’的作用。
但有些时候,没做到,却并不意味着没意义。
尤其是对于刘荣——对于封建君主而言,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,做没做,往往比‘做没做成’更重要。
什么我不问过程,只要结果,那都是言情小说里霸道总裁的人生格言;
封建君主要的,是既要做成,也要办的漂亮!
就算没办成,过程也得漂亮。
用更直白的话来说:成功与否,取决于能力,努力与否,则取决于态度。
对于窦氏这么一门外戚,尤其还是太后家的外戚而言,有个态度,往往便足矣。
至于能力?
刘荣恨不能汉家的外戚,都是空有态度,没有能力的机器人。
吕氏有能力吧?
薄氏——薄昭有能力吧?
再往后说,霍光总是有能力的吧?
你问问古往今来,历朝历代的封建帝王:谁想要自家的王朝出个诸吕,出个薄昭,更或是直接出个霍光?
“老大人心系宗庙、社稷,孤,谨谢。”
“只人力有时穷——东宫太后母仪天下,纵是父皇,也偏只能哄着、劝着;”
“若说要劝,过去倒是有个袁盎,能时不时劝进去几句。”
“只日后……”
如是说着,刘荣也不由得一阵摇头唏嘘,似是为袁盎的死,而感到无比的遗憾。
但事实上,朝野内外心里都跟个明镜似的。
——袁盎一条命,换来梁王刘武政治生命的彻底终结,要说这天底下谁最高兴,还就是如今的监国太子刘荣!
若不是袁盎以身殉国,为刘荣踢开了梁王刘武这个威胁者?
呵;
眼下,刘荣别说是太子监国了,怕不是还盘算着该怎么应对东宫窦太后、怎么应对那句‘储君皇太弟’。
见刘荣只简单地肯定自己——肯定了窦氏一族,在‘劝阻太后’一事上的努力,又明确指出希望不大,窦广国也不由得默然。
隐约感觉到刘荣不愿意多聊有关东宫太后的事,窦广国便也顺着话头,将话题不着痕迹的一转。
“说是梁王奉诏,随陛下去了上林游猎?”
闻言,刘荣只稍一颔首。
“是。”
“——梁王私逃那段时日,父皇和皇祖母,闹得很不愉快。”
“就算梁王找回来了,皇祖母也还是紧闭长乐宫门,不愿见人。”
···
“唉~”
“父皇也不容易啊~”
“平白受了冤屈不说,人都找回来了,还得再屈尊降贵的哄着,以求老太后能再展笑颜。”
“——父皇,当真是这天底下,最孝顺不过的人了。”
“换做谁,碰上父皇那档子糟心事,怕是都不会做到父皇那个份儿上。”
刘荣脸不红心不跳,直言不讳的拍起了皇帝老爹的马屁;
而在对座,窦广国却是眼中稍闪过一抹精光,似是听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新闻。
——梁王!
刘荣,居然直呼梁王刘武为‘梁王’!
不是且君臣、且叔侄的‘王叔’,而是只论君臣,不论亲缘的‘梁王’!
“嘶……”
“陛下,难道有心要置梁王于死地?”
“若不然,太子为何会如此这般……”
···
“也不对啊?”
“若陛下要治死梁王,又何必大费周折,又是赐宴、又是邀约同猎?”
“更何况太后那边……”
刘荣大咧咧一句话,甚至是极不起眼的一声‘梁王’,却是惹得窦广国心绪百转,眨眼的功夫,脑子都不知道转了几个来回。
始终不明白其中关键,便稍带着狐疑,小心试探道:“此番入朝,梁王当是不会再像过去那般,坏祖宗规矩了吧?”
“闹出这么多事端来,便是太后,怕是也不好再留梁王了?”
正悠然品着茶,突闻窦广国这没由来的一问,刘荣心下也随即了然。
——梁王刘武‘坏祖宗规矩’,不外乎太祖刘邦当年,定下的诸侯入朝长安,最多只能留一个月的规矩。
而梁王刘武自打封王就藩,虽然满共也就来了长安十来回,却是没有哪怕一次,是没有‘坏祖宗规矩’的。
先帝时还好些,留够一个月,再找东宫薄太后、椒房殿窦皇后哭一哭,也顶多多留个十天半个月;
到了当今天子启这一朝,那可就是彻底放浪形骸了——没个三五月,朝堂内外递给天子启,指责梁王刘武‘眷恋不去’的奏疏,就别想翻出什么浪!
尤其是吴楚之乱爆发前的一年,梁王刘武一来长安,那就是留了足足七八个月!
算上来回路途,都快留了一年了!
如此特权——如此明目张胆的特权,自然是东宫窦太后无底线的纵容,外加天子启的推波助澜,以及那段特殊的岁月,梁王刘武在汉家的特殊政治地位。
而此刻,窦广国毫无征兆的问起此番,梁王刘武还会不会像以往那般眷恋不去,在长安一留就是小半年,其目的,也是不言而喻……
“谁又说的准呢~”
“若是皇祖母还讲点道理,当是不会再容许梁王坏规矩的。”
“但皇祖母不讲道理,那也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“万一皇祖母要闹,父皇怕也只能由着梁王吧……”
语带愁苦的道出此语,刘荣便再度端起茶碗,做出一个‘我好气,但我也没办法’的憋闷之态。
见刘荣如此反应,窦广国只不着痕迹的垂下眸;
心下有了数,便也不再多问,转而和刘荣聊起窦婴、窦彭祖二人。
一番交谈下来,也算是宾主尽欢,双方各自达成了目的,也得到了充分的尊重。
只是刘荣离开之后,窦广国却是紧紧皱起了眉头,坐在客堂内,小半个时辰都没能回过神。
“太子……”
“陛下……”
“梁王………”
···
“唉~”
“阿姊,已是……”
“唉……”
···
“只求阿姊,万莫要一错再错吧……”
“若不然,待太子即了大位……”
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