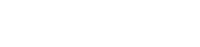第190章 族!
天子启新元三年,秋七月十四。
距离秋收,还有整一个月的时间。
虽然还没有秋收,但今年的粮食产量,也已经被丞相府撒去关中各地的农稼官,带回了预估数据。
——去年年末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,确实影响到了今年的春耕。
虽然叛乱三月而平,但那些随大军出征的兵卒、民夫,却都是在初夏才随大军班师;
家中壮劳力不在,无论是春耕日的播种,还是后续的灌溉、照料,自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但好在影响不算太大——今年的秋收,虽然不可能是大丰收,但也不至于欠收。
大抵能有个三石多点的平均亩产,属于即不高又不低的正常水准。
对于本就已经惨淡无比的粮价,这则消息,无疑又是一根压在骆驼背上的重草。
粮价,也终于随着这个消息的传出,而正式跌破三十钱,来到了二十八钱每石。
百姓们也从一开始,粮价大幅下降的喜悦,逐步转变为对粮价过低的担忧。
——粮食便宜,可不只是现在买的时候便宜!
秋收之后,大家伙要把手里的粮食卖出去的时候,必定会比现在更便宜!
便宜的过了头,农人的收入大幅缩水,虽然粮食还买得起,但其他的生活物资,恐怕就……
于是,粮价得以平抑带来的喜悦,便逐渐转变成了对粮价过低的担忧。
底层百姓忧心忡忡,朝野内外,也被梁王刘武突然失踪一事,给搞的人心惶惶。
有人说,是梁王刘武外出走动时太过高调,财帛动人心,让落草的‘好汉’给盯上了;
但这个猜想,很快就被否决。
开什么国际玩笑?
在这个世代——在天子启、窦太后这一朝,为了财物绑架梁王刘武?
这和扯旗造反有什么区别?
也有人说,或许真是天子启暗下动的手,把这个曾经觊觎神圣的弟弟,给人不知鬼不觉的噶掉了。
这个说法,也同样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认同。
——天子启是什么人?
二十多年的太子,甚至还做过监国太子,为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,连自己的老师都能下死手弄死不说,最后还一点骂名都没沾上的狠角色!
真想要杀梁王,还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?
真当谁都是梁王刘武啊?
···
再者说了:天子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这都已经是朝野内外心照不宣的事了。
这种微妙关头,天子启不想着一切求稳、不想着和母亲窦太后搞好关系,好让老太后确保政权交接的安稳进行,反而去通过对梁王刘武下死手,来刺激老太太?
这根本就说不通。
还是那句话:天子启,不是梁王刘武;
这样的蠢事儿,天子启干不出来。
排除了几个明显的错误答案之后,舆论才终于开始朝着正常人的方向发展起来。
——有人说到了点子上:梁王刘武,只怕是担心被天子启治罪,才逃走躲了起来。
至于躲去了哪里,却是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了。
而在这明显已经‘正常’起来的舆论中,却也不乏一种极其睿智,也对刘荣极其不利的说法。
说是梁王刘武‘畏罪潜逃’,身边必定没带多少随行护卫;
考虑到之前,闹得沸沸扬扬的皇太弟一事,梁王刘武‘落单’,对于太子刘荣而言,未必不是一个排除异己的良机……
这种说法的搞笑程度,其实和说天子启残害手足,是一个级别的——刘荣没这么蠢,也没这么低级。
和天子启一样:刘荣想搞死这位梁王叔,虽然没有天子启那至少九种办法,却也不至于沦落到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。
但这种明显有些搞笑的说法,却让一个极其要命的人,生出了半信半疑的动摇。
——东宫,窦太后。
连天子启都没有被排除嫌疑,更甚是直接让窦太后喊出一句‘帝杀吾子’,刘荣自然也逃不过这欲加之罪。
但让朝堂内外,都颇有些大跌眼镜的是:在被窦太后列为‘杀害梁王’的嫌疑人之后,刘荣却并没有选择低调做人,窝在太子宫闭门谢客。
在这一天——在天子启新元三年,秋七月十四,太子刘荣通过太子太师申屠嘉之口,向朝野内外下达通知:奉父皇诏谕,于秋七月十五日,举朔望朝议!
按理来说,每月初一、十五,即朔、望二日举朝议,是汉家由来已久的章程;
但天子不在长安的时候,朔望朝议,一般是会被替换成每五日举行一次的常朝的。
即:天子在长安时,每月初一、十五朔望朝,五日、十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五日,则举常朝;
天子不在长安,就由丞相负责主持每五日一次的常朝,直到天子回到长安。
过去这段时间,长安朝堂便一直是在丞相周亚夫不情不愿的主持下,每五日举行一次没有天子在场的常朝。
刘荣悉数与会,并承担起了书记员的工作,将朝议的所有内容整理成奏疏,并送去甘泉宫,给老爷子过目。
该批准的批准,该提意见的提意见,该拿主意的拿主意。
眼下,刘荣说要举朔望朝,又说是奉天子启诏谕,那天子启肯定还是不在场;
至于天子不在长安时,太子奉天子诏,举朔望朝……
“这,可是监国太子掌政之时,才会发生的事啊……”
嗅到这么一层的政治讯息,朝野内外不由得再度人心惶惶起来。
——太子,才刚得立不久啊!
就算平抑粮价一事,太子办的十分妥当,但距离太子监国,也还差了不止一点半点?
陛下这么急着要为太子铺路,甚至隐隐透露出太子监国的意图……
陛下,难道真的已经……
·
·
·
·
“父皇,是担心皇祖母借题发挥,才借这一出朔望朝议,来保孤几日。”
“几日之后,父皇也就该回到长安了……”
长安,蒿街中段北侧,太子宫正门之外。
太子刘荣一身戎装,站在自己的宝驹旁,一边打理着马鞍的皮带卡扣,嘴上一边如是说道。
听闻此言,一旁同样身着戎装,身后更是已经召集好太子卫队的中盾卫程不识,面上郁色不由得更深了几分。
“家上,真要在这要紧关头,如此高调的往尚冠里拿人?”
“让廷尉派人捉拿,也是一样的吧?”
忧心忡忡的说着,程不识不由再稍一颔首。
“眼下,梁王下落不明,太后都快要急疯了;”
“说是近几日,太后不是坐在榻上念叨‘梁王吾儿’,就是来回踱步间,嘀咕‘帝杀吾子’之类;”
“——便是家上,在此刻的太后眼中,只怕也是和梁王之事逃不开干系。”
“这种时候,难道不该是一动不如一静——一切,都以稳住太后为先,等陛下折返长安,再说其他吗?”
闻言,刘荣手上动作不由得一顿;
短暂的滞愣之后,刘荣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,忙完手里的事便回过身。
悠然一声长叹,方对程不识苦笑道:“若单论梁王叔的事,确实如此。”
“——如果只有梁王叔这件事,那孤眼下,确实应该自闭太子宫,静候父皇移驾回长安。”
“但除了梁王叔的事,父皇此番离京,还曾将平抑粮价一事托付于孤。”
“这件事,是肯定要杀一批人,以震慑宵小的。”
···
“原本我还有时间,慢慢搜集那些蠢货、蛀虫的罪证,再等秋收过后,顺理成章的拿人。”
“但眼下,父皇不日便要折返长安;”
“处置这些人的事,便不得不抓紧了……”
刘荣隐晦一提,程不识当即心下了然。
——在这个时代,治一个人死罪,重要的不是他犯了什么罪,而是这个人是什么身份。
如果是个奴隶,那别说是犯罪了——就算是看他不顺眼,你也完全可以弄死他,却根本不会有人说你什么;
甚至都不会有人,关注到你杀了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。
但若是个宗亲诸侯,那就算是他举兵谋逆,人们也会说:再怎么着,那也是老刘家的亲戚啊~
陛下,难道真要这么狠心?
对自家人都这么狠心,对俺们这些个农户黔首——对俺们这些外人,陛下还能好到哪儿去?
可别觉得这样的说法,有任何夸张的身份!
就说去年的吴楚七国之乱,主谋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二人;
也就是这俩人,或主动、或被动的自留体面了。
若不然——若是这二人活着被送到长安,那即便是对这二人恨之入骨的天子启,也几乎不可能光明正大的治这二人死罪。
要么,就在长安圈禁——甚至是软禁,而且还得好吃好喝,直到这二人老死;
顶天了去,也得是先‘使其闭门思过’,然后暗下里下死手,再对外敷衍一声:水土不服,暴毙而亡之类。
最大的可能性,是找个偏僻的院子给人关进去,象征性找几个人伺候起居,并确保日常生活供应;
再派专人看管关押,直到二人‘郁郁而终’。
说回眼下:刘荣因为平抑粮价一事,而揪出了十来家挖宗庙、社稷墙角的蛀虫,无论是出于个人情感,还是政治考量,都必须治这些人死罪。
而平抑粮价这件事,一开始是被天子启交给内史田叔和太子刘荣,之后又被刘荣大包大揽,抢到手里全权负责的。
所以,为了不让君父遭受‘这也太心狠了,这么点小事儿,就杀这么多与国同休的功侯’的指责,同时也是为了有始有终——把老爷子交代给自己的事处理干净,刘荣都得赶在老爷子回长安之前,把这些蛀虫搞定。若不然,老爷子人都到长安了,这些蛀虫却还在尚冠里住着,像个什么样子?
шwш? Λ n? c○
让天子启代劳吧?
——这件事是刘荣全权负责的,天子启插手此事,就等同于宣告刘荣差事办砸了,搞得天子启不得不亲自下场;
可若是不让天子启代劳?
——天子都回长安了,再让太子去拿主意、去拿捏功侯的身死,也终归是有些不合适。
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就是一句话:老爷子踏入长安的那一刻,凡是有关平抑粮价的所有事,都必须彻底宣告完成!
那些因此事而‘获罪于天’的蠢货,也必须在天子启踏入长安城之前,被各自埋进土里。
老爷子传回来的消息,是三天后,也就是秋七月十七日的清晨。
明日朔望朝,是刘荣太子生涯中,第一次以非书记员的身份——以决策者的角色,主持一场朔望朝;
后天,则要忙着准备迎接天子启圣驾的事宜。
换而言之:今天,是刘荣处理这件事的最后机会……
“走吧。”
“打起旌旗,走御道。”
“——到尚冠里之后,直接将这份名单上的功侯府邸围住!”
“孤,挨个上门拿人。”
丢下这么一句话,刘荣便也翻身上马,旋即将程不识递上前的青铜胄带在头上。
几乎是在盔胄戴上头的一瞬间,刘荣原本温润如玉的平和气质中,便陡然多出了一抹肃杀!
被那双大义凛然,又不时闪过森然寒意的双眸扫过,程不识也不由得下意识抬起手,对刘荣低头一拱手。
而后,便是整支太子卫队——共计五百北军禁卒,在太子刘荣、中盾卫程不识二人的带领下,浩浩荡荡的朝着尚冠里而去。
在沿经未央宫北宫门,以及位于蒿街、尚冠里交叉口的武库时,自然有禁卒惊惧交加的上前,询问刘荣‘意欲何为’。
当得知刘荣此行,是要前往尚冠里缉拿罪犯时,宫门、武库的护卫都是长松了一口气;
之后,便难免唏嘘感叹起来。
——这下,不知尚冠里,又要少几家‘与国同休’的功侯。
也不知这些人,究竟会沦落到怎样的下场。
自留体面,以保全家族?
罢官免爵,举族贬为庶人?
又或者,直接就是……
···
“殿、殿下此来……”
一行人才刚踏入尚冠里,当即便有几位‘德高望重’的老彻侯上前,挡在了刘荣所骑乘的战马前。
对于这几位虽然算不上德行崇高,却也勉强还算厚道的老者,刘荣的感官还算不错。
但眼下,显然不是和这些人嘘寒问暖,以彰显太子‘尊重长者’的时候。
“拿人。”
虽然一手持着马鞭拱起了手,但刘荣开口道出的话却是极其干脆。
那几位老功侯显然也没想到刘荣如此果决,面色当即便更难看了几分。
正要再开口,劝刘荣‘不要冲动行事’‘交由陛下圣断’之类,却被刘荣冷然抬手打断。
“公务在身,便不与几位老君侯寒暄了。”
“待拿了罪臣,再监斩行刑过后,孤在太子宫扫榻以待,恭候诸位大驾光临。”
言罢,刘荣便不顾几位老功侯还要再说,当即策动马匹,颇有些失礼的将几人逼退;
走出不多远,便在第一栋侯府外拉缰驻马。
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,满脸严肃的将其摊开;
而后,便当着尚冠里功侯贵戚的面,正对向那栋已经被重重包围的侯府,宣读起罪名。
“都昌侯:朱辟彊,五世侯,当今新元二年袭爵。”
“纵马于市,纵使仆从欺打民男至死。”
“——族!”
“即刻查抄都昌侯府,凡府内亲族,又仆从、雇工,尽数下狱!”
哗!!!
刘荣话音未落,尚冠里上下一片哗然!
不是,至于吗!!!
闹市纵马,这不就是交通违章嘛?!
纵容仆从殴打百姓至死,也不过就是赔个钱的事儿?
至于张口就是个骇人听闻的‘族’?!!
不等众人从惊骇中缓过神,刘荣已是策动马匹,看都不看鸡飞狗跳的都昌侯府一眼,便来到了几十步外的第二栋侯府外。
“阿陵侯:郭客,三世侯,当今新元三年袭爵。”
“酒后失德,与人言宫讳之事,语辱当朝皇后。”
“——族!”
“即可查抄侯府,凡府上之人,尽皆下狱!”
好嘛!
前面那个好歹还有点实打实的罪名,这个直接就是说了几句酒话,便也被定了个‘族’。
这……
“平侯:工师执,三世侯,太宗孝文皇帝后元元年袭爵。”
“策马践民粮稼。”
“——族!”
得——踩草坪的;
···
“隆虑侯:周通,二世侯,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二年袭爵。”
“荚钱欺民。”
“——族!”
漂亮——用假币的。
···
“堂阳侯:孙德,二世侯。”
“孝惠皇帝七年袭爵!”
念到这句‘孝惠皇帝七年袭爵’的时候,刘荣陡然加重了语气,还抬头狠狠瞪了那发须花白的老侯爵一眼。
——做了三十多年彻侯,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,瞎折腾什么?!
而后,又冷漠的低下头,继续念道:“私酿酒。”
“——族!”
这个最狠——未尽经营许可,私自酿造酒水的……
···
一路走下来,刘荣嘴里吐出来的罪名五花八门,愣是没一个罪名,能从《汉律》中找到依据;
但刘荣对这些人最初的最终判罚,却无一例外,都是个‘族’字。
事实如何,大家伙心里都明白:这是太子‘欲加之罪’,或者说是编造个罪名,好给这些人最后保留一点颜面。
但这动辄就是个‘族’字,留的那点体面,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……
“家上。”
“陛下不在长安,又太后忧心梁王安危,朝野内外人心惶惶。”
“值此人心思安之际,家上大兴牢狱,只怕是……”
见那十几家功侯,真的被刘荣带来的太子亲卫查抄,也真的被‘举族下狱’,尚冠里自不免为一阵兔死狐悲的悲怆所充斥。
但对于这声‘劝阻’,刘荣的态度,却是比那一日的窦太后还要坚决。
“父皇离京,移驾甘泉之时,曾有诏谕:使太子假天子节,许便宜行事。”
“诸位若是有话,大可在明日朔望朝——或直接等父皇移驾长安,再亲呈陛前。”
丢下这么一句冰冷无情的话,刘荣便带着押送‘罪臣’的队伍,朝着廷尉大牢的方向走去。
——十几家功侯,千八百号人,要想在今天,或者说是在天子启回长安之前杀完,肯定是不现实的。
而且杀人之前不和天子启知会一声、递个申请报告,也多少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在天子启回长安之前,刘荣至少要把这些人的罪给定了。
天子启新元三年,秋七月十四。
距离秋收,还有整一个月的时间。
虽然还没有秋收,但今年的粮食产量,也已经被丞相府撒去关中各地的农稼官,带回了预估数据。
——去年年末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,确实影响到了今年的春耕。
虽然叛乱三月而平,但那些随大军出征的兵卒、民夫,却都是在初夏才随大军班师;
家中壮劳力不在,无论是春耕日的播种,还是后续的灌溉、照料,自然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。
但好在影响不算太大——今年的秋收,虽然不可能是大丰收,但也不至于欠收。
大抵能有个三石多点的平均亩产,属于即不高又不低的正常水准。
对于本就已经惨淡无比的粮价,这则消息,无疑又是一根压在骆驼背上的重草。
粮价,也终于随着这个消息的传出,而正式跌破三十钱,来到了二十八钱每石。
百姓们也从一开始,粮价大幅下降的喜悦,逐步转变为对粮价过低的担忧。
——粮食便宜,可不只是现在买的时候便宜!
秋收之后,大家伙要把手里的粮食卖出去的时候,必定会比现在更便宜!
便宜的过了头,农人的收入大幅缩水,虽然粮食还买得起,但其他的生活物资,恐怕就……
于是,粮价得以平抑带来的喜悦,便逐渐转变成了对粮价过低的担忧。
底层百姓忧心忡忡,朝野内外,也被梁王刘武突然失踪一事,给搞的人心惶惶。
有人说,是梁王刘武外出走动时太过高调,财帛动人心,让落草的‘好汉’给盯上了;
但这个猜想,很快就被否决。
开什么国际玩笑?
在这个世代——在天子启、窦太后这一朝,为了财物绑架梁王刘武?
这和扯旗造反有什么区别?
也有人说,或许真是天子启暗下动的手,把这个曾经觊觎神圣的弟弟,给人不知鬼不觉的噶掉了。
这个说法,也同样没有得到太多人的认同。
——天子启是什么人?
二十多年的太子,甚至还做过监国太子,为了平定吴楚七国之乱,连自己的老师都能下死手弄死不说,最后还一点骂名都没沾上的狠角色!
真想要杀梁王,还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?
真当谁都是梁王刘武啊?
···
再者说了:天子启身体状况每况愈下,这都已经是朝野内外心照不宣的事了。
这种微妙关头,天子启不想着一切求稳、不想着和母亲窦太后搞好关系,好让老太后确保政权交接的安稳进行,反而去通过对梁王刘武下死手,来刺激老太太?
这根本就说不通。
还是那句话:天子启,不是梁王刘武;
这样的蠢事儿,天子启干不出来。
排除了几个明显的错误答案之后,舆论才终于开始朝着正常人的方向发展起来。
——有人说到了点子上:梁王刘武,只怕是担心被天子启治罪,才逃走躲了起来。
至于躲去了哪里,却是没人能说出个一二三四了。
而在这明显已经‘正常’起来的舆论中,却也不乏一种极其睿智,也对刘荣极其不利的说法。
说是梁王刘武‘畏罪潜逃’,身边必定没带多少随行护卫;
考虑到之前,闹得沸沸扬扬的皇太弟一事,梁王刘武‘落单’,对于太子刘荣而言,未必不是一个排除异己的良机……
这种说法的搞笑程度,其实和说天子启残害手足,是一个级别的——刘荣没这么蠢,也没这么低级。
和天子启一样:刘荣想搞死这位梁王叔,虽然没有天子启那至少九种办法,却也不至于沦落到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。
但这种明显有些搞笑的说法,却让一个极其要命的人,生出了半信半疑的动摇。
——东宫,窦太后。
连天子启都没有被排除嫌疑,更甚是直接让窦太后喊出一句‘帝杀吾子’,刘荣自然也逃不过这欲加之罪。
但让朝堂内外,都颇有些大跌眼镜的是:在被窦太后列为‘杀害梁王’的嫌疑人之后,刘荣却并没有选择低调做人,窝在太子宫闭门谢客。
在这一天——在天子启新元三年,秋七月十四,太子刘荣通过太子太师申屠嘉之口,向朝野内外下达通知:奉父皇诏谕,于秋七月十五日,举朔望朝议!
按理来说,每月初一、十五,即朔、望二日举朝议,是汉家由来已久的章程;
但天子不在长安的时候,朔望朝议,一般是会被替换成每五日举行一次的常朝的。
即:天子在长安时,每月初一、十五朔望朝,五日、十日、二十日、二十五日,则举常朝;
天子不在长安,就由丞相负责主持每五日一次的常朝,直到天子回到长安。
过去这段时间,长安朝堂便一直是在丞相周亚夫不情不愿的主持下,每五日举行一次没有天子在场的常朝。
刘荣悉数与会,并承担起了书记员的工作,将朝议的所有内容整理成奏疏,并送去甘泉宫,给老爷子过目。
该批准的批准,该提意见的提意见,该拿主意的拿主意。
眼下,刘荣说要举朔望朝,又说是奉天子启诏谕,那天子启肯定还是不在场;
至于天子不在长安时,太子奉天子诏,举朔望朝……
“这,可是监国太子掌政之时,才会发生的事啊……”
嗅到这么一层的政治讯息,朝野内外不由得再度人心惶惶起来。
——太子,才刚得立不久啊!
就算平抑粮价一事,太子办的十分妥当,但距离太子监国,也还差了不止一点半点?
陛下这么急着要为太子铺路,甚至隐隐透露出太子监国的意图……
陛下,难道真的已经……
·
·
·
·
“父皇,是担心皇祖母借题发挥,才借这一出朔望朝议,来保孤几日。”
“几日之后,父皇也就该回到长安了……”
长安,蒿街中段北侧,太子宫正门之外。
太子刘荣一身戎装,站在自己的宝驹旁,一边打理着马鞍的皮带卡扣,嘴上一边如是说道。
听闻此言,一旁同样身着戎装,身后更是已经召集好太子卫队的中盾卫程不识,面上郁色不由得更深了几分。
“家上,真要在这要紧关头,如此高调的往尚冠里拿人?”
“让廷尉派人捉拿,也是一样的吧?”
忧心忡忡的说着,程不识不由再稍一颔首。
“眼下,梁王下落不明,太后都快要急疯了;”
“说是近几日,太后不是坐在榻上念叨‘梁王吾儿’,就是来回踱步间,嘀咕‘帝杀吾子’之类;”
“——便是家上,在此刻的太后眼中,只怕也是和梁王之事逃不开干系。”
“这种时候,难道不该是一动不如一静——一切,都以稳住太后为先,等陛下折返长安,再说其他吗?”
闻言,刘荣手上动作不由得一顿;
短暂的滞愣之后,刘荣却是苦笑着摇了摇头,忙完手里的事便回过身。
悠然一声长叹,方对程不识苦笑道:“若单论梁王叔的事,确实如此。”
“——如果只有梁王叔这件事,那孤眼下,确实应该自闭太子宫,静候父皇移驾回长安。”
“但除了梁王叔的事,父皇此番离京,还曾将平抑粮价一事托付于孤。”
“这件事,是肯定要杀一批人,以震慑宵小的。”
···
“原本我还有时间,慢慢搜集那些蠢货、蛀虫的罪证,再等秋收过后,顺理成章的拿人。”
“但眼下,父皇不日便要折返长安;”
“处置这些人的事,便不得不抓紧了……”
刘荣隐晦一提,程不识当即心下了然。
——在这个时代,治一个人死罪,重要的不是他犯了什么罪,而是这个人是什么身份。
如果是个奴隶,那别说是犯罪了——就算是看他不顺眼,你也完全可以弄死他,却根本不会有人说你什么;
甚至都不会有人,关注到你杀了一个完全没有社会地位的奴隶。
但若是个宗亲诸侯,那就算是他举兵谋逆,人们也会说:再怎么着,那也是老刘家的亲戚啊~
陛下,难道真要这么狠心?
对自家人都这么狠心,对俺们这些个农户黔首——对俺们这些外人,陛下还能好到哪儿去?
可别觉得这样的说法,有任何夸张的身份!
就说去年的吴楚七国之乱,主谋吴王刘濞、楚王刘戊二人;
也就是这俩人,或主动、或被动的自留体面了。
若不然——若是这二人活着被送到长安,那即便是对这二人恨之入骨的天子启,也几乎不可能光明正大的治这二人死罪。
要么,就在长安圈禁——甚至是软禁,而且还得好吃好喝,直到这二人老死;
顶天了去,也得是先‘使其闭门思过’,然后暗下里下死手,再对外敷衍一声:水土不服,暴毙而亡之类。
最大的可能性,是找个偏僻的院子给人关进去,象征性找几个人伺候起居,并确保日常生活供应;
再派专人看管关押,直到二人‘郁郁而终’。
说回眼下:刘荣因为平抑粮价一事,而揪出了十来家挖宗庙、社稷墙角的蛀虫,无论是出于个人情感,还是政治考量,都必须治这些人死罪。
而平抑粮价这件事,一开始是被天子启交给内史田叔和太子刘荣,之后又被刘荣大包大揽,抢到手里全权负责的。
所以,为了不让君父遭受‘这也太心狠了,这么点小事儿,就杀这么多与国同休的功侯’的指责,同时也是为了有始有终——把老爷子交代给自己的事处理干净,刘荣都得赶在老爷子回长安之前,把这些蛀虫搞定。若不然,老爷子人都到长安了,这些蛀虫却还在尚冠里住着,像个什么样子?
шwш? Λ n? c○
让天子启代劳吧?
——这件事是刘荣全权负责的,天子启插手此事,就等同于宣告刘荣差事办砸了,搞得天子启不得不亲自下场;
可若是不让天子启代劳?
——天子都回长安了,再让太子去拿主意、去拿捏功侯的身死,也终归是有些不合适。
总而言之,言而总之,就是一句话:老爷子踏入长安的那一刻,凡是有关平抑粮价的所有事,都必须彻底宣告完成!
那些因此事而‘获罪于天’的蠢货,也必须在天子启踏入长安城之前,被各自埋进土里。
老爷子传回来的消息,是三天后,也就是秋七月十七日的清晨。
明日朔望朝,是刘荣太子生涯中,第一次以非书记员的身份——以决策者的角色,主持一场朔望朝;
后天,则要忙着准备迎接天子启圣驾的事宜。
换而言之:今天,是刘荣处理这件事的最后机会……
“走吧。”
“打起旌旗,走御道。”
“——到尚冠里之后,直接将这份名单上的功侯府邸围住!”
“孤,挨个上门拿人。”
丢下这么一句话,刘荣便也翻身上马,旋即将程不识递上前的青铜胄带在头上。
几乎是在盔胄戴上头的一瞬间,刘荣原本温润如玉的平和气质中,便陡然多出了一抹肃杀!
被那双大义凛然,又不时闪过森然寒意的双眸扫过,程不识也不由得下意识抬起手,对刘荣低头一拱手。
而后,便是整支太子卫队——共计五百北军禁卒,在太子刘荣、中盾卫程不识二人的带领下,浩浩荡荡的朝着尚冠里而去。
在沿经未央宫北宫门,以及位于蒿街、尚冠里交叉口的武库时,自然有禁卒惊惧交加的上前,询问刘荣‘意欲何为’。
当得知刘荣此行,是要前往尚冠里缉拿罪犯时,宫门、武库的护卫都是长松了一口气;
之后,便难免唏嘘感叹起来。
——这下,不知尚冠里,又要少几家‘与国同休’的功侯。
也不知这些人,究竟会沦落到怎样的下场。
自留体面,以保全家族?
罢官免爵,举族贬为庶人?
又或者,直接就是……
···
“殿、殿下此来……”
一行人才刚踏入尚冠里,当即便有几位‘德高望重’的老彻侯上前,挡在了刘荣所骑乘的战马前。
对于这几位虽然算不上德行崇高,却也勉强还算厚道的老者,刘荣的感官还算不错。
但眼下,显然不是和这些人嘘寒问暖,以彰显太子‘尊重长者’的时候。
“拿人。”
虽然一手持着马鞭拱起了手,但刘荣开口道出的话却是极其干脆。
那几位老功侯显然也没想到刘荣如此果决,面色当即便更难看了几分。
正要再开口,劝刘荣‘不要冲动行事’‘交由陛下圣断’之类,却被刘荣冷然抬手打断。
“公务在身,便不与几位老君侯寒暄了。”
“待拿了罪臣,再监斩行刑过后,孤在太子宫扫榻以待,恭候诸位大驾光临。”
言罢,刘荣便不顾几位老功侯还要再说,当即策动马匹,颇有些失礼的将几人逼退;
走出不多远,便在第一栋侯府外拉缰驻马。
从怀中掏出一卷竹简,满脸严肃的将其摊开;
而后,便当着尚冠里功侯贵戚的面,正对向那栋已经被重重包围的侯府,宣读起罪名。
“都昌侯:朱辟彊,五世侯,当今新元二年袭爵。”
“纵马于市,纵使仆从欺打民男至死。”
“——族!”
“即刻查抄都昌侯府,凡府内亲族,又仆从、雇工,尽数下狱!”
哗!!!
刘荣话音未落,尚冠里上下一片哗然!
不是,至于吗!!!
闹市纵马,这不就是交通违章嘛?!
纵容仆从殴打百姓至死,也不过就是赔个钱的事儿?
至于张口就是个骇人听闻的‘族’?!!
不等众人从惊骇中缓过神,刘荣已是策动马匹,看都不看鸡飞狗跳的都昌侯府一眼,便来到了几十步外的第二栋侯府外。
“阿陵侯:郭客,三世侯,当今新元三年袭爵。”
“酒后失德,与人言宫讳之事,语辱当朝皇后。”
“——族!”
“即可查抄侯府,凡府上之人,尽皆下狱!”
好嘛!
前面那个好歹还有点实打实的罪名,这个直接就是说了几句酒话,便也被定了个‘族’。
这……
“平侯:工师执,三世侯,太宗孝文皇帝后元元年袭爵。”
“策马践民粮稼。”
“——族!”
得——踩草坪的;
···
“隆虑侯:周通,二世侯,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二年袭爵。”
“荚钱欺民。”
“——族!”
漂亮——用假币的。
···
“堂阳侯:孙德,二世侯。”
“孝惠皇帝七年袭爵!”
念到这句‘孝惠皇帝七年袭爵’的时候,刘荣陡然加重了语气,还抬头狠狠瞪了那发须花白的老侯爵一眼。
——做了三十多年彻侯,都一大把年纪的人了,瞎折腾什么?!
而后,又冷漠的低下头,继续念道:“私酿酒。”
“——族!”
这个最狠——未尽经营许可,私自酿造酒水的……
···
一路走下来,刘荣嘴里吐出来的罪名五花八门,愣是没一个罪名,能从《汉律》中找到依据;
但刘荣对这些人最初的最终判罚,却无一例外,都是个‘族’字。
事实如何,大家伙心里都明白:这是太子‘欲加之罪’,或者说是编造个罪名,好给这些人最后保留一点颜面。
但这动辄就是个‘族’字,留的那点体面,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……
“家上。”
“陛下不在长安,又太后忧心梁王安危,朝野内外人心惶惶。”
“值此人心思安之际,家上大兴牢狱,只怕是……”
见那十几家功侯,真的被刘荣带来的太子亲卫查抄,也真的被‘举族下狱’,尚冠里自不免为一阵兔死狐悲的悲怆所充斥。
但对于这声‘劝阻’,刘荣的态度,却是比那一日的窦太后还要坚决。
“父皇离京,移驾甘泉之时,曾有诏谕:使太子假天子节,许便宜行事。”
“诸位若是有话,大可在明日朔望朝——或直接等父皇移驾长安,再亲呈陛前。”
丢下这么一句冰冷无情的话,刘荣便带着押送‘罪臣’的队伍,朝着廷尉大牢的方向走去。
——十几家功侯,千八百号人,要想在今天,或者说是在天子启回长安之前杀完,肯定是不现实的。
而且杀人之前不和天子启知会一声、递个申请报告,也多少有点说不过去。
但在天子启回长安之前,刘荣至少要把这些人的罪给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