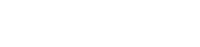袁盎死了!
如果单看这四个字,倒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——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长安朝堂之上,单就是比二千石以上级别,便有至少二十人离世。
人食五谷杂粮,便必有生老病死。
虽然令人哀婉、唏嘘,却也仅限于此了。
只不过袁盎的死,却并非自然死亡。
甚至是比起朝服腰斩的晁错,都还要更离奇一些……
“廷尉属衙外七十步?!”
长乐宫,长信殿。
端坐于御榻之上,目光涣散的撒向殿内,廷尉张欧那且惊且惧的模糊身影,窦太后才刚燃起的怒火,便好似被淋下了液氮般,当即僵在了脸上。
——耻辱!
——奇耻大辱!
要知道袁盎至死,都还是汉家的奉常卿!
虽然是战时临时任命,并不具备实际行政权,但吴楚之乱平定之后,罢免袁盎奉常一职的诏书,却也至今都还没有颁下!
太子刘荣没走完获立为储的政治程序,却也依然是板上钉钉的太子;
而袁盎这个奉常卿,虽然也是板上钉钉要离任,但一天没走完政治程序,就仍旧还是汉家的九卿。
即将离任、必将离任,但终归还没有正式离任。
这么说起来,问题就大条了。
——堂堂九卿,中二千石的秩禄;
掰着指头算,也绝对属于能排进汉家决策层前十五的重臣。
就这么死在了廷尉——死在汉家最高级别的司法部门外?
拿后世的时代来举例,这就好比某部尚书在大庭广众、朗朗乾坤之下,被刺杀死在了大理寺外。
“何人胆敢!……”
只刹那间,窦太后便勃然大怒!
正要出声厉喝,却被身旁的女儿刘嫖轻轻一拉衣袖。
半带盛怒,半带不接的侧过身,隐约看见刘嫖对自己轻轻一摇头;
再度正过头,却见身旁的老寺人噔噔噔小跑下御阶,似是从张欧手中接过了什么,便又噔噔噔折返而回。
“太后……”
仅仅只是‘太后’二字,窦太后便从老寺人——从自己几十年的忠仆字里行间,听出了惊惧!
下意识伸出手,几乎只是在摸到那枚符信轮廓的刹那,窦太后才刚被压下的怒火,便再也不受控制的彻底迸发。
“血口喷人!!!”
“——来人呐!”
“——将张欧这个乱臣贼子,即刻腰斩于东市!!!”
“为宗庙、社稷拼死奋战的梁王,也是你张欧一介外姓可以泼脏水的?!!!”
啪!!
含怒几声厉喝,窦太后仍不觉得丝毫解气,索性将手中玉符砸出。
玉符本就脆薄,被窦太后这么奋力砸出,纵是窦太后老迈,也还是被摔了个稀碎。
张欧却丝毫没有被窦太后口中,那‘泼脏水’三个字吓到;
只无奈的摇头叹息间,从怀中又掏出七八枚一模一样——和方才,被窦太后砸碎的那枚符毫无不同的玉符。
又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神情凄苦的昂起头。
“至昨日晚间,廷尉在长安缉拿下狱的关东刺客,共计八人。”
“——除去方才,被太后砸碎的那枚符信,臣这里,还另有七枚。”
“如果太后需要的话,臣还能找来更多。”
“臣入宫之前,廷尉又才抓了刺客三五人——无一例外,身上,也都带着这样的玉符……”
如是说着,张欧便就地跪坐下身,将手中玉符一枚枚摆在身前。
一边摆放着,嘴上一边不忘苦涩道:“臣知道,臣出自陛下的太子府,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;”
“仅仅只是凭借一个‘治刑名学’的由头,便被陛下任命为廷尉。”
“——至今为止,朝野内外都还有人说:张欧为廷尉,不过是陛下想要在朝中安插党羽,又实在无人可用,才在矮子里面拔高个,让张欧这个纨绔子弟捡了便宜,沐猴而冠。”
“还说臣——说张欧这个廷尉,将故廷尉张释之打下的局面,给搅合的乱七八糟……”
道出这最后一句话,张欧手中的最后一枚玉符,也应声落在了张欧身前。
只见张欧抬起头,五味杂陈的拱起手:“还请太后好生想想。”
“——像臣这样的幸臣,怎敢伪造如此拙劣的证据,去诬陷陛下一母同胞的手足兄弟、太后怀胎九月生下的梁王?”
“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,朝野内外,恐怕也就不会说臣这个廷尉,几乎让我汉家再也没有了被处死的人,更不再有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廷尉卿了……”
张欧话音落下,御榻上的窦太后,面色也随之一阵风云变幻起来。
作为汉家的第二位‘皇帝’,或者说是天子启口中的‘东帝’,窦太后虽然已近目不视物,但对于朝野内外的大小事务,却仍旧保持着相当全面的掌控。
朝野内外发生了什么事、出现了什么样的言论,窦太后不说了若指掌,也起码是有所耳闻。
至于张欧口中,朝堂内外冷嘲热讽,说张欧‘德不配位’,是被天子启强行提拔上了九卿,窦太后自也是有所了解。
——三年前,先帝驾崩,廷尉张释之诚惶诚恐的入宫请罪,请求曾被自己狂刷声望的储君太子、先帝驾崩后的新君:天子启,能大人不记小人过,原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之后,天子启虽然原谅了张释之,却也还是记仇的将张释之‘外放’——从廷尉卿的位置,挪到了淮南国相的职务上。
从中二千石的九卿,到同为中二千石的诸侯王相,虽然是同级调动,却是从京官外放关东;
多少也带着些公报私仇,亦或是‘眼不见为净’的意味在其中。
而在张释之外放为淮南国相后,便是由天子启的潜邸心腹:太子舍人安丘侯张欧,成为了天子启一朝的首任廷尉卿。
任命张欧为廷尉时,天子启对朝野内外给出的交代是:张欧治刑名学,又乃功臣之后,可堪一用。
治不治刑名学,没人能说清楚;
至于是否可堪一用,张欧过去这几年的表现,却是给全天下人,交出了一个近乎趋近于零分的糟糕答卷。
作为廷尉卿,张欧手中最重要的职责,便是批准地方郡县递交上来的死刑执行申请。
只有廷尉卿用印批准,这一例死刑(腰斩、坐死、枭首等),才可以从审批阶段进入执行阶段。
原本不是这样的。
汉家的死刑执行权,原本并非完全由中央掌控,而是给予了地方郡县相当大的自主权;
至于朝堂中央的廷尉,地方郡县则只需要在事后,补交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报告,以供复核即可。
而如今,汉家的死刑执行权,之所以被收归朝堂中央的廷尉所有,则是从先帝年间的著名典故:缇萦救父开始的。
缇萦救父的典故,在后世几可谓妇孺皆知,自不必再多赘述。
在这件事发生之后,先帝便以‘汉律尚有严苛之处’为由,废除了汉家相当一部分肉刑。
也恰恰是这件事,给了先帝从律法着手,以执法权为切入点,将地方行政权——主要是死刑执行权收归中央的机会。
与之一同出现的,便是那句让世人耳熟能详的‘将相不辱’,即:二千石及以上级别官员,地方郡县不再具备审理权,而是应当由长安中央的廷尉直接审理。
言归正传。
作为廷尉卿——尤其是先帝专门进行过强化,甚至是作为汉家中央集权之开端的廷尉属衙主官,张欧本该在履任之后大展身手,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但在过去这三年,或者说是整个廷尉生涯,张欧这个廷尉卿亲自批准的死刑执行申请,却是五个指头都数得过来。
——这很离谱!
要知道如今汉家,便是抛去关东各宗亲诸侯,单只是长安中央直辖的郡县——甚至单只是关中,便有起码上千万人口!
便说一个几万口人的县,一年也总会有那么三五个烂人,因为犯下种种人神共愤的罪行,而被依律判处死刑。
更何况过去这三年,绝对属与汉家自太祖皇帝立国以来,少有的‘多事之秋’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死在张欧那方廷尉印章下的死囚,就算没有三五万,也总该有个万儿八千人才是。
结果张欧可倒好:一看到死罪审批的文档,便动辄头痛脑热,接连告病休假;实在是装病都装不下去了,也都是尽可能寻各种由头,将锅甩给副手:那什么,我忙,你把这个案子批了。
到了推无可推、避无可避的地步,张欧也都是哭丧着脸,磨磨唧唧老半天,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用印批准。
甚至即便是批准了,也不忘沐浴更衣,焚香祷告,并告诉左右:绝非是我冷血嗜杀,实在是形势所迫……
对此,五星评论家太子刘荣说:张欧做廷尉,就好比和尚转行做了刽子手——别人砍头前往刀上喷酒,他可倒好,砍头前要先诵几句佛经……
更要命的是:张欧的不作为,非但让许多原本早就该被执行的死囚苟活于牢狱之中,甚至还等来了自先帝驾崩至今,天子启先后两次颁下的赦令!
——第一次,是薄太皇太后驾崩,天子启依照惯例举国丧,并大赦天下;
第二次,则是吴楚乱平,天子启碍于那句‘深入多杀为要’惹得天下人心惶惶,才姗姗来迟的大赦天下,以安定人心。
这,就有些让人接受不能了。
一个无恶不作的渣滓,为祸地方多年,好不容易被一个公正的县令捉拿下狱,并依律判了死罪;
结果送去廷尉审批的卷宗,等来的却不是‘可以执行’的审批通过回执,而是天子启大赦天下的诏令……
好,算你小子走运,放你出来;
结果没两天的功夫,又是犯下杀人放火之类的大罪,再次被捉拿下狱,判了死罪。
当地百姓群情激愤,恨不能啖其肉、寝其皮!
县令也很给力——这边刚抓了人,那边便给长安廷尉发去了死刑执行申请。
结果又等了大半年,再度等来了天子启大赦天下……
如今,关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很危险的说法了!
——说是只要张欧做廷尉,那除了谋反之外,便没有第二种罪行,会真的让罪犯被处死;
左右不过‘判’了死刑,然后在张廷尉的宅心仁厚下吃几年牢饭。
长则一两年,短则三五月,总能等来下一次大赦……
“朝野内外对廷尉的指责,究竟有几分真假,廷尉自己心里清楚。”
“——我这双眼睛再瞎,也不至于看不清一个廷尉,究竟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。”
“若不是看在廷尉已故的父亲:安丘懿侯的份上,我也不会对朝野内外的劾章视若无睹,仍留用君侯于廷尉任上。”
“只是此番,君侯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,却是实实在在的把我,果真当成一个瞎了眼的乡野愚妇了……”
明明已经自嘲过,却还是被窦太后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责‘别装可怜,你就是个很不称职的廷尉’,张欧自是不敢多辩解。
正要说点什么——好歹为自己没有污蔑梁王刘武解释几句,便见御榻之上,窦太后原本满含盛怒的面庞,此刻却是布满了阴森冷然。
“君侯,还是回到自己的府邸,静侯皇帝的罢免诏书吧。”
“——太宗皇帝有制:将相不辱,许公卿二千石自留体面,不得刀剑加身。”
“按照惯例,应该是由廷尉卿登门,为君侯斟上御赐鸩酒的。”
“既然君侯自己就是廷尉,那倒也省却了不少麻烦?”
窦太后清冷之语,这便算是在眨眼之间,宣判了一位当朝九卿的死刑。
按照惯例,被太后如此不留情面的说上一句‘回家等着被罢免吧’,以如今汉家的风气,张欧甚至都不用廷尉带鸩酒上门,便会自己给自己留体面。
但这件事,显然没有这么简单。
——至少张欧这条性命,还没这么容易就被盛怒之下,不惜将梁王刘武的疯狂举动归咎为‘有人诬陷’的窦太后取走。
不知是早就到了殿外,只是没有进来;
亦或是真的有那么巧。
几乎是张欧这边,刚面色灰败的叩首领命,表示自己这就回去,给自己保留体面,天子启和刘荣的身影,便也随即出现在了殿门之外。
没有唱喏,也没有通传。
汉家的天子和储君,就这么大咧咧走进了东宫太后的居所,齐声对御榻上的母亲/祖母拱手一礼。
“儿臣,参见母后。”
“——孙儿,参见皇祖母。”
“——惟愿太后千秋万福,长乐未央……”
对窦太后,父子二人的态度虽不尽相同,但面上神情,却好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都是微皱着眉头,勉强维持的淡定,却一眼就能看出郁闷之色。
窦太后显然看不清这些细节;
听到皇帝儿子,以及长孙刘荣的声音,本就不甚愉快的神情,只霎时间便更多出一抹讥讽。
“喏?”
“——戏台刚搭出个架子,角儿这便来亮相了。”
“皇帝这戏瘾,可真是越来越大了……”
阴阳怪气的一语道出口,窦太后只双手抓着鸠杖顶部,将脑袋往异侧一别,以颧骨撑在手背上。
只嘴上,仍是极尽讥讽道:“今儿个,皇帝是要唱哪一出啊?”
“——冒顿单于鸣镝弑父?”
“还是乌孙王子残害手足?”
相较于后世,京、川、昆、豫等地方戏曲相对发达的时代,如今汉家,其实是没有成体系的戏曲类目的。
唯一可被称作‘戏’的,是禁中宫讳于年节时,半祭祀、半娱乐性质的蚩尤戏。
最早的蚩尤戏,大约出现在周中期,以蚩尤为丑角,讲黄帝斩杀蚩尤的故事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根据地域文化差异,而发展出了不同的内容——以敌对国的某位暴君,又或是某个残暴的将领、奸诈的文臣为丑角,讲本国击败对方的故事。
到如今汉室,尤其是先帝一朝天下大治,百姓民安居乐业之后,蚩尤戏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。
有以疫病、灾害为丑角的祭祀专供曲目;
有以妖魔、恶人为丑角的单纯娱乐项目。
自然,也有了以草原游牧民族为丑角,披着‘娱乐’的皮,隐晦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曲目。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便是冒顿单于鸣镝弑父、老上单于迎娶亲母,以及乌孙王子残害手足这样的人伦大戏。
而此刻,窦太后以这几个曲目,来暗讽天子启‘戏瘾越来越大’,其言外之意,自也不言而喻。
“皇祖母……”
见老爹应声黑了脸,刘荣自是按照过往的惯例,或者说是愈发熟练的本能,想要站出来为老爷子蹚遍雷。
——有没有效果另说,起码态度得摆出来。
只不过一声‘皇祖母’都还没完全道出口,便见老爷子猛然一抬手!
旋即便昂起头,面上不见丝毫恭顺之色,只阴沉着脸,将双手缓慢背负于身后。
仰望向御榻之上,执拗的将头别过去的窦太后,天子启阴郁的面庞之上,终是缓缓涌现出一抹无奈。
“母亲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呢?”
一声‘母亲’,当即惹得一旁的张欧、刘荣两人赶忙低下头去,全当自己什么都没听见。
天子启却毫不在乎,只定定的望向上首——望向母亲窦太后那手握鸠杖,别过头不愿,或者说是不敢直视自己的执拗侧脸。
“母亲,还要顽固到什么时候?”
“还要护……”
···
“嘶~~~……”
“呼~~~~~……”
···
“——母亲,还要纵容阿武到什么时候?!!”
如果单看这四个字,倒也没什么大不了。
——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长安朝堂之上,单就是比二千石以上级别,便有至少二十人离世。
人食五谷杂粮,便必有生老病死。
虽然令人哀婉、唏嘘,却也仅限于此了。
只不过袁盎的死,却并非自然死亡。
甚至是比起朝服腰斩的晁错,都还要更离奇一些……
“廷尉属衙外七十步?!”
长乐宫,长信殿。
端坐于御榻之上,目光涣散的撒向殿内,廷尉张欧那且惊且惧的模糊身影,窦太后才刚燃起的怒火,便好似被淋下了液氮般,当即僵在了脸上。
——耻辱!
——奇耻大辱!
要知道袁盎至死,都还是汉家的奉常卿!
虽然是战时临时任命,并不具备实际行政权,但吴楚之乱平定之后,罢免袁盎奉常一职的诏书,却也至今都还没有颁下!
太子刘荣没走完获立为储的政治程序,却也依然是板上钉钉的太子;
而袁盎这个奉常卿,虽然也是板上钉钉要离任,但一天没走完政治程序,就仍旧还是汉家的九卿。
即将离任、必将离任,但终归还没有正式离任。
这么说起来,问题就大条了。
——堂堂九卿,中二千石的秩禄;
掰着指头算,也绝对属于能排进汉家决策层前十五的重臣。
就这么死在了廷尉——死在汉家最高级别的司法部门外?
拿后世的时代来举例,这就好比某部尚书在大庭广众、朗朗乾坤之下,被刺杀死在了大理寺外。
“何人胆敢!……”
只刹那间,窦太后便勃然大怒!
正要出声厉喝,却被身旁的女儿刘嫖轻轻一拉衣袖。
半带盛怒,半带不接的侧过身,隐约看见刘嫖对自己轻轻一摇头;
再度正过头,却见身旁的老寺人噔噔噔小跑下御阶,似是从张欧手中接过了什么,便又噔噔噔折返而回。
“太后……”
仅仅只是‘太后’二字,窦太后便从老寺人——从自己几十年的忠仆字里行间,听出了惊惧!
下意识伸出手,几乎只是在摸到那枚符信轮廓的刹那,窦太后才刚被压下的怒火,便再也不受控制的彻底迸发。
“血口喷人!!!”
“——来人呐!”
“——将张欧这个乱臣贼子,即刻腰斩于东市!!!”
“为宗庙、社稷拼死奋战的梁王,也是你张欧一介外姓可以泼脏水的?!!!”
啪!!
含怒几声厉喝,窦太后仍不觉得丝毫解气,索性将手中玉符砸出。
玉符本就脆薄,被窦太后这么奋力砸出,纵是窦太后老迈,也还是被摔了个稀碎。
张欧却丝毫没有被窦太后口中,那‘泼脏水’三个字吓到;
只无奈的摇头叹息间,从怀中又掏出七八枚一模一样——和方才,被窦太后砸碎的那枚符毫无不同的玉符。
又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神情凄苦的昂起头。
“至昨日晚间,廷尉在长安缉拿下狱的关东刺客,共计八人。”
“——除去方才,被太后砸碎的那枚符信,臣这里,还另有七枚。”
“如果太后需要的话,臣还能找来更多。”
“臣入宫之前,廷尉又才抓了刺客三五人——无一例外,身上,也都带着这样的玉符……”
如是说着,张欧便就地跪坐下身,将手中玉符一枚枚摆在身前。
一边摆放着,嘴上一边不忘苦涩道:“臣知道,臣出自陛下的太子府,没有什么突出的才能;”
“仅仅只是凭借一个‘治刑名学’的由头,便被陛下任命为廷尉。”
“——至今为止,朝野内外都还有人说:张欧为廷尉,不过是陛下想要在朝中安插党羽,又实在无人可用,才在矮子里面拔高个,让张欧这个纨绔子弟捡了便宜,沐猴而冠。”
“还说臣——说张欧这个廷尉,将故廷尉张释之打下的局面,给搅合的乱七八糟……”
道出这最后一句话,张欧手中的最后一枚玉符,也应声落在了张欧身前。
只见张欧抬起头,五味杂陈的拱起手:“还请太后好生想想。”
“——像臣这样的幸臣,怎敢伪造如此拙劣的证据,去诬陷陛下一母同胞的手足兄弟、太后怀胎九月生下的梁王?”
“如果真有这样的胆量,朝野内外,恐怕也就不会说臣这个廷尉,几乎让我汉家再也没有了被处死的人,更不再有一个有责任、有担当的廷尉卿了……”
张欧话音落下,御榻上的窦太后,面色也随之一阵风云变幻起来。
作为汉家的第二位‘皇帝’,或者说是天子启口中的‘东帝’,窦太后虽然已近目不视物,但对于朝野内外的大小事务,却仍旧保持着相当全面的掌控。
朝野内外发生了什么事、出现了什么样的言论,窦太后不说了若指掌,也起码是有所耳闻。
至于张欧口中,朝堂内外冷嘲热讽,说张欧‘德不配位’,是被天子启强行提拔上了九卿,窦太后自也是有所了解。
——三年前,先帝驾崩,廷尉张释之诚惶诚恐的入宫请罪,请求曾被自己狂刷声望的储君太子、先帝驾崩后的新君:天子启,能大人不记小人过,原谅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。
之后,天子启虽然原谅了张释之,却也还是记仇的将张释之‘外放’——从廷尉卿的位置,挪到了淮南国相的职务上。
从中二千石的九卿,到同为中二千石的诸侯王相,虽然是同级调动,却是从京官外放关东;
多少也带着些公报私仇,亦或是‘眼不见为净’的意味在其中。
而在张释之外放为淮南国相后,便是由天子启的潜邸心腹:太子舍人安丘侯张欧,成为了天子启一朝的首任廷尉卿。
任命张欧为廷尉时,天子启对朝野内外给出的交代是:张欧治刑名学,又乃功臣之后,可堪一用。
治不治刑名学,没人能说清楚;
至于是否可堪一用,张欧过去这几年的表现,却是给全天下人,交出了一个近乎趋近于零分的糟糕答卷。
作为廷尉卿,张欧手中最重要的职责,便是批准地方郡县递交上来的死刑执行申请。
只有廷尉卿用印批准,这一例死刑(腰斩、坐死、枭首等),才可以从审批阶段进入执行阶段。
原本不是这样的。
汉家的死刑执行权,原本并非完全由中央掌控,而是给予了地方郡县相当大的自主权;
至于朝堂中央的廷尉,地方郡县则只需要在事后,补交案件审理的过程和报告,以供复核即可。
而如今,汉家的死刑执行权,之所以被收归朝堂中央的廷尉所有,则是从先帝年间的著名典故:缇萦救父开始的。
缇萦救父的典故,在后世几可谓妇孺皆知,自不必再多赘述。
在这件事发生之后,先帝便以‘汉律尚有严苛之处’为由,废除了汉家相当一部分肉刑。
也恰恰是这件事,给了先帝从律法着手,以执法权为切入点,将地方行政权——主要是死刑执行权收归中央的机会。
与之一同出现的,便是那句让世人耳熟能详的‘将相不辱’,即:二千石及以上级别官员,地方郡县不再具备审理权,而是应当由长安中央的廷尉直接审理。
言归正传。
作为廷尉卿——尤其是先帝专门进行过强化,甚至是作为汉家中央集权之开端的廷尉属衙主官,张欧本该在履任之后大展身手,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
但在过去这三年,或者说是整个廷尉生涯,张欧这个廷尉卿亲自批准的死刑执行申请,却是五个指头都数得过来。
——这很离谱!
要知道如今汉家,便是抛去关东各宗亲诸侯,单只是长安中央直辖的郡县——甚至单只是关中,便有起码上千万人口!
便说一个几万口人的县,一年也总会有那么三五个烂人,因为犯下种种人神共愤的罪行,而被依律判处死刑。
更何况过去这三年,绝对属与汉家自太祖皇帝立国以来,少有的‘多事之秋’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死在张欧那方廷尉印章下的死囚,就算没有三五万,也总该有个万儿八千人才是。
结果张欧可倒好:一看到死罪审批的文档,便动辄头痛脑热,接连告病休假;实在是装病都装不下去了,也都是尽可能寻各种由头,将锅甩给副手:那什么,我忙,你把这个案子批了。
到了推无可推、避无可避的地步,张欧也都是哭丧着脸,磨磨唧唧老半天,才心不甘情不愿的用印批准。
甚至即便是批准了,也不忘沐浴更衣,焚香祷告,并告诉左右:绝非是我冷血嗜杀,实在是形势所迫……
对此,五星评论家太子刘荣说:张欧做廷尉,就好比和尚转行做了刽子手——别人砍头前往刀上喷酒,他可倒好,砍头前要先诵几句佛经……
更要命的是:张欧的不作为,非但让许多原本早就该被执行的死囚苟活于牢狱之中,甚至还等来了自先帝驾崩至今,天子启先后两次颁下的赦令!
——第一次,是薄太皇太后驾崩,天子启依照惯例举国丧,并大赦天下;
第二次,则是吴楚乱平,天子启碍于那句‘深入多杀为要’惹得天下人心惶惶,才姗姗来迟的大赦天下,以安定人心。
这,就有些让人接受不能了。
一个无恶不作的渣滓,为祸地方多年,好不容易被一个公正的县令捉拿下狱,并依律判了死罪;
结果送去廷尉审批的卷宗,等来的却不是‘可以执行’的审批通过回执,而是天子启大赦天下的诏令……
好,算你小子走运,放你出来;
结果没两天的功夫,又是犯下杀人放火之类的大罪,再次被捉拿下狱,判了死罪。
当地百姓群情激愤,恨不能啖其肉、寝其皮!
县令也很给力——这边刚抓了人,那边便给长安廷尉发去了死刑执行申请。
结果又等了大半年,再度等来了天子启大赦天下……
如今,关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个很危险的说法了!
——说是只要张欧做廷尉,那除了谋反之外,便没有第二种罪行,会真的让罪犯被处死;
左右不过‘判’了死刑,然后在张廷尉的宅心仁厚下吃几年牢饭。
长则一两年,短则三五月,总能等来下一次大赦……
“朝野内外对廷尉的指责,究竟有几分真假,廷尉自己心里清楚。”
“——我这双眼睛再瞎,也不至于看不清一个廷尉,究竟有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。”
“若不是看在廷尉已故的父亲:安丘懿侯的份上,我也不会对朝野内外的劾章视若无睹,仍留用君侯于廷尉任上。”
“只是此番,君侯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来,却是实实在在的把我,果真当成一个瞎了眼的乡野愚妇了……”
明明已经自嘲过,却还是被窦太后如此不留情面的指责‘别装可怜,你就是个很不称职的廷尉’,张欧自是不敢多辩解。
正要说点什么——好歹为自己没有污蔑梁王刘武解释几句,便见御榻之上,窦太后原本满含盛怒的面庞,此刻却是布满了阴森冷然。
“君侯,还是回到自己的府邸,静侯皇帝的罢免诏书吧。”
“——太宗皇帝有制:将相不辱,许公卿二千石自留体面,不得刀剑加身。”
“按照惯例,应该是由廷尉卿登门,为君侯斟上御赐鸩酒的。”
“既然君侯自己就是廷尉,那倒也省却了不少麻烦?”
窦太后清冷之语,这便算是在眨眼之间,宣判了一位当朝九卿的死刑。
按照惯例,被太后如此不留情面的说上一句‘回家等着被罢免吧’,以如今汉家的风气,张欧甚至都不用廷尉带鸩酒上门,便会自己给自己留体面。
但这件事,显然没有这么简单。
——至少张欧这条性命,还没这么容易就被盛怒之下,不惜将梁王刘武的疯狂举动归咎为‘有人诬陷’的窦太后取走。
不知是早就到了殿外,只是没有进来;
亦或是真的有那么巧。
几乎是张欧这边,刚面色灰败的叩首领命,表示自己这就回去,给自己保留体面,天子启和刘荣的身影,便也随即出现在了殿门之外。
没有唱喏,也没有通传。
汉家的天子和储君,就这么大咧咧走进了东宫太后的居所,齐声对御榻上的母亲/祖母拱手一礼。
“儿臣,参见母后。”
“——孙儿,参见皇祖母。”
“——惟愿太后千秋万福,长乐未央……”
对窦太后,父子二人的态度虽不尽相同,但面上神情,却好似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
都是微皱着眉头,勉强维持的淡定,却一眼就能看出郁闷之色。
窦太后显然看不清这些细节;
听到皇帝儿子,以及长孙刘荣的声音,本就不甚愉快的神情,只霎时间便更多出一抹讥讽。
“喏?”
“——戏台刚搭出个架子,角儿这便来亮相了。”
“皇帝这戏瘾,可真是越来越大了……”
阴阳怪气的一语道出口,窦太后只双手抓着鸠杖顶部,将脑袋往异侧一别,以颧骨撑在手背上。
只嘴上,仍是极尽讥讽道:“今儿个,皇帝是要唱哪一出啊?”
“——冒顿单于鸣镝弑父?”
“还是乌孙王子残害手足?”
相较于后世,京、川、昆、豫等地方戏曲相对发达的时代,如今汉家,其实是没有成体系的戏曲类目的。
唯一可被称作‘戏’的,是禁中宫讳于年节时,半祭祀、半娱乐性质的蚩尤戏。
最早的蚩尤戏,大约出现在周中期,以蚩尤为丑角,讲黄帝斩杀蚩尤的故事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也根据地域文化差异,而发展出了不同的内容——以敌对国的某位暴君,又或是某个残暴的将领、奸诈的文臣为丑角,讲本国击败对方的故事。
到如今汉室,尤其是先帝一朝天下大治,百姓民安居乐业之后,蚩尤戏更是得到了长足发展。
有以疫病、灾害为丑角的祭祀专供曲目;
有以妖魔、恶人为丑角的单纯娱乐项目。
自然,也有了以草原游牧民族为丑角,披着‘娱乐’的皮,隐晦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曲目。
其中最具代表性的,便是冒顿单于鸣镝弑父、老上单于迎娶亲母,以及乌孙王子残害手足这样的人伦大戏。
而此刻,窦太后以这几个曲目,来暗讽天子启‘戏瘾越来越大’,其言外之意,自也不言而喻。
“皇祖母……”
见老爹应声黑了脸,刘荣自是按照过往的惯例,或者说是愈发熟练的本能,想要站出来为老爷子蹚遍雷。
——有没有效果另说,起码态度得摆出来。
只不过一声‘皇祖母’都还没完全道出口,便见老爷子猛然一抬手!
旋即便昂起头,面上不见丝毫恭顺之色,只阴沉着脸,将双手缓慢背负于身后。
仰望向御榻之上,执拗的将头别过去的窦太后,天子启阴郁的面庞之上,终是缓缓涌现出一抹无奈。
“母亲,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变成如今这般模样的呢?”
一声‘母亲’,当即惹得一旁的张欧、刘荣两人赶忙低下头去,全当自己什么都没听见。
天子启却毫不在乎,只定定的望向上首——望向母亲窦太后那手握鸠杖,别过头不愿,或者说是不敢直视自己的执拗侧脸。
“母亲,还要顽固到什么时候?”
“还要护……”
···
“嘶~~~……”
“呼~~~~~……”
···
“——母亲,还要纵容阿武到什么时候?!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