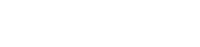刘濞麾下的吴楚叛军自彭城西出,连战连捷,带着高昂的士气兵临睢阳。
长安朝堂派出的太尉周亚夫、大将军窦婴,以及车骑将军郦寄这三路平叛大军,也正式从蓝田大营开拔。
——窦婴所部东进,欲出函谷;
周亚夫、郦寄所部,则都自蓝田南下,绕道武关。
而在睢阳战役爆发之前,长安朝堂中央,与吴楚叛军之间的舆论战,也正式打响。
只是和军事上连战连捷,近乎平推到睢阳城下的出奇顺利截然相反的是:在舆论战上,吴王刘濞,就差没把底裤也给输进去……
·
·
·
“申屠嘉……”
睢阳东五十里,吴楚叛军大营,中军大帐。
看着手中,由长安朝堂颁行于天下,列数自己无数罪证的檄文,吴王刘濞原本还算愉快的心情,只瞬间蒙上了一层雾霾。
——倒也不是这封檄文上,写了什么出乎刘濞预料的内容。
左右不过抗旨不遵,举兵谋逆,居心叵测之类,都是刘濞早有心理准备的那套说辞。
真正让刘濞感到牙疼的是:这封讨贼檄文,属的是当朝丞相——申屠嘉的名。
这就让刘濞有些脸颊发烫了……
“寡人的檄文,前脚才刚指责长安‘帝相不和’,长安天子远贤臣、亲小人;”
“结果寡人口中的‘贤臣’,后脚就在征讨寡人的檄文上署名……”
“——署的还是‘汉相故安侯申屠嘉’的名?!”
半带自嘲,半带恼怒的一声反问,只惹得帐内为之一静,吴楚众将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愣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,这场吴楚之乱,是在明年春正月,洛阳宫被雷劈着火,连带着城墙也被烧了好几天,才让吴王刘濞自认‘得了天命’,从而下定决心举兵的。
而在这个时间线,吴王刘濞之所以会提前举兵,除了长安朝堂太过于咄咄逼人,开口就是削夺吴国的会稽、豫章两郡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,便是那则长安朝堂‘帝相不和’的传闻。
也正是基于此,吴王刘濞才以‘长安天子昏聩无道,薄待贤臣申屠嘉,亲近小人晁错’为名,打起了诛晁错、清君侧的旗号。
结果现在回过味来,什么‘帝相不和’之类,怕都是长安天子设的局,不过是引刘濞入套而已;
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,军队都已经开到睢阳城下了,被长安摆这么一道,吴王刘濞,多少有些尴尬。
——但也就仅限于尴尬了。
从帐内众将的面上神情也不难看出:除了吴王刘濞,并没有其他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。
“左右不过长安天子呈口舌之快,操弄权术的小把戏罢了,大王不必耿耿于怀!”
“他长安天子再怎么操弄权术,也总不至于凭这一纸檄文,就能将淮阳郡再给夺回去?”
“啊?”
老将满是肆意的一番话,只惹得帐内一阵哄笑不止。
便是吴王刘濞,也只是再低头看了看那檄文,便随手将其丢到了一旁。
面上,也逐渐涌上近些时日,时常挂在脸上的自信笑容。
——后世有一句话:战争,是政治的延伸。
而战争的胜利,往往能掩盖许多矛盾。
此时大帐内的情况,便大抵如是。
自彭城西出,兵指睢阳这数百里路,吴楚叛军主力连战连捷,甚至一日连下数城!
到如今,年关将至,举兵才刚一个多月,便已是尽下整个淮阳郡,外加梁国在都城睢阳以东的大部分城池。
再加上这些城池所贡献的兵力,此时的吴楚主力,除去最开始的三十万吴国军队、十万楚国兵马,又多了足足十数万的混编别部!
五十多万大军!
近乎与楚汉争霸之时,太祖高皇帝为攻打项羽的楚都,而征集的诸侯联军兵力平齐!
有如此大军,又有过往月余的连战连捷,吴王刘濞纵是对长安朝堂的‘小心机’感到恼怒,却也并没有太当回事。
还是那句话;
——天大地大,赢家最大!
若此战得胜,占据睢阳,从而将整个梁国也纳入控制范围之内,刘濞将来最差的结果,也至少是和长安划江而治!
届时,别说什么诛晁错、清君侧了——便是顺天应命,讨伐暴君之类的旗号,刘濞也没什么不敢打出来的。
若不能胜,则极有可能会功败垂成,兵败身亡。
无论胜败,刘濞和长安朝堂之间的舆论战,都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。
赢了,自有大儒为刘濞辩经;
输了,也有的是志向远大之辈,想要拿刘濞的人头去长安邀功。
反正都到了这一步,与其再去纠结舆论,倒不如赶紧把睢阳攻下来得实在。
——左右拿长安朝堂的舆论攻势没办法,刘濞便如是安慰着自己。
只是有一个问题,被刘濞或有意,或无意的忽视了。
舆论,确实无法成为决定性因素。
在某一方优势过大的时候,舆论确实只能是优势方锦上添花,或劣势方无能狂怒的手段。
但当双方不分伯仲,战况僵持,或是某一方陷入险境,即将崩溃之时,舆论,便很可能会成为左右胜利天平的关键,甚至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……
“说说战事吧。”
“左右他长安朝堂,尽是牙尖嘴利之辈,我吴楚大军的忠臣良将,自比不得他长安朝堂巧舌如簧。”
“尽快把睢阳攻破,最好拿了梁王武!”
“到那时,再看看长安朝堂,还能说出个什么花出来。”
刘濞此言一出,众吴将自又是一阵哄笑,俨然一副不日便要攻破睢阳,兵临函谷的作态。
也不怪吴国的将军们自信;
实在是过去这一个多月,刘濞的吴楚叛军,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遇到。
一路上,沿途城池不是望风而逃,就是战战兢兢开城献降;
纵是有抵抗的,也不过是吴楚大军乌泱泱一冲,城墙上的戍卒就都跑没影了。
吴楚众将本以为:这不过是淮阳、梁地的小县城,自知无法阻挡吴楚大军的脚步,才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;
但在昨日,大军抵达睢阳,并试探性发起了一次进攻之后,原本就已经有些膨胀的吴楚众将,更愈发感到此战,胜算已经无限接近十成……
“大将军认为,若我军全力攻打,睢阳,能支撑多长时间?”
开口一问,刘濞便直勾勾望向距离最近的大将军田禄伯,目光中满含着期待。
闻言,田禄伯也没有让刘濞失望,只认认真真思考了一会儿,便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应答。
“从昨日,梁国军队的应对来看,应该大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。”
“虽然操演得当,但在我军突袭之后,大多数人都吓得愣在原地,即便偶有举剑者,也是无力挥砍。”
“——睢阳城头,大致有五十架床弩,本可予我军重创。”
“但昨日,末将率军冲了三次,那五十架床弩,却总共只射出四箭……”
说到此处,帐内又是一阵嘻嘻琐碎的窃笑,便是田禄伯那不苟言笑的面容之上,也悄然涌上一抹淡淡笑意。
再三思虑过后,才终是对吴王刘濞一拱手。
“依臣之见,如果梁王不尽快做出应对,单凭城中守卒昨日展现出的战力,睢阳城,至多只能抵挡我军半月!”
“当然,这是建立在睢阳守卒接下来的表现,都是昨日那般不堪入目,且长安朝堂的援军还没有抵达的前提下。”
“如果长安的援军抵达,尤其是援军不进入睢阳,而是在城外某处与睢阳互为犄角的话,那我大军除了要攻打睢阳,恐怕还要分出小半兵力,去防备这路援军。”
“届时,睢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攻下,就是无法推断的事了……”
随着田禄伯这番中肯、客观的分析,帐内原本欢愉无比的氛围,也终是稍趋于平静。
上首主位,吴王刘濞更是连连点下头,显然也对大将军田禄伯的这番话无比认同。
从昨日的状况来看,睢阳东城墙之上,至多不过两万梁国兵把守;
若是分兵围攻,南、北两面城墙,也至少需要梁王刘武安排各一万兵力,才能勉强抵御吴楚大军的攻击。
这,便是四万。
根据刘濞早先的估算,以及近些时日的查探,睢阳城内的守卒,至多也不过十万。
十万守卒,东、南、北三面城墙,却需要时刻维持四万人的战备状态;
这就意味着城内的十万守卒,连三批次轮换都做不到,大概率只能两班倒,再分出两万人马作为机动力量,以应对意外状况。
四万人,两班倒,面对的却是城外吴楚五十多万大军,可以分五批次以上,连绵不绝的进攻潮……
“长安传来消息:绛侯周亚夫,被长安天子拜为太尉,领兵十万,正向睢阳驰援而来。”
“外戚窦婴,也官拜大将军,率兵二十万,即将进驻荥阳-敖仓一向。”
“——窦婴东出函谷,当还要十余日才能抵达睢阳。”
“周亚夫所部,更是向南绕行武关,没有个二、三十日,是断不可能出现在睢阳附近的……”
初闻吴王刘濞提起绛侯周亚夫——尤其是‘绛侯’这二字,一众吴楚将领都不由心下一急!
实在是初代绛侯:武侯周勃,在关东众诸侯国,至今都还是鼎鼎大名,如雷贯耳。
乃至周亚夫,虽非嫡出,却也有先帝‘细柳阅兵’的故事,于关东大地广为流传,算是如今汉家最顶尖的将领,甚至都没有之一。
但在听到吴王刘濞说,周亚夫没有东出函谷,直扑睢阳而来,而是绕道武关,还要个把月才能抵达战场时,一众吴楚将帅,也不由暗下稍松了口气。
——还来得及,还有时间。
只要能在周亚夫赶到战场之前,一鼓作气攻下睢阳,甚至拿梁王刘武的性命来做筹码,那即便周亚夫怎般用兵如神,也不可能靠手里的十万兵马,去攻打彼时,有吴楚五十万大军守卫的睢阳城!
意识到这一点,众将面上神容只齐齐一肃,都不用吴王刘濞下令,便已经达成了默契。
速速攻下睢阳!
“传寡人将令!”
“我吴军主力,以三万人为一部,共十部,共计三十万兵马!”
“每部攻城一个时辰,十部交替轮换,日夜不休,强攻睢阳东城墙!”
···
“余下楚兵、别部二十万,以两万人为一部,共十部,各分五部于南、北城墙——同样挑灯夜战,轮番强攻!”
“十日之内,务必攻破睢阳城!”
刘濞军令下的果决,帐内众将也是轰然应诺,答应的极为爽快。
有过去这一个多月的连续胜利,以及昨日那试探性一击探清了睢阳的深浅,众将帅都有十足的信心,在十日之内攻下睢阳!
于是,带着必胜的斗志,以及对援军即将抵达的紧迫感,吴楚叛军主力在简单地修整过后,便正式开始了针对的睢阳城的进攻。
而在睢阳城东城墙之上,看着城外如虫蚁般涌来,又如潮水般退去的叛军,梁王刘武只呆愣愣眺望着,又猛咽了口唾沫···
咕噜!
“额……”
“第、第几日了?”
木然望向叛军退去的方向,呆愣愣站在城垛前,如梦呓般的一问,却惹得身旁的老将顿时咬紧了牙槽。
“第四日。”
“才第四日。”
“——吴楚贼军日夜不休,更不惜挑灯夜战,已有四日。”
“我睢阳将士寝食难安,和衣而睡,浴血奋战,也足有四日……”
老将沙哑疲惫的身线,终是将梁王刘武呆滞的目光从城墙外拉回。
转过身,便见老将浑身布满血污,面上髯须杂乱,也沾上了血、泥之类;
跨过老将的身影,望向不远处的城墙之上,梁王刘武更觉触目惊心。
——残肢断臂,遍地血污;
一具又一具尸体被抬下城墙,有守军的,有叛军的。
即便是幸存的将士们,也都难掩疲惫的抱着戈矛,背靠墙垛蹲下身,趁着这难得的休息时间闭上双眼,麻木的等候起下一声‘敌袭’。
“将士们,都已经很疲惫了……”
“伤亡如何?”
许是被遍目猩红所惊醒,梁王刘武总算是稍敛回心神。
开口一问,却又惹得老将一阵摇头哀叹。
“短短四日,我睢阳守军,战殁者便已有三千余!”
“因负伤而退回城墙内,等候诊治——更或直接不治者,恐怕倍之。”
“只四日,我睢阳守军九万,便已有近万人伤、亡;”
“将士们士气低迷,更多是麻木的挥砍、突刺,趁贼军退去稍歇片刻,再周而复始……”
“——将士们,是根本顾不上思考,也没心思去查看左右,少了多少袍泽的身影。”
“一旦贼军停止了攻势,将士们心里绷着的弦一松,军心士气,只怕是当即便要土崩瓦解……”
听着老将刻意压低着声线,以莫名哀愁的语调汇报着城内状况,梁王刘武的心,只一点点沉入谷底。
“敌袭!!!”
不片刻的功夫,城楼旁的瞭远台上,再度响起一声嘹亮的呼号。
城墙之上,将士们滞讷的从墙垛下起身,费力的睁开眼,将手中的兵器指向城外。
只是那一对对望向城外的双眸,有昏暗,有麻木,唯独不见丝毫战意,亦或是死战不退的决绝……
“长安的援军到哪里了?!”
接连几天的高压之下,梁王刘武显然也已经不堪重负,只是余光扫到城外的叛军再度涌来,便莫名感到一阵焦躁。
含怒发出一问,却只见身前老将一边抬起剑,将剑刃夹在手肘内侧一划;
将剑上血污大致擦去,才苦笑着抬头望向梁王刘武。
“大将军窦婴,还没到函谷关。”
“太尉周亚夫,更是要绕道武关——现在到没到武关,也是未知之数。”
“依臣之见,大王要想得保睢阳,恐怕不能再将希望,寄托在长安的援军上了。”
“若不另寻自救之法,睢阳城,不日即破……”
丢下这么一句话,老将便回过身,深吸一口气,大步朝着不远处的箭楼走去。
——原本应该在箭楼两侧墙垛防守的军士,已经有小半都负伤下了城墙。
这至少三人个人防守位置,只能由老将——只能由堂堂梁国中尉:张羽本人来驻守了。
“周亚夫!”
“寡人于汝,不共戴天!!!”
注视着城墙之上,将士们麻木准备应敌的身影;
耳边传来的,却是城墙外的叛军将士,在吃饱喝足、养精蓄锐之后,所发出的激昂喊杀声。
感受着这一切,梁王刘武双眼愈发明亮,却也愈发趋于猩红;
嘴唇更是随着逐渐激昂的战鼓声,而愈发强烈的颤动起来。
“大王!”
一声焦急地呼号,甚至都没能将将士们的目光吸引哪怕片刻,仍木然的将手中戈矛指向城墙外,正攀梯而上的叛军。
而在城楼之上,梁王刘武却毅然拔剑,先割下一片衣角,而后又在手掌上猛地一划!
带着所有的愤恨,用那血糊糊的手使劲揉搓着那片衣角,旋即便猛地回过身。
“去!”
“带着寡人的血书,去长安求援!”
“——向寡人的长兄,还有母亲,求援!!!”
言罢,梁王刘武持剑回身,目眦欲裂的望向城外,已经开始冒着箭羽发起冲锋的叛军将士。
“刘濞老贼!”
“且看尔僚那三二朽牙,可啃得下寡人这赳赳睢阳?!!”
长安朝堂派出的太尉周亚夫、大将军窦婴,以及车骑将军郦寄这三路平叛大军,也正式从蓝田大营开拔。
——窦婴所部东进,欲出函谷;
周亚夫、郦寄所部,则都自蓝田南下,绕道武关。
而在睢阳战役爆发之前,长安朝堂中央,与吴楚叛军之间的舆论战,也正式打响。
只是和军事上连战连捷,近乎平推到睢阳城下的出奇顺利截然相反的是:在舆论战上,吴王刘濞,就差没把底裤也给输进去……
·
·
·
“申屠嘉……”
睢阳东五十里,吴楚叛军大营,中军大帐。
看着手中,由长安朝堂颁行于天下,列数自己无数罪证的檄文,吴王刘濞原本还算愉快的心情,只瞬间蒙上了一层雾霾。
——倒也不是这封檄文上,写了什么出乎刘濞预料的内容。
左右不过抗旨不遵,举兵谋逆,居心叵测之类,都是刘濞早有心理准备的那套说辞。
真正让刘濞感到牙疼的是:这封讨贼檄文,属的是当朝丞相——申屠嘉的名。
这就让刘濞有些脸颊发烫了……
“寡人的檄文,前脚才刚指责长安‘帝相不和’,长安天子远贤臣、亲小人;”
“结果寡人口中的‘贤臣’,后脚就在征讨寡人的檄文上署名……”
“——署的还是‘汉相故安侯申屠嘉’的名?!”
半带自嘲,半带恼怒的一声反问,只惹得帐内为之一静,吴楚众将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愣是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在原本的历史上,这场吴楚之乱,是在明年春正月,洛阳宫被雷劈着火,连带着城墙也被烧了好几天,才让吴王刘濞自认‘得了天命’,从而下定决心举兵的。
而在这个时间线,吴王刘濞之所以会提前举兵,除了长安朝堂太过于咄咄逼人,开口就是削夺吴国的会稽、豫章两郡之外,最主要的原因,便是那则长安朝堂‘帝相不和’的传闻。
也正是基于此,吴王刘濞才以‘长安天子昏聩无道,薄待贤臣申屠嘉,亲近小人晁错’为名,打起了诛晁错、清君侧的旗号。
结果现在回过味来,什么‘帝相不和’之类,怕都是长安天子设的局,不过是引刘濞入套而已;
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,军队都已经开到睢阳城下了,被长安摆这么一道,吴王刘濞,多少有些尴尬。
——但也就仅限于尴尬了。
从帐内众将的面上神情也不难看出:除了吴王刘濞,并没有其他人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了不起。
“左右不过长安天子呈口舌之快,操弄权术的小把戏罢了,大王不必耿耿于怀!”
“他长安天子再怎么操弄权术,也总不至于凭这一纸檄文,就能将淮阳郡再给夺回去?”
“啊?”
老将满是肆意的一番话,只惹得帐内一阵哄笑不止。
便是吴王刘濞,也只是再低头看了看那檄文,便随手将其丢到了一旁。
面上,也逐渐涌上近些时日,时常挂在脸上的自信笑容。
——后世有一句话:战争,是政治的延伸。
而战争的胜利,往往能掩盖许多矛盾。
此时大帐内的情况,便大抵如是。
自彭城西出,兵指睢阳这数百里路,吴楚叛军主力连战连捷,甚至一日连下数城!
到如今,年关将至,举兵才刚一个多月,便已是尽下整个淮阳郡,外加梁国在都城睢阳以东的大部分城池。
再加上这些城池所贡献的兵力,此时的吴楚主力,除去最开始的三十万吴国军队、十万楚国兵马,又多了足足十数万的混编别部!
五十多万大军!
近乎与楚汉争霸之时,太祖高皇帝为攻打项羽的楚都,而征集的诸侯联军兵力平齐!
有如此大军,又有过往月余的连战连捷,吴王刘濞纵是对长安朝堂的‘小心机’感到恼怒,却也并没有太当回事。
还是那句话;
——天大地大,赢家最大!
若此战得胜,占据睢阳,从而将整个梁国也纳入控制范围之内,刘濞将来最差的结果,也至少是和长安划江而治!
届时,别说什么诛晁错、清君侧了——便是顺天应命,讨伐暴君之类的旗号,刘濞也没什么不敢打出来的。
若不能胜,则极有可能会功败垂成,兵败身亡。
无论胜败,刘濞和长安朝堂之间的舆论战,都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影响。
赢了,自有大儒为刘濞辩经;
输了,也有的是志向远大之辈,想要拿刘濞的人头去长安邀功。
反正都到了这一步,与其再去纠结舆论,倒不如赶紧把睢阳攻下来得实在。
——左右拿长安朝堂的舆论攻势没办法,刘濞便如是安慰着自己。
只是有一个问题,被刘濞或有意,或无意的忽视了。
舆论,确实无法成为决定性因素。
在某一方优势过大的时候,舆论确实只能是优势方锦上添花,或劣势方无能狂怒的手段。
但当双方不分伯仲,战况僵持,或是某一方陷入险境,即将崩溃之时,舆论,便很可能会成为左右胜利天平的关键,甚至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……
“说说战事吧。”
“左右他长安朝堂,尽是牙尖嘴利之辈,我吴楚大军的忠臣良将,自比不得他长安朝堂巧舌如簧。”
“尽快把睢阳攻破,最好拿了梁王武!”
“到那时,再看看长安朝堂,还能说出个什么花出来。”
刘濞此言一出,众吴将自又是一阵哄笑,俨然一副不日便要攻破睢阳,兵临函谷的作态。
也不怪吴国的将军们自信;
实在是过去这一个多月,刘濞的吴楚叛军,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遇到。
一路上,沿途城池不是望风而逃,就是战战兢兢开城献降;
纵是有抵抗的,也不过是吴楚大军乌泱泱一冲,城墙上的戍卒就都跑没影了。
吴楚众将本以为:这不过是淮阳、梁地的小县城,自知无法阻挡吴楚大军的脚步,才‘识时务者为俊杰’;
但在昨日,大军抵达睢阳,并试探性发起了一次进攻之后,原本就已经有些膨胀的吴楚众将,更愈发感到此战,胜算已经无限接近十成……
“大将军认为,若我军全力攻打,睢阳,能支撑多长时间?”
开口一问,刘濞便直勾勾望向距离最近的大将军田禄伯,目光中满含着期待。
闻言,田禄伯也没有让刘濞失望,只认认真真思考了一会儿,便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应答。
“从昨日,梁国军队的应对来看,应该大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兵。”
“虽然操演得当,但在我军突袭之后,大多数人都吓得愣在原地,即便偶有举剑者,也是无力挥砍。”
“——睢阳城头,大致有五十架床弩,本可予我军重创。”
“但昨日,末将率军冲了三次,那五十架床弩,却总共只射出四箭……”
说到此处,帐内又是一阵嘻嘻琐碎的窃笑,便是田禄伯那不苟言笑的面容之上,也悄然涌上一抹淡淡笑意。
再三思虑过后,才终是对吴王刘濞一拱手。
“依臣之见,如果梁王不尽快做出应对,单凭城中守卒昨日展现出的战力,睢阳城,至多只能抵挡我军半月!”
“当然,这是建立在睢阳守卒接下来的表现,都是昨日那般不堪入目,且长安朝堂的援军还没有抵达的前提下。”
“如果长安的援军抵达,尤其是援军不进入睢阳,而是在城外某处与睢阳互为犄角的话,那我大军除了要攻打睢阳,恐怕还要分出小半兵力,去防备这路援军。”
“届时,睢阳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攻下,就是无法推断的事了……”
随着田禄伯这番中肯、客观的分析,帐内原本欢愉无比的氛围,也终是稍趋于平静。
上首主位,吴王刘濞更是连连点下头,显然也对大将军田禄伯的这番话无比认同。
从昨日的状况来看,睢阳东城墙之上,至多不过两万梁国兵把守;
若是分兵围攻,南、北两面城墙,也至少需要梁王刘武安排各一万兵力,才能勉强抵御吴楚大军的攻击。
这,便是四万。
根据刘濞早先的估算,以及近些时日的查探,睢阳城内的守卒,至多也不过十万。
十万守卒,东、南、北三面城墙,却需要时刻维持四万人的战备状态;
这就意味着城内的十万守卒,连三批次轮换都做不到,大概率只能两班倒,再分出两万人马作为机动力量,以应对意外状况。
四万人,两班倒,面对的却是城外吴楚五十多万大军,可以分五批次以上,连绵不绝的进攻潮……
“长安传来消息:绛侯周亚夫,被长安天子拜为太尉,领兵十万,正向睢阳驰援而来。”
“外戚窦婴,也官拜大将军,率兵二十万,即将进驻荥阳-敖仓一向。”
“——窦婴东出函谷,当还要十余日才能抵达睢阳。”
“周亚夫所部,更是向南绕行武关,没有个二、三十日,是断不可能出现在睢阳附近的……”
初闻吴王刘濞提起绛侯周亚夫——尤其是‘绛侯’这二字,一众吴楚将领都不由心下一急!
实在是初代绛侯:武侯周勃,在关东众诸侯国,至今都还是鼎鼎大名,如雷贯耳。
乃至周亚夫,虽非嫡出,却也有先帝‘细柳阅兵’的故事,于关东大地广为流传,算是如今汉家最顶尖的将领,甚至都没有之一。
但在听到吴王刘濞说,周亚夫没有东出函谷,直扑睢阳而来,而是绕道武关,还要个把月才能抵达战场时,一众吴楚将帅,也不由暗下稍松了口气。
——还来得及,还有时间。
只要能在周亚夫赶到战场之前,一鼓作气攻下睢阳,甚至拿梁王刘武的性命来做筹码,那即便周亚夫怎般用兵如神,也不可能靠手里的十万兵马,去攻打彼时,有吴楚五十万大军守卫的睢阳城!
意识到这一点,众将面上神容只齐齐一肃,都不用吴王刘濞下令,便已经达成了默契。
速速攻下睢阳!
“传寡人将令!”
“我吴军主力,以三万人为一部,共十部,共计三十万兵马!”
“每部攻城一个时辰,十部交替轮换,日夜不休,强攻睢阳东城墙!”
···
“余下楚兵、别部二十万,以两万人为一部,共十部,各分五部于南、北城墙——同样挑灯夜战,轮番强攻!”
“十日之内,务必攻破睢阳城!”
刘濞军令下的果决,帐内众将也是轰然应诺,答应的极为爽快。
有过去这一个多月的连续胜利,以及昨日那试探性一击探清了睢阳的深浅,众将帅都有十足的信心,在十日之内攻下睢阳!
于是,带着必胜的斗志,以及对援军即将抵达的紧迫感,吴楚叛军主力在简单地修整过后,便正式开始了针对的睢阳城的进攻。
而在睢阳城东城墙之上,看着城外如虫蚁般涌来,又如潮水般退去的叛军,梁王刘武只呆愣愣眺望着,又猛咽了口唾沫···
咕噜!
“额……”
“第、第几日了?”
木然望向叛军退去的方向,呆愣愣站在城垛前,如梦呓般的一问,却惹得身旁的老将顿时咬紧了牙槽。
“第四日。”
“才第四日。”
“——吴楚贼军日夜不休,更不惜挑灯夜战,已有四日。”
“我睢阳将士寝食难安,和衣而睡,浴血奋战,也足有四日……”
老将沙哑疲惫的身线,终是将梁王刘武呆滞的目光从城墙外拉回。
转过身,便见老将浑身布满血污,面上髯须杂乱,也沾上了血、泥之类;
跨过老将的身影,望向不远处的城墙之上,梁王刘武更觉触目惊心。
——残肢断臂,遍地血污;
一具又一具尸体被抬下城墙,有守军的,有叛军的。
即便是幸存的将士们,也都难掩疲惫的抱着戈矛,背靠墙垛蹲下身,趁着这难得的休息时间闭上双眼,麻木的等候起下一声‘敌袭’。
“将士们,都已经很疲惫了……”
“伤亡如何?”
许是被遍目猩红所惊醒,梁王刘武总算是稍敛回心神。
开口一问,却又惹得老将一阵摇头哀叹。
“短短四日,我睢阳守军,战殁者便已有三千余!”
“因负伤而退回城墙内,等候诊治——更或直接不治者,恐怕倍之。”
“只四日,我睢阳守军九万,便已有近万人伤、亡;”
“将士们士气低迷,更多是麻木的挥砍、突刺,趁贼军退去稍歇片刻,再周而复始……”
“——将士们,是根本顾不上思考,也没心思去查看左右,少了多少袍泽的身影。”
“一旦贼军停止了攻势,将士们心里绷着的弦一松,军心士气,只怕是当即便要土崩瓦解……”
听着老将刻意压低着声线,以莫名哀愁的语调汇报着城内状况,梁王刘武的心,只一点点沉入谷底。
“敌袭!!!”
不片刻的功夫,城楼旁的瞭远台上,再度响起一声嘹亮的呼号。
城墙之上,将士们滞讷的从墙垛下起身,费力的睁开眼,将手中的兵器指向城外。
只是那一对对望向城外的双眸,有昏暗,有麻木,唯独不见丝毫战意,亦或是死战不退的决绝……
“长安的援军到哪里了?!”
接连几天的高压之下,梁王刘武显然也已经不堪重负,只是余光扫到城外的叛军再度涌来,便莫名感到一阵焦躁。
含怒发出一问,却只见身前老将一边抬起剑,将剑刃夹在手肘内侧一划;
将剑上血污大致擦去,才苦笑着抬头望向梁王刘武。
“大将军窦婴,还没到函谷关。”
“太尉周亚夫,更是要绕道武关——现在到没到武关,也是未知之数。”
“依臣之见,大王要想得保睢阳,恐怕不能再将希望,寄托在长安的援军上了。”
“若不另寻自救之法,睢阳城,不日即破……”
丢下这么一句话,老将便回过身,深吸一口气,大步朝着不远处的箭楼走去。
——原本应该在箭楼两侧墙垛防守的军士,已经有小半都负伤下了城墙。
这至少三人个人防守位置,只能由老将——只能由堂堂梁国中尉:张羽本人来驻守了。
“周亚夫!”
“寡人于汝,不共戴天!!!”
注视着城墙之上,将士们麻木准备应敌的身影;
耳边传来的,却是城墙外的叛军将士,在吃饱喝足、养精蓄锐之后,所发出的激昂喊杀声。
感受着这一切,梁王刘武双眼愈发明亮,却也愈发趋于猩红;
嘴唇更是随着逐渐激昂的战鼓声,而愈发强烈的颤动起来。
“大王!”
一声焦急地呼号,甚至都没能将将士们的目光吸引哪怕片刻,仍木然的将手中戈矛指向城墙外,正攀梯而上的叛军。
而在城楼之上,梁王刘武却毅然拔剑,先割下一片衣角,而后又在手掌上猛地一划!
带着所有的愤恨,用那血糊糊的手使劲揉搓着那片衣角,旋即便猛地回过身。
“去!”
“带着寡人的血书,去长安求援!”
“——向寡人的长兄,还有母亲,求援!!!”
言罢,梁王刘武持剑回身,目眦欲裂的望向城外,已经开始冒着箭羽发起冲锋的叛军将士。
“刘濞老贼!”
“且看尔僚那三二朽牙,可啃得下寡人这赳赳睢阳?!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