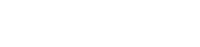“儿,当然不敢对皇祖母怎样。”
“莫说是皇祖母——便是馆陶姑母,那也是能压的儿喘不过气来的。”
未央宫,凤凰殿。
发现自己对那些因自己‘落难’而各奔东西的宫人的处置,似乎让母亲有些胆颤,刘荣便不自然的将话题转移开来。
当母亲问起‘我儿难道要和太后为敌?’,刘荣只如是道出一语,旋即无奈的耸了耸肩。
“自吕太后以来,我汉家,便一直是有两个皇帝的。”
“——一个,是西宫未央的天子,一个,便是东宫长乐的太后。”
“虽说诸吕之乱后,东宫太后多了个‘恐复为吕氏’的忌讳,但终归还是天子的母亲,母仪天下的汉太后。”
“就连父皇,对皇祖母那都是慎之又慎,虽谈不上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,却也绝对算不得轻松。”
“父皇尚且如此——我汉家的天子尚且如此,自更别提儿这个连储君都还不是的皇长子了。”
见刘荣愿意给自己讲这些,栗姬只本能的感到高兴。
曾几何时,栗姬和刘荣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,已是疏离到刘荣根本不愿意多说一句话,除了日常见礼、告退,更是连一個眼神都不愿意给母亲的程度。
尤其是去年,栗姬严词拒绝馆陶公主刘嫖的姻亲之后,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,更是降到了临近冰点。
距今为止,栗姬其实也还是不大明白:自己拒绝刘嫖,究竟为何会让儿子刘荣那般恼怒。
但经历过那段被儿子疏离,甚至是漠视的日子之后,对于儿子愿意对自己提起的话,栗姬都很乐意去听。
——哪怕听不懂。
果不其然,刘荣一番话道出口,栗姬便愈发不解了起来,眉头更是应声拧在了一起。
“既然如此,我儿又为何……?”
见母亲问起,刘荣却是一时语塞,陷入了短暂的纠结当中。
刘荣知道,无论自己说的再怎么直白、剖析的再如何细致,母亲该听不懂,也还是听不懂。
非但听不懂,还可能会说漏了嘴,从而坏了事。
不能说,又不忍心完全不说——最终,刘荣只带着坚定地目光,抬头望向面前的母亲。
“母亲,可信得过儿?”
闻言,栗姬只本能的点下头,又微咧嘴一笑:“这话说的……”
“连儿子都信不过,我还能信谁?”
得到满意的答案,刘荣面上郑重之色稍缓,只轻轻拉过母亲的手,含笑低下头。
过了许久,才温声道:“儿,是在为母亲和老二老三,也是在为自己拼前程。”
“此事,牵连甚广!”
“——皇祖母,馆陶姑母,梁王叔,父皇,还有绮兰殿,乃至宣明殿、广明殿,薄、窦外戚,都无不于此事有关。”
“甚至就连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,也与此事关联甚深。”
“待日后时机成熟,儿自会娓娓道来,悉数讲给母亲听。”
“及当下,母亲只须知道:儿,是在做大事,而且是和父皇站在一边。”
“看似险象环生,又是挨板子、又是在太庙饿肚子,实则,却根本不曾涉险……”
嘴上虽是这么说,但刘荣心里却并没这么轻松。
危险,是有的。
或者应该说:刘荣的每一步棋,都是在兵行险着。
一着不慎,便会满盘皆输,乃至万劫不复。
便说这回的事,死神的镰刀,就至少有三次擦着刘荣的头皮,从刘荣头顶上挥舞而过。
——窦太后,不是非得从太庙里,把刘荣兄弟俩接出来的。
不给刘荣当面对峙,巧舌诡辩的机会,直接对外放出话,说皇长子咒太后早死!
然后‘盛怒’之下,勒令刘荣在太庙思过,直到活生生饿死在太庙,也根本没人能挑的出错。
我没想饿死皇长子啊?
我只是让他在太庙思过而已。
什么?
没人给送饭?
来人!
把负责送饭的人给斩了!!!
刘荣赌赢了。
赌窦太后,不敢让自己的手沾上刘氏宗亲的血,从而顶上‘或复为吕氏’的大帽——刘荣赌赢了。
这是第一次。
第二次,便是深宫里的那位太皇太后。
作为当今天子启的祖母、当朝窦太后的婆婆——尤其还是作为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姬妾,薄太皇太后哪怕避居深宫,所掌握的力量、所能造成的影响,都是无与伦比的庞大!
若是不顾生前身后名,拼着身败名裂也要出手,那别说是惩治刘荣这个皇长子了;
便是要废立天子,乃至废太后,也根本没人能挑的出程序上的错!
刘荣猜对了。
猜薄太皇太后,会一如往常的束手旁观,不问世事——刘荣猜对了。
第三次,便是今日宫宴……
“若皇祖母狠得下心,直接放弃与立皇太弟,并拼死‘自证清白’的话……”
“呼~”
“坏了父皇的大事是小,将祖母太后逼到那般地步,我这不肖子孙,可就不得不‘羞愧自尽’了……”
一时间,刘荣心底只阵阵发寒。
去年,太宗孝文皇帝驾崩,窦太后想要召梁王刘武入朝奔丧,天子启以‘不合制度’将此事搁置。
然后,窦太后绝食了三天。
此事过去了一年,至今都还有人拿着此事,骂天子启不遵孝道!
彼时的天子启无奈之下,只得赶忙召梁王入朝,又跑去长乐宫好说歹说,才让窦太后吃了些东西。
亲眼看着母亲吃下饭,天子启才顶着‘不孝东宫’的骂名,身心俱疲的回到了未央宫。
天子尚且如此——面对孝道,天子尚且这般无奈,更枉论刘荣这区区一个皇长子。
只是除了这么做,刘荣,别无选择。
要想顺利住进太子宫,刘荣必须时刻站在天子启这一边,并在未来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,拿出足够多的筹码。
——足以让天子启下定决心,在那封册立储君的诏书上,盖下那方传国玉玺的筹码……
“我儿既有了盘算,我便也就不多问了。”
“——左右我儿说了,我当也不大能明白。”
“只是下回,总要提前跟我说一声……”
见母亲眨眼间又红了眼眶,刘荣心下一阵动容之余,也悄然涌过一股暖流。
好歹还有母亲。
刘荣,好歹还有个母亲……
“往后这几个月,梁王叔,应该会一直在长安。”
“凤凰殿,还是照旧封着吧——免得节外生枝。”
刘荣一语,栗姬只温笑着点下头,又如释重负般,长呼出一口气。
“听我儿的。”
“我儿有了盘算,便都由我儿做主,我也乐得落个轻松……”
“莫说是皇祖母——便是馆陶姑母,那也是能压的儿喘不过气来的。”
未央宫,凤凰殿。
发现自己对那些因自己‘落难’而各奔东西的宫人的处置,似乎让母亲有些胆颤,刘荣便不自然的将话题转移开来。
当母亲问起‘我儿难道要和太后为敌?’,刘荣只如是道出一语,旋即无奈的耸了耸肩。
“自吕太后以来,我汉家,便一直是有两个皇帝的。”
“——一个,是西宫未央的天子,一个,便是东宫长乐的太后。”
“虽说诸吕之乱后,东宫太后多了个‘恐复为吕氏’的忌讳,但终归还是天子的母亲,母仪天下的汉太后。”
“就连父皇,对皇祖母那都是慎之又慎,虽谈不上战战兢兢、如履薄冰,却也绝对算不得轻松。”
“父皇尚且如此——我汉家的天子尚且如此,自更别提儿这个连储君都还不是的皇长子了。”
见刘荣愿意给自己讲这些,栗姬只本能的感到高兴。
曾几何时,栗姬和刘荣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,已是疏离到刘荣根本不愿意多说一句话,除了日常见礼、告退,更是连一個眼神都不愿意给母亲的程度。
尤其是去年,栗姬严词拒绝馆陶公主刘嫖的姻亲之后,母子二人之间的关系,更是降到了临近冰点。
距今为止,栗姬其实也还是不大明白:自己拒绝刘嫖,究竟为何会让儿子刘荣那般恼怒。
但经历过那段被儿子疏离,甚至是漠视的日子之后,对于儿子愿意对自己提起的话,栗姬都很乐意去听。
——哪怕听不懂。
果不其然,刘荣一番话道出口,栗姬便愈发不解了起来,眉头更是应声拧在了一起。
“既然如此,我儿又为何……?”
见母亲问起,刘荣却是一时语塞,陷入了短暂的纠结当中。
刘荣知道,无论自己说的再怎么直白、剖析的再如何细致,母亲该听不懂,也还是听不懂。
非但听不懂,还可能会说漏了嘴,从而坏了事。
不能说,又不忍心完全不说——最终,刘荣只带着坚定地目光,抬头望向面前的母亲。
“母亲,可信得过儿?”
闻言,栗姬只本能的点下头,又微咧嘴一笑:“这话说的……”
“连儿子都信不过,我还能信谁?”
得到满意的答案,刘荣面上郑重之色稍缓,只轻轻拉过母亲的手,含笑低下头。
过了许久,才温声道:“儿,是在为母亲和老二老三,也是在为自己拼前程。”
“此事,牵连甚广!”
“——皇祖母,馆陶姑母,梁王叔,父皇,还有绮兰殿,乃至宣明殿、广明殿,薄、窦外戚,都无不于此事有关。”
“甚至就连我汉家的宗庙、社稷,也与此事关联甚深。”
“待日后时机成熟,儿自会娓娓道来,悉数讲给母亲听。”
“及当下,母亲只须知道:儿,是在做大事,而且是和父皇站在一边。”
“看似险象环生,又是挨板子、又是在太庙饿肚子,实则,却根本不曾涉险……”
嘴上虽是这么说,但刘荣心里却并没这么轻松。
危险,是有的。
或者应该说:刘荣的每一步棋,都是在兵行险着。
一着不慎,便会满盘皆输,乃至万劫不复。
便说这回的事,死神的镰刀,就至少有三次擦着刘荣的头皮,从刘荣头顶上挥舞而过。
——窦太后,不是非得从太庙里,把刘荣兄弟俩接出来的。
不给刘荣当面对峙,巧舌诡辩的机会,直接对外放出话,说皇长子咒太后早死!
然后‘盛怒’之下,勒令刘荣在太庙思过,直到活生生饿死在太庙,也根本没人能挑的出错。
我没想饿死皇长子啊?
我只是让他在太庙思过而已。
什么?
没人给送饭?
来人!
把负责送饭的人给斩了!!!
刘荣赌赢了。
赌窦太后,不敢让自己的手沾上刘氏宗亲的血,从而顶上‘或复为吕氏’的大帽——刘荣赌赢了。
这是第一次。
第二次,便是深宫里的那位太皇太后。
作为当今天子启的祖母、当朝窦太后的婆婆——尤其还是作为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姬妾,薄太皇太后哪怕避居深宫,所掌握的力量、所能造成的影响,都是无与伦比的庞大!
若是不顾生前身后名,拼着身败名裂也要出手,那别说是惩治刘荣这个皇长子了;
便是要废立天子,乃至废太后,也根本没人能挑的出程序上的错!
刘荣猜对了。
猜薄太皇太后,会一如往常的束手旁观,不问世事——刘荣猜对了。
第三次,便是今日宫宴……
“若皇祖母狠得下心,直接放弃与立皇太弟,并拼死‘自证清白’的话……”
“呼~”
“坏了父皇的大事是小,将祖母太后逼到那般地步,我这不肖子孙,可就不得不‘羞愧自尽’了……”
一时间,刘荣心底只阵阵发寒。
去年,太宗孝文皇帝驾崩,窦太后想要召梁王刘武入朝奔丧,天子启以‘不合制度’将此事搁置。
然后,窦太后绝食了三天。
此事过去了一年,至今都还有人拿着此事,骂天子启不遵孝道!
彼时的天子启无奈之下,只得赶忙召梁王入朝,又跑去长乐宫好说歹说,才让窦太后吃了些东西。
亲眼看着母亲吃下饭,天子启才顶着‘不孝东宫’的骂名,身心俱疲的回到了未央宫。
天子尚且如此——面对孝道,天子尚且这般无奈,更枉论刘荣这区区一个皇长子。
只是除了这么做,刘荣,别无选择。
要想顺利住进太子宫,刘荣必须时刻站在天子启这一边,并在未来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,拿出足够多的筹码。
——足以让天子启下定决心,在那封册立储君的诏书上,盖下那方传国玉玺的筹码……
“我儿既有了盘算,我便也就不多问了。”
“——左右我儿说了,我当也不大能明白。”
“只是下回,总要提前跟我说一声……”
见母亲眨眼间又红了眼眶,刘荣心下一阵动容之余,也悄然涌过一股暖流。
好歹还有母亲。
刘荣,好歹还有个母亲……
“往后这几个月,梁王叔,应该会一直在长安。”
“凤凰殿,还是照旧封着吧——免得节外生枝。”
刘荣一语,栗姬只温笑着点下头,又如释重负般,长呼出一口气。
“听我儿的。”
“我儿有了盘算,便都由我儿做主,我也乐得落个轻松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