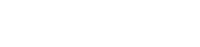这一下,凤凰殿是真的‘闭门谢客’了。
——天子启口谕:皇长子母栗姬,教子无方,罚俸一年,禁足凤凰殿!
——皇长子荣、次子德、三子淤,嚣扬跋扈,无限期禁足思过!
消息传出,朝堂默然,朝野内外鸦雀无声。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皇长子这一次,怕是真的要向储君太子之位挥手告别了。
只是这件事的后续,有一些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,并不曾被人们关注。
首先,作为刘荣‘嚣扬跋扈’的帮凶,那些出身凤凰殿,遵刘荣之令打死那女官的寺人们,并没有得到太过严重的惩罚;
非但没丢掉小命,反而还被‘罚’去了刘荣身边,美其名曰:盯着皇长子禁足,以赎罪过。
其次,在刘荣被‘无限期禁足’的同时,太医属也派了几名太医,为刘荣诊治起了后腰、后股处的伤势。
最为关键的是:那被打死的女官,尸首即没有被刘荣下令收敛,也不曾被绮兰殿收走;
就那么在绮兰殿外,由天子启的贴身官宦盯着,晾了足有三日,才被丢去了长安城外的乱葬岗。
其间,王夫人不止一次派人,想要收走那好似巴掌印般,明晃晃晾在绮兰殿外的尸首。
但对此,天子启的贴身老宦官,却只答了一句话。
——既然不是夫人指使,那此人,便不再是绮兰殿的人了。
就这么战战兢兢等了三天,直到那具尸首消失在殿外,王夫人才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,从宫外叫来了自己的弟弟:田蚡。
也是直到田蚡走入宫中,出现在绮兰殿的那一刻,王夫人多日来积攒的惶恐,才终得以宣泄出来……
·
·
·
“宫外如何?!”
见到弟弟田蚡的第一时间,王娡便是连招呼都顾不上打,只赶忙上前,仅仅抓住了田蚡的手臂!
看出姐姐王娡此时的慌乱,田蚡也只沉着脸,面色凝重的摇了摇头。
“皇长子此番,当真是把许多人都吓坏了……”
“虽说被陛下禁足,让很多人都认为皇长子惹下了大祸,自此回天乏术,却也有不少人认为:皇长子如此作为,却也颇有人主之相……”
作为王娡最为信任的母族助力,甚至可以说是皇十子刘彘争储夺嫡的急先锋,尤其还是作为商贾,田蚡对很多事,看的都比大多数人透彻。
皇长子被禁足?
听起来是挺吓人,但实际上,皇长子本来就才挨了板子,身上还带着伤呢;
就算没被禁足,回宫之后,也是肯定要在凤凰殿卧榻静养的。
至于栗姬也被禁足,听起来像是受到了惩罚,但田蚡用膝盖都能想到:此时的皇长子,肯定是乐开了花。
——正愁着怎样才能让母亲别再闹出乱子,天子的禁足令就适时送到,皇长子能不开心?
再考虑到‘禁足’刘荣之后,天子启也没忘派太医去给刘荣治病,以及天子启在这件事上的后续处理……
田蚡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:此番,天子启看似是重重惩治了刘荣母子,但实际上,不过是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。
反倒是绮兰殿,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惩罚,实则……
“近几日,陛下可曾来看过姐姐?”
语带凝重的一问,只惹得王娡面带忐忑的摇摇头:“不曾。”
“便是儿姁(xu)那里,陛下也不曾来过。”
只此一语,便惹得田蚡满是苦涩的闭上双眼,轻叹着缓缓摇起头。
对于后宫的女人而言,很多事情,其实都能凭这一点判断出是吉是凶;
——事后,天子有没有来过。
就拿这次的事来说,如果天子启当真认为绮兰殿、王娡毫无过错,整个事件都是皇长子刘荣全责,那在事后,天子启肯定会来绮兰殿一趟。
温言抚慰也好,隐晦敲打也罢;
便是对发生的事只字不提,只单纯的来走上一趟、坐上一会儿,聊一些毫无意义的家长里短,也足以说明很多事情。
但天子启没来。
非但没来‘受了委屈、欺辱’的王娡这里,就连怀着龙子凤孙,不日便要临盆的王儿姁,天子启也没来探望。
这样一来,这件事在天子启那里的性质,也就是一目了然的了。
“此番,恐怕就连陛下,也对姐姐失望了啊……”
满是唏嘘得一声感叹,终是让王娡烦躁的深吸一口气,又实在按捺不下惊惧,愤愤咬紧了后槽牙。
“那贱婢,当真是害苦了我……”
此言一出,田蚡当即一愣,满是不可置信道:“这件事,不是姐姐暗中授意?”
却见王娡满是不屑的冷哼一声:“我有那么蠢?!”
“便是要设计,也总不至于傻到派自家下人去做?”
“——还不是那贱婢自作主张!!!”
“若是早点知道,我好歹也能想办法找补,总不至于这般被动!”
听闻王娡此言,田蚡只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本就苦涩的面庞之上,也更多出一分唏嘘。
“是啊……”
“姐姐再傻,也总不至于傻到派自己身边的人,去光明正大的做这种事情。”
“——早先我还奇怪:那日,皇长子怎就那般痛快,替姐姐将那女官灭了口。”
“如此看来,只怕是皇长子也早知此事,与姐姐无甚大关联……”
说着,田蚡便又是一阵摇头苦笑,旋即意味深长道:“怕是往日,我们,都看错皇长子了。”
“就此次的事来看,皇长子,绝非善类……”
许是有田蚡在身边,又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,王娡也逐渐从惶恐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。
又闻田蚡此言,便深吸一口气,面色凝重道:“终归是皇长子,半个准储君。”
“若是连这点手段都没有,倒也省的我姐弟为之头疼了。”
“唉……”
“——若那贱婢还活着,我倒还能把人被陛下送去,以自证清白。”
“只如今死无对证,我便是有心自证,却也百口莫辩……”
随着王娡这满含愤闷的话语,姐弟二人便也就此沉默了下来。
显而易见:这次的事,王娡被刘荣打了个措手不及,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。
事情闹到如今这个地步,也已经没有了继续纠缠下去的意义。
最明智的做法,就是将此事冷处理,打碎牙齿和血吞,吃下这个哑巴亏。
至于以后……
“馆陶公主那边,可搭上线了?”
沉思良久,王娡终轻声发出一问,却惹得田蚡一阵苦笑不止。
“倒是见了一面。”
“只是光见这一面,就贴进去不下千金的拜礼;”
“听话里话外的意思,要想谈成那件事,只怕是……”
听出田蚡话中埋怨,王娡也不由眼底一黯,悠悠道:“你长陵田氏,难道还缺这点黄白之物?”
“还是我儿彘,不值得你长陵田氏花些钱、金?”
便见田蚡嘿嘿一阵讪笑,又颇有些不自然的挠了挠头。
“瞧姐姐这话说的;”
“——我姐弟二人虽非同姓,却也终归是一個母亲所生。”
“彘儿大了,也总还是要唤我一声舅父的。”
“只是姐姐也知道,我田氏纵然家大业大,也终归不全是我这少主说了算。”
“动辄数千上万金的花销,若是换不来入项,我也没法给族人交代?”
说到最后,田蚡的语调之中,也已是隐约带上了些期翼。
对此,王娡自也不会装傻充楞。
只深吸一口气,又漠然望向殿门的方向,好似自言自语般,为田蚡给出了自己的承诺。
“商贾末业,终归不是正道。”
“指不定什么时候,便要被某家勋贵、某任丞相抄了宅院,毁了宗祠。”
“这几年,兄弟可得好好想想:等日后,要如何处置那硕大产业。”
“——再怎么说,堂堂国舅,本是可以入朝为官、封侯拜相的。”
“若仍自甘堕落,行商做贾,总归要惹人笑话……”
——天子启口谕:皇长子母栗姬,教子无方,罚俸一年,禁足凤凰殿!
——皇长子荣、次子德、三子淤,嚣扬跋扈,无限期禁足思过!
消息传出,朝堂默然,朝野内外鸦雀无声。
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皇长子这一次,怕是真的要向储君太子之位挥手告别了。
只是这件事的后续,有一些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,并不曾被人们关注。
首先,作为刘荣‘嚣扬跋扈’的帮凶,那些出身凤凰殿,遵刘荣之令打死那女官的寺人们,并没有得到太过严重的惩罚;
非但没丢掉小命,反而还被‘罚’去了刘荣身边,美其名曰:盯着皇长子禁足,以赎罪过。
其次,在刘荣被‘无限期禁足’的同时,太医属也派了几名太医,为刘荣诊治起了后腰、后股处的伤势。
最为关键的是:那被打死的女官,尸首即没有被刘荣下令收敛,也不曾被绮兰殿收走;
就那么在绮兰殿外,由天子启的贴身官宦盯着,晾了足有三日,才被丢去了长安城外的乱葬岗。
其间,王夫人不止一次派人,想要收走那好似巴掌印般,明晃晃晾在绮兰殿外的尸首。
但对此,天子启的贴身老宦官,却只答了一句话。
——既然不是夫人指使,那此人,便不再是绮兰殿的人了。
就这么战战兢兢等了三天,直到那具尸首消失在殿外,王夫人才终于怀着忐忑的心情,从宫外叫来了自己的弟弟:田蚡。
也是直到田蚡走入宫中,出现在绮兰殿的那一刻,王夫人多日来积攒的惶恐,才终得以宣泄出来……
·
·
·
“宫外如何?!”
见到弟弟田蚡的第一时间,王娡便是连招呼都顾不上打,只赶忙上前,仅仅抓住了田蚡的手臂!
看出姐姐王娡此时的慌乱,田蚡也只沉着脸,面色凝重的摇了摇头。
“皇长子此番,当真是把许多人都吓坏了……”
“虽说被陛下禁足,让很多人都认为皇长子惹下了大祸,自此回天乏术,却也有不少人认为:皇长子如此作为,却也颇有人主之相……”
作为王娡最为信任的母族助力,甚至可以说是皇十子刘彘争储夺嫡的急先锋,尤其还是作为商贾,田蚡对很多事,看的都比大多数人透彻。
皇长子被禁足?
听起来是挺吓人,但实际上,皇长子本来就才挨了板子,身上还带着伤呢;
就算没被禁足,回宫之后,也是肯定要在凤凰殿卧榻静养的。
至于栗姬也被禁足,听起来像是受到了惩罚,但田蚡用膝盖都能想到:此时的皇长子,肯定是乐开了花。
——正愁着怎样才能让母亲别再闹出乱子,天子的禁足令就适时送到,皇长子能不开心?
再考虑到‘禁足’刘荣之后,天子启也没忘派太医去给刘荣治病,以及天子启在这件事上的后续处理……
田蚡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:此番,天子启看似是重重惩治了刘荣母子,但实际上,不过是高高举起,轻轻放下。
反倒是绮兰殿,看上去没有受到任何惩罚,实则……
“近几日,陛下可曾来看过姐姐?”
语带凝重的一问,只惹得王娡面带忐忑的摇摇头:“不曾。”
“便是儿姁(xu)那里,陛下也不曾来过。”
只此一语,便惹得田蚡满是苦涩的闭上双眼,轻叹着缓缓摇起头。
对于后宫的女人而言,很多事情,其实都能凭这一点判断出是吉是凶;
——事后,天子有没有来过。
就拿这次的事来说,如果天子启当真认为绮兰殿、王娡毫无过错,整个事件都是皇长子刘荣全责,那在事后,天子启肯定会来绮兰殿一趟。
温言抚慰也好,隐晦敲打也罢;
便是对发生的事只字不提,只单纯的来走上一趟、坐上一会儿,聊一些毫无意义的家长里短,也足以说明很多事情。
但天子启没来。
非但没来‘受了委屈、欺辱’的王娡这里,就连怀着龙子凤孙,不日便要临盆的王儿姁,天子启也没来探望。
这样一来,这件事在天子启那里的性质,也就是一目了然的了。
“此番,恐怕就连陛下,也对姐姐失望了啊……”
满是唏嘘得一声感叹,终是让王娡烦躁的深吸一口气,又实在按捺不下惊惧,愤愤咬紧了后槽牙。
“那贱婢,当真是害苦了我……”
此言一出,田蚡当即一愣,满是不可置信道:“这件事,不是姐姐暗中授意?”
却见王娡满是不屑的冷哼一声:“我有那么蠢?!”
“便是要设计,也总不至于傻到派自家下人去做?”
“——还不是那贱婢自作主张!!!”
“若是早点知道,我好歹也能想办法找补,总不至于这般被动!”
听闻王娡此言,田蚡只悠悠发出一声长叹,本就苦涩的面庞之上,也更多出一分唏嘘。
“是啊……”
“姐姐再傻,也总不至于傻到派自己身边的人,去光明正大的做这种事情。”
“——早先我还奇怪:那日,皇长子怎就那般痛快,替姐姐将那女官灭了口。”
“如此看来,只怕是皇长子也早知此事,与姐姐无甚大关联……”
说着,田蚡便又是一阵摇头苦笑,旋即意味深长道:“怕是往日,我们,都看错皇长子了。”
“就此次的事来看,皇长子,绝非善类……”
许是有田蚡在身边,又说出了憋在心里的话,王娡也逐渐从惶恐不安的情绪中平静下来。
又闻田蚡此言,便深吸一口气,面色凝重道:“终归是皇长子,半个准储君。”
“若是连这点手段都没有,倒也省的我姐弟为之头疼了。”
“唉……”
“——若那贱婢还活着,我倒还能把人被陛下送去,以自证清白。”
“只如今死无对证,我便是有心自证,却也百口莫辩……”
随着王娡这满含愤闷的话语,姐弟二人便也就此沉默了下来。
显而易见:这次的事,王娡被刘荣打了个措手不及,甚至可以说是毫无还手之力。
事情闹到如今这个地步,也已经没有了继续纠缠下去的意义。
最明智的做法,就是将此事冷处理,打碎牙齿和血吞,吃下这个哑巴亏。
至于以后……
“馆陶公主那边,可搭上线了?”
沉思良久,王娡终轻声发出一问,却惹得田蚡一阵苦笑不止。
“倒是见了一面。”
“只是光见这一面,就贴进去不下千金的拜礼;”
“听话里话外的意思,要想谈成那件事,只怕是……”
听出田蚡话中埋怨,王娡也不由眼底一黯,悠悠道:“你长陵田氏,难道还缺这点黄白之物?”
“还是我儿彘,不值得你长陵田氏花些钱、金?”
便见田蚡嘿嘿一阵讪笑,又颇有些不自然的挠了挠头。
“瞧姐姐这话说的;”
“——我姐弟二人虽非同姓,却也终归是一個母亲所生。”
“彘儿大了,也总还是要唤我一声舅父的。”
“只是姐姐也知道,我田氏纵然家大业大,也终归不全是我这少主说了算。”
“动辄数千上万金的花销,若是换不来入项,我也没法给族人交代?”
说到最后,田蚡的语调之中,也已是隐约带上了些期翼。
对此,王娡自也不会装傻充楞。
只深吸一口气,又漠然望向殿门的方向,好似自言自语般,为田蚡给出了自己的承诺。
“商贾末业,终归不是正道。”
“指不定什么时候,便要被某家勋贵、某任丞相抄了宅院,毁了宗祠。”
“这几年,兄弟可得好好想想:等日后,要如何处置那硕大产业。”
“——再怎么说,堂堂国舅,本是可以入朝为官、封侯拜相的。”
“若仍自甘堕落,行商做贾,总归要惹人笑话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