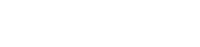三天时间很快过去,申屠嘉那封再三斟酌,反复推演,才终于得出的奏疏,也终于送上了天子启的案前。
结果不出刘荣所料:在拿到疏奏短短一个时辰之后,天子启便再度召见了申屠嘉。
这一次,君臣二人并没有再固执己见,而是深入浅出的交流了接下来,汉家一系列举措的相关细节和走向。
最终,申屠嘉低调回到了侯府,并没能让长安坊间,从自己身上看出任何端倪。
——这君臣二人聊了什么,结果如何,达成了什么默契,都没人知道。
唯独申屠嘉回府时,在申屠嘉身旁随行的宣诏侍中,让朝堂内外隐约有了猜测。
皇长子,应该是熬过这一关了……
·
还是那处‘书房’,或者应该说是凉亭。
仍旧是堆满亭内的如山竹简,以及那方简陋、古朴的案几。
也依旧是丞相申屠嘉,以及皇长子刘荣二人。
只是这一次,换做是刘荣负手而立,打量起亭外——打量起侯府上下。
只短短三日的功夫,刘荣对申屠嘉这位老丞相、老元勋的敬意,便陡然再增三五个台阶。
——就说此刻,刘荣目光所及,二人所身处的凉亭周围,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拿得出手的装饰。
除了用来装竹简的木箱、夜时供明的灯台,便是单纯被夯实的泥土地——莫说是石板,就连鹅卵石都没铺。
这个院子往里,是侯府后院,住着仅有的三五女眷;
与院子一墙之隔的正堂、正院,更好似小一号的相府,基本只供申屠嘉进行工作上的往来,压根儿就不能算作侯府的一部分。
至于最能体现权贵财力的仆人,刘荣更是自惭形秽。
在凤凰殿,单是刘荣自己,便有两个负责起居的宫人、两个负责衣物的婢女,以及三五随时待命的杂役寺人。
至于‘殿主’栗姬,那更是连庖厨带奴仆加侍女寺人,掌握着不下二十人的命运!
区区一個栗姬、一座凤凰殿,都养着三五十仆从,申屠嘉怎么说也是百官之首,总不至于太差;
但就刘荣亲眼所见,整座故安侯府上下,就一个门房,一个管家,一个厨娘,两个杂役。
就算加上后院女眷的贴身婢女、丫头,也绝不过十指之数。
在长安,别说是公卿这一级别了——凡官秩千石以上,恐怕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此节俭的人。
而申屠嘉对此做出的解释,却更让刘荣羞愧难当,为自己‘奢靡’的生活而感到害臊。
“公子应该知道,老臣早年,发于行伍之间……”
了却最大的一桩心事,虽然也自此背负了更重的担子,但申屠嘉的面容之上,却反而带上了一抹轻松。
对于刘荣,也没了先前那刻意至极的疏离,看出刘荣的疑惑,便也语带唏嘘的自顾自解释起来。
“一将功成万骨枯,一国鼎立百将殁。”
“世人都以为开国元勋,是杀了几个人、打了几场仗,就得以裂土而侯,泽及子孙的人。”
“却不知这骤然贵幸的元勋,是不知几千、几万人当中才能出一个,既立了武勋,又难得活到开国那一天的幸运儿……”
说着,申屠嘉语调中明明带着自嘲,眉宇间,却也应声涌上阵阵感伤。
“太祖高皇帝受封汉王之时,老臣累功至队率,麾下卒五百。”
“自汉元年,太祖高皇帝还定三秦,到汉五年,项羽自刎乌江;
——这短短五年时间里,我麾下五百悍卒,便战死不下三千……”
“嘿,好笑吧?”
“明明只有五百人,却先后有三千多大好儿郎,战死在随我冲锋陷阵的路上……”
三两句花的功夫,老丞相便是红了眼眶,面上笑意也愈发苦涩、更显刻意。
“战死的,太祖高皇帝都下令抚恤过,老臣也尽量登门,拜访了他们的亲长。”
“而伤残者,便只能仰仗我这故安侯国的五百户食邑,方得以苟延残喘,艰难度日……”
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官至丞相、贵为彻侯,却依旧过的如此清贫,申屠嘉便颤巍巍在案几前一侧躺。
许是年岁已高,脊背不再那般灵活,觉得侧躺太费力,更索性翻身平躺下来。
长呼一口气,再稍一侧头,对刘荣咧嘴一笑。
“陛下,答应了。”
“陛下答应在开春时,给匈奴人送去国书,以求和亲。”
“待匈奴使团入朝,再伺机联络长安侯、韩王信的后人,打探匈奴人的情况。”
“我也答应了陛下:只要能确定军臣打算对右贤王动手,便不再为边墙感到担忧,全力帮助陛下削藩,并应对削藩所引发的一切后果……”
说着说着,申屠嘉的话语声便低了下去,看向刘荣的目光,也愈发深邃起来。
感受到申屠嘉的异样目光,刘荣纵然心虚,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;
养了三天,后腰、后股虽然才结痂,却也已是能勉强行走自如,便呵笑着走到亭柱旁,将肩侧轻倚在柱上。
“这不是好事吗?”
“故安侯得偿所愿,父皇也不用再为‘如何劝说丞相这头老倔牛’而感到苦恼;”
“君臣相得,通力协作,待日后刘濞起兵,朝堂也能众志成城……”
“——为什么?”
却见申屠嘉冷不丁一开口,便不顾刘荣呆愕的目光,重新在案几前坐起了身。
“自那日,公子告诉老臣:军臣必定会对右贤王动手,老臣,便没再头疼匈奴人的事了。”
“唯独一点,老臣百般思虑,也终不得其解。”
“——为什么?”
“公子,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,先在宫门内邀我同行,后又告诉我这件事呢?”
·
“既然知道匈奴人不会帮刘濞,那公子应该是原本就不担心陛下削藩,会导致宗庙、社稷陷入危难吧?”
“有如此把握,公子明明更应该作壁上观,坐等吴楚平灭;”
“又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,也要将那个连来源都不方便说的消息,告诉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呢?”
“我何德何能,值得公子冒如此巨大的风险……”
听出申屠嘉话语中的深意,刘荣只本能愣在原地,似是为申屠嘉能想到这方面而感到惊奇。
只片刻之后,便又释然一笑。
——申屠嘉,只是倔;
但作为汉家的丞相,申屠嘉,绝对不傻。
不收受贿赂、不蝇营狗苟,绝不意味着这位老丞相,看不明白其中的门道;
不屑于与人往来,也绝不意味着这位功勋卓著的老臣,会看不出旁人的意图。
刘荣心知:自己有无数种说辞,可以将申屠嘉的这一问搪塞过去。
但最终,刘荣还是选择坦然面对。
“确实如故安侯所言:我最明智的选择,其实是什么都不做。”
“——因为我知道匈奴人,绝不会发兵南下,帮助刘濞;”
“——也知道梁王叔这个‘储君皇太弟’的美梦,必定会和刘濞‘位及九五’的美梦一同醒来。”
“如果要明哲保身,我原本不需要做这些,只需要配合父皇演好戏,在父皇那里做个恭顺、懂事的皇长子,便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”
“但最终,我还是选择冒险出手。”
“故安侯老臣谋国,当真看不明白我的意图?”
刘荣此言一出,申屠嘉面上笑容依旧,言辞却立时带上了早先,将刘荣拒于千里之外的那股子疏离。
“老臣,是绝对不会帮助公子的。”
“无论是公子还是旁人,凡是关乎储位的事,老臣便断然不会插手。”
却见刘荣闻言,只洒然一笑,深深凝望向申屠嘉目光深处;
良久过后,便含笑转身,朝着府门的方向而去,只留给申屠嘉一个潇洒的背影。
“将来的太子储君,或许不需要老丞相申屠嘉~”
“但眼下,我汉家需要故安侯。”
“某个自认为‘一切尽在掌控’的黄毛小子,也舍不得鞠躬尽瘁的老丞相,死在阴险狡诈之辈手中……”
·
“故安侯保重啊~”
“下次再见时,公子荣,当也不再只是公子荣啦……”
结果不出刘荣所料:在拿到疏奏短短一个时辰之后,天子启便再度召见了申屠嘉。
这一次,君臣二人并没有再固执己见,而是深入浅出的交流了接下来,汉家一系列举措的相关细节和走向。
最终,申屠嘉低调回到了侯府,并没能让长安坊间,从自己身上看出任何端倪。
——这君臣二人聊了什么,结果如何,达成了什么默契,都没人知道。
唯独申屠嘉回府时,在申屠嘉身旁随行的宣诏侍中,让朝堂内外隐约有了猜测。
皇长子,应该是熬过这一关了……
·
还是那处‘书房’,或者应该说是凉亭。
仍旧是堆满亭内的如山竹简,以及那方简陋、古朴的案几。
也依旧是丞相申屠嘉,以及皇长子刘荣二人。
只是这一次,换做是刘荣负手而立,打量起亭外——打量起侯府上下。
只短短三日的功夫,刘荣对申屠嘉这位老丞相、老元勋的敬意,便陡然再增三五个台阶。
——就说此刻,刘荣目光所及,二人所身处的凉亭周围,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拿得出手的装饰。
除了用来装竹简的木箱、夜时供明的灯台,便是单纯被夯实的泥土地——莫说是石板,就连鹅卵石都没铺。
这个院子往里,是侯府后院,住着仅有的三五女眷;
与院子一墙之隔的正堂、正院,更好似小一号的相府,基本只供申屠嘉进行工作上的往来,压根儿就不能算作侯府的一部分。
至于最能体现权贵财力的仆人,刘荣更是自惭形秽。
在凤凰殿,单是刘荣自己,便有两个负责起居的宫人、两个负责衣物的婢女,以及三五随时待命的杂役寺人。
至于‘殿主’栗姬,那更是连庖厨带奴仆加侍女寺人,掌握着不下二十人的命运!
区区一個栗姬、一座凤凰殿,都养着三五十仆从,申屠嘉怎么说也是百官之首,总不至于太差;
但就刘荣亲眼所见,整座故安侯府上下,就一个门房,一个管家,一个厨娘,两个杂役。
就算加上后院女眷的贴身婢女、丫头,也绝不过十指之数。
在长安,别说是公卿这一级别了——凡官秩千石以上,恐怕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如此节俭的人。
而申屠嘉对此做出的解释,却更让刘荣羞愧难当,为自己‘奢靡’的生活而感到害臊。
“公子应该知道,老臣早年,发于行伍之间……”
了却最大的一桩心事,虽然也自此背负了更重的担子,但申屠嘉的面容之上,却反而带上了一抹轻松。
对于刘荣,也没了先前那刻意至极的疏离,看出刘荣的疑惑,便也语带唏嘘的自顾自解释起来。
“一将功成万骨枯,一国鼎立百将殁。”
“世人都以为开国元勋,是杀了几个人、打了几场仗,就得以裂土而侯,泽及子孙的人。”
“却不知这骤然贵幸的元勋,是不知几千、几万人当中才能出一个,既立了武勋,又难得活到开国那一天的幸运儿……”
说着,申屠嘉语调中明明带着自嘲,眉宇间,却也应声涌上阵阵感伤。
“太祖高皇帝受封汉王之时,老臣累功至队率,麾下卒五百。”
“自汉元年,太祖高皇帝还定三秦,到汉五年,项羽自刎乌江;
——这短短五年时间里,我麾下五百悍卒,便战死不下三千……”
“嘿,好笑吧?”
“明明只有五百人,却先后有三千多大好儿郎,战死在随我冲锋陷阵的路上……”
三两句花的功夫,老丞相便是红了眼眶,面上笑意也愈发苦涩、更显刻意。
“战死的,太祖高皇帝都下令抚恤过,老臣也尽量登门,拜访了他们的亲长。”
“而伤残者,便只能仰仗我这故安侯国的五百户食邑,方得以苟延残喘,艰难度日……”
解释过自己为什么官至丞相、贵为彻侯,却依旧过的如此清贫,申屠嘉便颤巍巍在案几前一侧躺。
许是年岁已高,脊背不再那般灵活,觉得侧躺太费力,更索性翻身平躺下来。
长呼一口气,再稍一侧头,对刘荣咧嘴一笑。
“陛下,答应了。”
“陛下答应在开春时,给匈奴人送去国书,以求和亲。”
“待匈奴使团入朝,再伺机联络长安侯、韩王信的后人,打探匈奴人的情况。”
“我也答应了陛下:只要能确定军臣打算对右贤王动手,便不再为边墙感到担忧,全力帮助陛下削藩,并应对削藩所引发的一切后果……”
说着说着,申屠嘉的话语声便低了下去,看向刘荣的目光,也愈发深邃起来。
感受到申屠嘉的异样目光,刘荣纵然心虚,也不得不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;
养了三天,后腰、后股虽然才结痂,却也已是能勉强行走自如,便呵笑着走到亭柱旁,将肩侧轻倚在柱上。
“这不是好事吗?”
“故安侯得偿所愿,父皇也不用再为‘如何劝说丞相这头老倔牛’而感到苦恼;”
“君臣相得,通力协作,待日后刘濞起兵,朝堂也能众志成城……”
“——为什么?”
却见申屠嘉冷不丁一开口,便不顾刘荣呆愕的目光,重新在案几前坐起了身。
“自那日,公子告诉老臣:军臣必定会对右贤王动手,老臣,便没再头疼匈奴人的事了。”
“唯独一点,老臣百般思虑,也终不得其解。”
“——为什么?”
“公子,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,先在宫门内邀我同行,后又告诉我这件事呢?”
·
“既然知道匈奴人不会帮刘濞,那公子应该是原本就不担心陛下削藩,会导致宗庙、社稷陷入危难吧?”
“有如此把握,公子明明更应该作壁上观,坐等吴楚平灭;”
“又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,也要将那个连来源都不方便说的消息,告诉我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呢?”
“我何德何能,值得公子冒如此巨大的风险……”
听出申屠嘉话语中的深意,刘荣只本能愣在原地,似是为申屠嘉能想到这方面而感到惊奇。
只片刻之后,便又释然一笑。
——申屠嘉,只是倔;
但作为汉家的丞相,申屠嘉,绝对不傻。
不收受贿赂、不蝇营狗苟,绝不意味着这位老丞相,看不明白其中的门道;
不屑于与人往来,也绝不意味着这位功勋卓著的老臣,会看不出旁人的意图。
刘荣心知:自己有无数种说辞,可以将申屠嘉的这一问搪塞过去。
但最终,刘荣还是选择坦然面对。
“确实如故安侯所言:我最明智的选择,其实是什么都不做。”
“——因为我知道匈奴人,绝不会发兵南下,帮助刘濞;”
“——也知道梁王叔这个‘储君皇太弟’的美梦,必定会和刘濞‘位及九五’的美梦一同醒来。”
“如果要明哲保身,我原本不需要做这些,只需要配合父皇演好戏,在父皇那里做个恭顺、懂事的皇长子,便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。”
“但最终,我还是选择冒险出手。”
“故安侯老臣谋国,当真看不明白我的意图?”
刘荣此言一出,申屠嘉面上笑容依旧,言辞却立时带上了早先,将刘荣拒于千里之外的那股子疏离。
“老臣,是绝对不会帮助公子的。”
“无论是公子还是旁人,凡是关乎储位的事,老臣便断然不会插手。”
却见刘荣闻言,只洒然一笑,深深凝望向申屠嘉目光深处;
良久过后,便含笑转身,朝着府门的方向而去,只留给申屠嘉一个潇洒的背影。
“将来的太子储君,或许不需要老丞相申屠嘉~”
“但眼下,我汉家需要故安侯。”
“某个自认为‘一切尽在掌控’的黄毛小子,也舍不得鞠躬尽瘁的老丞相,死在阴险狡诈之辈手中……”
·
“故安侯保重啊~”
“下次再见时,公子荣,当也不再只是公子荣啦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