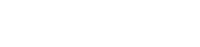随着刘荣话音落下,原本还能听到木块碰撞声的牌桌之上,只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老二刘德含笑看着大哥刘荣,面带赞同的点了点头。
老三刘淤不知是输得太多,还是仍旧不能将四弟刘余当自己人,望向刘余的目光中,隐约带着一丝审视。
而老四刘余,则是在刘荣诚恳的目光注视下,面色阴晴变幻许久,才终洒然一笑。
“是……”
“凡世、世间事,多、多难、两全;”
“鱼、鱼与熊、熊掌、不、不可兼、兼得。”
“总要有、有个、抉择,取、取舍……”
言罢,刘余又似是下定决心般,含笑一点头,将面前的牌往前一推。
最普通不过的屁胡,也算是表明了刘余,以及刘余背后,众皇子兄弟的立场:大哥吃肉,老二老三啃骨头,我们兄弟几个,喝点儿汤就行。
体会到刘余这层深意,刘荣只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,深深凝视向刘余目光深处。
良久,方索然无味般长叹口气,从牌桌前起身。
“今天,就到这里吧。”
“该忙正事儿喽~”
嘴上说着,刘荣手上,也将那足有拳头大小的布袋拿起,不轻不重的放在刘余身前。
“先帝崇倡简朴之风,兄弟们的日子,怕也松快不到哪儿去。”
“老五历来尚武,又整日里嚷嚷着,没有趁手的强弓。”
“——拿这些钱去少府,给老五打一把好弓。”
·
“哦,对了;”
“老二啊……”
一声招呼,老二刘德应声而起,见刘荣朝自己微一点头,便折身而去,不多时又带着几卷竹简而来。
便见刘荣接过竹简,旋即如数家珍般,一卷一卷递到刘余手中。
“卜家说,相面之术,分相地、相人、相兽。”
“平日里听老二说,老四喜犬类?”
“喏,这卷《相狗经》,当是能供老四闲时解闷了。”
“——不过鸡犬之类,终非正道。”
“老四用于怡情尚可,断不可沉迷此道。”
刘荣话音未落,刘余那本还带着些许局促的面容,只陡然间绽放出一阵狂喜!
刚要开口表达谢意,却见刘荣好似一位正在整理书籍的文吏般,低头再抓起一卷竹简。
“老六怕生,不怎么与人交谈,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”
“碰巧得了卷《秦廷秘闻》的残卷,权当是话本看看得了。”
这一下,不单是刘余面色剧变,便是一旁的老三刘淤,都有些按捺不住伸手讨要的冲动了。
《秦廷秘闻》,并非是什么名家所著,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,又有多少是真的;
但对于困居深宫,理论上没有机会走出宫墙的众皇子、姬嫔而言,这种不知来由,且讲述前朝宫廷秘闻的类小说,不说有价无市,也起码是可遇不可求。
在刘余满是感激、刘淤略带幽怨的目光注视下,刘荣又将最后两卷竹简一股脑塞进刘余怀里。
“老七好辩论,这卷残卷也不知出自何处,讲的是那场关于‘白马非马’的名辩。”
“至于老九……”
话说一半,刘荣只略带些害臊的摸了摸鼻尖,朝刘余怀中,那最后一卷竹简一昂首。
“咳咳,九岁多啦,不小啦……”
“稍微了解了解男女之事……咳咳咳……”
此言一出,刘余当即心下了然,望向刘荣的目光中,也不由带上了些许复杂。
只是这抹复杂,仅仅是出于刘余对弟弟的关切,以及对心目中,大哥刘荣伟岸形象崩塌的茫然。
——做大哥的,给小弟搞黄书?
多少有些冒昧了吧?
但换个角度说,这虽然不像皇长子会干的事,倒也很符合做大哥的……
“就先这样吧,若是想玩儿,你们留下玩儿就是。”
“我得去趟宣室。”
“——丞相入宫觐见,可是已经有好几个时辰喽~”
“若不去一趟,都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儿……”
语带慵懒的说着,刘荣甚至还不顾形象的伸了个大懒腰,才整理了一下身上衣衫,朝着宣室殿的方向走去。
而在牌桌前,望着大哥离去的背影,皇四子刘余抱着怀中竹简的手紧了紧,嘴角之上,也悄然翘起一抹浅浅的弧度……
·
·
·
未央宫,宣室殿。
除了天子启、丞相申屠嘉,整座宣室殿内,便再也不见第三道身影。
御榻之上,天子启满是疲惫的揉着额头,却还是压不下突突直跳的太阳穴;
而在殿中央,丞相申屠嘉拱手跪地,面上神情满是哀戚。
很显然,君臣二人之间的坦诚交流,并没能取得什么积极地成果。
不知沉默多久,终还是天子启将手从额角放下,又极尽疲惫的长呼出一口浊气。
“丞相,怎么就不明白呢?”
“——吴王刘濞,是必定会反的啊?”
“——是必定会为王太子报仇的啊!!”
“杀死王太子的仇人,此刻正端坐在未央宫宣室正殿的御榻之上!!!”
“他吴王刘濞,怎么可能不暴起篡逆?!”
·
“偏那吴王刘濞,是父皇入继大统之后一手扶持,又是许其卤海得盐,又是允其开山得铜、铸铜为钱的强藩!”
“其国富,其民众,其兵强!!!”
“这般关乎宗庙、社稷的大事,朕不先下手为强,难道还要等他吴王刘濞叩关函谷,方后发制人吗?”
好话坏话都说了個遍,天子启已然是口干舌燥,只烦躁的咽了咽不存在的唾沫。
只是申屠嘉仍旧是那副跪地拱手,满目哀创的神态,似是仍在祈求天子启。
“正是因为关乎宗庙、社稷,陛下,才不得不慎之又慎呐……”
“若是有万全准备,都不需要陛下筹谋布局,老臣便会一马当先,力主推行《削藩策》。”
“但如今的汉家,还万万承受不起一场波及大半,乃至整个关东的诸侯叛乱呐……”
这,便是说到了天子启和申屠嘉的第二个分歧。
第一个分歧,是天子启觉得先下手为强,后下手遭殃,申屠嘉却觉得谋定而后动,应该后发制人;
而这第二个分歧,便是天子启认为《削藩策》推行之后,基本只有吴王刘濞是铁定会反的,其他藩王则大都会观望。
只是作为丞相——作为汉家社稷实际上的管理者,申屠嘉更为深切的知道:齐系、淮南系诸王,究竟怀揣着怎样的心思;自太祖高皇帝以来,便愈发不受长安监管掌控的关东,又烂到了怎样骇人的程度……
老二刘德含笑看着大哥刘荣,面带赞同的点了点头。
老三刘淤不知是输得太多,还是仍旧不能将四弟刘余当自己人,望向刘余的目光中,隐约带着一丝审视。
而老四刘余,则是在刘荣诚恳的目光注视下,面色阴晴变幻许久,才终洒然一笑。
“是……”
“凡世、世间事,多、多难、两全;”
“鱼、鱼与熊、熊掌、不、不可兼、兼得。”
“总要有、有个、抉择,取、取舍……”
言罢,刘余又似是下定决心般,含笑一点头,将面前的牌往前一推。
最普通不过的屁胡,也算是表明了刘余,以及刘余背后,众皇子兄弟的立场:大哥吃肉,老二老三啃骨头,我们兄弟几个,喝点儿汤就行。
体会到刘余这层深意,刘荣只带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,深深凝视向刘余目光深处。
良久,方索然无味般长叹口气,从牌桌前起身。
“今天,就到这里吧。”
“该忙正事儿喽~”
嘴上说着,刘荣手上,也将那足有拳头大小的布袋拿起,不轻不重的放在刘余身前。
“先帝崇倡简朴之风,兄弟们的日子,怕也松快不到哪儿去。”
“老五历来尚武,又整日里嚷嚷着,没有趁手的强弓。”
“——拿这些钱去少府,给老五打一把好弓。”
·
“哦,对了;”
“老二啊……”
一声招呼,老二刘德应声而起,见刘荣朝自己微一点头,便折身而去,不多时又带着几卷竹简而来。
便见刘荣接过竹简,旋即如数家珍般,一卷一卷递到刘余手中。
“卜家说,相面之术,分相地、相人、相兽。”
“平日里听老二说,老四喜犬类?”
“喏,这卷《相狗经》,当是能供老四闲时解闷了。”
“——不过鸡犬之类,终非正道。”
“老四用于怡情尚可,断不可沉迷此道。”
刘荣话音未落,刘余那本还带着些许局促的面容,只陡然间绽放出一阵狂喜!
刚要开口表达谢意,却见刘荣好似一位正在整理书籍的文吏般,低头再抓起一卷竹简。
“老六怕生,不怎么与人交谈,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。”
“碰巧得了卷《秦廷秘闻》的残卷,权当是话本看看得了。”
这一下,不单是刘余面色剧变,便是一旁的老三刘淤,都有些按捺不住伸手讨要的冲动了。
《秦廷秘闻》,并非是什么名家所著,甚至压根儿就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,又有多少是真的;
但对于困居深宫,理论上没有机会走出宫墙的众皇子、姬嫔而言,这种不知来由,且讲述前朝宫廷秘闻的类小说,不说有价无市,也起码是可遇不可求。
在刘余满是感激、刘淤略带幽怨的目光注视下,刘荣又将最后两卷竹简一股脑塞进刘余怀里。
“老七好辩论,这卷残卷也不知出自何处,讲的是那场关于‘白马非马’的名辩。”
“至于老九……”
话说一半,刘荣只略带些害臊的摸了摸鼻尖,朝刘余怀中,那最后一卷竹简一昂首。
“咳咳,九岁多啦,不小啦……”
“稍微了解了解男女之事……咳咳咳……”
此言一出,刘余当即心下了然,望向刘荣的目光中,也不由带上了些许复杂。
只是这抹复杂,仅仅是出于刘余对弟弟的关切,以及对心目中,大哥刘荣伟岸形象崩塌的茫然。
——做大哥的,给小弟搞黄书?
多少有些冒昧了吧?
但换个角度说,这虽然不像皇长子会干的事,倒也很符合做大哥的……
“就先这样吧,若是想玩儿,你们留下玩儿就是。”
“我得去趟宣室。”
“——丞相入宫觐见,可是已经有好几个时辰喽~”
“若不去一趟,都不知道要闹成什么样儿……”
语带慵懒的说着,刘荣甚至还不顾形象的伸了个大懒腰,才整理了一下身上衣衫,朝着宣室殿的方向走去。
而在牌桌前,望着大哥离去的背影,皇四子刘余抱着怀中竹简的手紧了紧,嘴角之上,也悄然翘起一抹浅浅的弧度……
·
·
·
未央宫,宣室殿。
除了天子启、丞相申屠嘉,整座宣室殿内,便再也不见第三道身影。
御榻之上,天子启满是疲惫的揉着额头,却还是压不下突突直跳的太阳穴;
而在殿中央,丞相申屠嘉拱手跪地,面上神情满是哀戚。
很显然,君臣二人之间的坦诚交流,并没能取得什么积极地成果。
不知沉默多久,终还是天子启将手从额角放下,又极尽疲惫的长呼出一口浊气。
“丞相,怎么就不明白呢?”
“——吴王刘濞,是必定会反的啊?”
“——是必定会为王太子报仇的啊!!”
“杀死王太子的仇人,此刻正端坐在未央宫宣室正殿的御榻之上!!!”
“他吴王刘濞,怎么可能不暴起篡逆?!”
·
“偏那吴王刘濞,是父皇入继大统之后一手扶持,又是许其卤海得盐,又是允其开山得铜、铸铜为钱的强藩!”
“其国富,其民众,其兵强!!!”
“这般关乎宗庙、社稷的大事,朕不先下手为强,难道还要等他吴王刘濞叩关函谷,方后发制人吗?”
好话坏话都说了個遍,天子启已然是口干舌燥,只烦躁的咽了咽不存在的唾沫。
只是申屠嘉仍旧是那副跪地拱手,满目哀创的神态,似是仍在祈求天子启。
“正是因为关乎宗庙、社稷,陛下,才不得不慎之又慎呐……”
“若是有万全准备,都不需要陛下筹谋布局,老臣便会一马当先,力主推行《削藩策》。”
“但如今的汉家,还万万承受不起一场波及大半,乃至整个关东的诸侯叛乱呐……”
这,便是说到了天子启和申屠嘉的第二个分歧。
第一个分歧,是天子启觉得先下手为强,后下手遭殃,申屠嘉却觉得谋定而后动,应该后发制人;
而这第二个分歧,便是天子启认为《削藩策》推行之后,基本只有吴王刘濞是铁定会反的,其他藩王则大都会观望。
只是作为丞相——作为汉家社稷实际上的管理者,申屠嘉更为深切的知道:齐系、淮南系诸王,究竟怀揣着怎样的心思;自太祖高皇帝以来,便愈发不受长安监管掌控的关东,又烂到了怎样骇人的程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