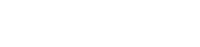在这一点上,刘荣倒是误会梁王刘武了。
此刻,梁王刘武非但没有在‘等’着刘荣兄弟三人的动作,甚至还在因刚得知的消息,而感到惊骇不已。
“储君?!”
“——皇太弟?!!”
下意识一声惊呼出口,刘武这才意识到不对,赶忙噤声,旋即面色阴冷的望向一旁。
待身旁文吏赶忙走到室外,在周遭打量一圈,又回身朝刘武摇摇头,刘武方心下稍安。
眼神示意文士不必回到室内,又看了看身边;
确定只有自己和身侧的姐姐刘嫖,刘武这才满脸凝重的压低声线:“阿姊说的什么胡话!”
“这莫不是要我这个做弟弟的,去抢皇帝兄长的大位?”
“如此大逆不道的事,别说我做了,将来怎么面见先帝,便是活着,我又该怎么面对如君如父的兄长,以及天下人悠悠众口呢?”
“——阿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,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”
“只是这样的话,阿姊以后可莫再提了。”
“如果皇兄知道阿姊有这样的念头,恐怕也会很难过、很心寒的。”
言罢,梁王刘武当即绷着脸,端起茶碗,愣是一个眼神都没再给姐姐刘嫖。
虽然这个时代还没有‘端茶送客’的说法,但刘武那明写在脸上的不愉,也已然是最直白不过的‘好走不送’之意。
对于弟弟刘武这般反应,刘嫖却好似早有所料。
只忍俊不禁的笑着摇摇头:“瞧把你吓得……”
“我何曾说要梁王,去抢阿启的大位了?”
“——储君皇太弟,可还得皇帝点头答应,配合着母后颁下册立诏书呢。”
“这怎能算抢?”
这一下,刘武算是彻底糊涂了。
什么玩意儿?
皇帝哥哥又不是没儿子,便是脑袋被宣室殿那千斤重门挤了,也不至于放着儿子不管,反而立弟弟为储君?
天子启必定不会这么做,刘嫖又非得怂恿刘武去做储君皇太弟,这不就是抢大位吗?
这般骇人听闻的说辞,也亏刘嫖想得出来。
“我看这些年,阿姊是被先帝和皇兄,宠的都有些找不着北了。”
“——储君之位,也是阿姊能觊觎、盘算的?”
“莫说皇兄断不会答应,便是答应,我又哪来的胆子,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?”
说着,刘武便再度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作态,好似刘嫖再继续说,就真的要生自己姐姐的气了。
但早就对此有所预料,甚至有所准备的刘嫖,又怎会如此轻易的退缩?
喜色不减的又笑了笑,方故作神秘的、叹息着摇了摇头。
“唉~”
“阿武这脑子,可真是累苦了我这做姐姐的……”
“说得好像我这么做,是为了我自己似的?”
这话一出,梁王刘武面上,只更添一分疑惑。
是啊!
图个什么?!
明明自己有个皇帝弟弟,却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,让自己的另一個弟弟做皇储;
刘嫖,到底图个什么?
未有所图,刘武是绝对不信的。
自家人知道自家事——对于自己家这几口子,梁王刘武还是有着基本的认知。
——先帝刘恒,舍小家为大家,一切以天下为重;
为了天下人,刘恒愿意牺牲自己除宗庙、社稷之外,所拥有的一切。
——当朝窦太后,大多数时候都识大体、顾大局,偶尔会钻牛角尖,但也总还听劝;
只是随着眼疾愈发严重,老太后也随之愈发敏感起来,变得气量极小、极度记仇,也更难以被劝说。
——当今天子启,心机深沉,手段狠辣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!
不动则已,一动,便必定是早已万事俱备,且已然等来了自己需要的‘东风’。
而此刻,正劝说刘武拼上一把,去争一争那储君太子之位的馆陶长公主刘嫖,如果有什么人物标签,那便必定是一句:无利不起早。
长安城谁人不知:办事找馆陶,稳妥且可靠?
但凡收了钱,这位长公主不管事儿能不能办成,起码人家实打实会去办!
力所能及的争取,即便实在没办成,也会规规矩矩把钱退回去不说,还会多加一两成作为赔礼,或者说陪葬。
嗯,在如今汉家,若是连馆陶公主都平不了的事儿,大抵也只能到阎王面前说说情了。
平日里,若是有人提起自家姐姐贪婪、好财、无利不起早,梁王刘武自是会‘据理力争’,甚至不惜仗势欺人,也要保全姐姐的声誉。
但不说归不说,却并不意味着在梁王刘武心中,刘嫖这个姐姐,真的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。
——刘武很清楚:姐姐刘嫖,压根儿就是淤泥本泥!
所以此刻,刘武不再疑惑于‘刘嫖怎么敢的’,而是不解刘嫖这么做,究竟是有何图谋。
想不出个所以然,自然便将审视的目光,撒向刘嫖那写满精明的面庞。
也正是这个举动,让梁王刘武跳进了刘嫖为自己量身定做,但凡换一个人,都绝不可能跳下去的私人订制版陷阱。
“我今日来,是受母后所托~”
“若不是母后有令,我才不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!”
“瞧我这弟弟,都把我当什么人了?”
嘴上说着,刘嫖面上不忘做出一个十分受伤,甚至为自己感到不值的凄苦表情。
任谁见了刘嫖这做作之态,恐怕都不会被诓了去;
偏偏刘武这个不讳世事,又不识人间险恶的浪漫主义者,被刘嫖这表情彻底诓了进去。
“母后说了:阿启要削藩,吴王那老贼,无论如何都是会反的。”
“偏偏这吴王老贼,是当年先帝从代地入继大统之后,一手扶持出来的强藩,只要没明着造反,朝堂就绝不能先动手。”
“所以,阿启只能以削藩之名逼反吴王老贼,而后再一举除之,以一劳永逸,绝了我汉家的祸患。”
·
“吴王老贼奸诈,必也明白仅凭自己,绝无可能成事。”
“母后估摸着,齐系、淮南系诸王,恐怕大都会和吴王搭上关系,就算不会全反,也绝不可能都忠于我汉家。”
“真到了那时,我汉家能依仗着,除了阿武又有何人?”
听闻刘嫖这番话,准确的说,是听闻刘嫖第一句话,刘武便下意识将身子坐直了些,面上神容也立时严肃了起来。
——这件事,如果是刘嫖的主意,刘武只会当个笑话听;
但倘若是母亲窦太后的意思,那刘武就不会这么想了。
至少要听一听;
听一听母亲这么做,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考量。
此刻,梁王刘武非但没有在‘等’着刘荣兄弟三人的动作,甚至还在因刚得知的消息,而感到惊骇不已。
“储君?!”
“——皇太弟?!!”
下意识一声惊呼出口,刘武这才意识到不对,赶忙噤声,旋即面色阴冷的望向一旁。
待身旁文吏赶忙走到室外,在周遭打量一圈,又回身朝刘武摇摇头,刘武方心下稍安。
眼神示意文士不必回到室内,又看了看身边;
确定只有自己和身侧的姐姐刘嫖,刘武这才满脸凝重的压低声线:“阿姊说的什么胡话!”
“这莫不是要我这个做弟弟的,去抢皇帝兄长的大位?”
“如此大逆不道的事,别说我做了,将来怎么面见先帝,便是活着,我又该怎么面对如君如父的兄长,以及天下人悠悠众口呢?”
“——阿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,我实在是想不明白。”
“只是这样的话,阿姊以后可莫再提了。”
“如果皇兄知道阿姊有这样的念头,恐怕也会很难过、很心寒的。”
言罢,梁王刘武当即绷着脸,端起茶碗,愣是一个眼神都没再给姐姐刘嫖。
虽然这个时代还没有‘端茶送客’的说法,但刘武那明写在脸上的不愉,也已然是最直白不过的‘好走不送’之意。
对于弟弟刘武这般反应,刘嫖却好似早有所料。
只忍俊不禁的笑着摇摇头:“瞧把你吓得……”
“我何曾说要梁王,去抢阿启的大位了?”
“——储君皇太弟,可还得皇帝点头答应,配合着母后颁下册立诏书呢。”
“这怎能算抢?”
这一下,刘武算是彻底糊涂了。
什么玩意儿?
皇帝哥哥又不是没儿子,便是脑袋被宣室殿那千斤重门挤了,也不至于放着儿子不管,反而立弟弟为储君?
天子启必定不会这么做,刘嫖又非得怂恿刘武去做储君皇太弟,这不就是抢大位吗?
这般骇人听闻的说辞,也亏刘嫖想得出来。
“我看这些年,阿姊是被先帝和皇兄,宠的都有些找不着北了。”
“——储君之位,也是阿姊能觊觎、盘算的?”
“莫说皇兄断不会答应,便是答应,我又哪来的胆子,敢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?”
说着,刘武便再度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作态,好似刘嫖再继续说,就真的要生自己姐姐的气了。
但早就对此有所预料,甚至有所准备的刘嫖,又怎会如此轻易的退缩?
喜色不减的又笑了笑,方故作神秘的、叹息着摇了摇头。
“唉~”
“阿武这脑子,可真是累苦了我这做姐姐的……”
“说得好像我这么做,是为了我自己似的?”
这话一出,梁王刘武面上,只更添一分疑惑。
是啊!
图个什么?!
明明自己有个皇帝弟弟,却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,让自己的另一個弟弟做皇储;
刘嫖,到底图个什么?
未有所图,刘武是绝对不信的。
自家人知道自家事——对于自己家这几口子,梁王刘武还是有着基本的认知。
——先帝刘恒,舍小家为大家,一切以天下为重;
为了天下人,刘恒愿意牺牲自己除宗庙、社稷之外,所拥有的一切。
——当朝窦太后,大多数时候都识大体、顾大局,偶尔会钻牛角尖,但也总还听劝;
只是随着眼疾愈发严重,老太后也随之愈发敏感起来,变得气量极小、极度记仇,也更难以被劝说。
——当今天子启,心机深沉,手段狠辣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!
不动则已,一动,便必定是早已万事俱备,且已然等来了自己需要的‘东风’。
而此刻,正劝说刘武拼上一把,去争一争那储君太子之位的馆陶长公主刘嫖,如果有什么人物标签,那便必定是一句:无利不起早。
长安城谁人不知:办事找馆陶,稳妥且可靠?
但凡收了钱,这位长公主不管事儿能不能办成,起码人家实打实会去办!
力所能及的争取,即便实在没办成,也会规规矩矩把钱退回去不说,还会多加一两成作为赔礼,或者说陪葬。
嗯,在如今汉家,若是连馆陶公主都平不了的事儿,大抵也只能到阎王面前说说情了。
平日里,若是有人提起自家姐姐贪婪、好财、无利不起早,梁王刘武自是会‘据理力争’,甚至不惜仗势欺人,也要保全姐姐的声誉。
但不说归不说,却并不意味着在梁王刘武心中,刘嫖这个姐姐,真的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。
——刘武很清楚:姐姐刘嫖,压根儿就是淤泥本泥!
所以此刻,刘武不再疑惑于‘刘嫖怎么敢的’,而是不解刘嫖这么做,究竟是有何图谋。
想不出个所以然,自然便将审视的目光,撒向刘嫖那写满精明的面庞。
也正是这个举动,让梁王刘武跳进了刘嫖为自己量身定做,但凡换一个人,都绝不可能跳下去的私人订制版陷阱。
“我今日来,是受母后所托~”
“若不是母后有令,我才不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呢!”
“瞧我这弟弟,都把我当什么人了?”
嘴上说着,刘嫖面上不忘做出一个十分受伤,甚至为自己感到不值的凄苦表情。
任谁见了刘嫖这做作之态,恐怕都不会被诓了去;
偏偏刘武这个不讳世事,又不识人间险恶的浪漫主义者,被刘嫖这表情彻底诓了进去。
“母后说了:阿启要削藩,吴王那老贼,无论如何都是会反的。”
“偏偏这吴王老贼,是当年先帝从代地入继大统之后,一手扶持出来的强藩,只要没明着造反,朝堂就绝不能先动手。”
“所以,阿启只能以削藩之名逼反吴王老贼,而后再一举除之,以一劳永逸,绝了我汉家的祸患。”
·
“吴王老贼奸诈,必也明白仅凭自己,绝无可能成事。”
“母后估摸着,齐系、淮南系诸王,恐怕大都会和吴王搭上关系,就算不会全反,也绝不可能都忠于我汉家。”
“真到了那时,我汉家能依仗着,除了阿武又有何人?”
听闻刘嫖这番话,准确的说,是听闻刘嫖第一句话,刘武便下意识将身子坐直了些,面上神容也立时严肃了起来。
——这件事,如果是刘嫖的主意,刘武只会当个笑话听;
但倘若是母亲窦太后的意思,那刘武就不会这么想了。
至少要听一听;
听一听母亲这么做,背后有什么更深层次的考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