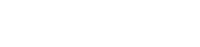“特勤,这是为何啊?”
老者大惊失色。
摄图平静的看了他一眼,“我打不过。”
老者赶忙说道:“特勒岂能不战而退呢?都不曾交战,怎么就知打不过?我当特勒是天下闻名的勇士,各部敬畏,不知竟是如此怯弱,只听闻敌人出兵,就想要逃离,可悲,可叹,想那伊利可汗何等的英雄,竟有这般的儿子!”
“老夫当真是看错了人.齐人孱弱,特勒竟还不如这些齐人!!”
听到对方的话,摄图笑了起来,“既是这般孱弱,你们怎么不打?”
老者一顿。
“想那当初的宇文可汗是何等的英雄,怎么他会有这样的部下?看着齐人从身边经过,却不敢发兵,莫不是想要借他们之手来收拾自家盟友?”
老者赶忙摇头,“特勒,岂敢,岂敢.”
他急忙改变了口吻,“您如今要是撤离,您这部下极多,只怕是没走出多久,就会被齐人追上,到时候,您就再也没有反击的能力了只能任由敌人宰割!”
“无碍,只要留下些东西,带着一部人离开就是了。”
“啊,特勒奉命来这里整顿蠕蠕诸部,当下诸部刚刚归顺,您就要放弃他们离开,如此有损可汗威名,只怕可汗不会饶恕了您,就算他饶恕了,蠕蠕诸部也不会再信任您,这几年的苦心,可都要白费.”
老者还在苦苦劝说,想要劝说对方主动应战,他甚至说道:“倘若特勒能出兵,我们也愿意出兵,断他们后路,夹攻齐人!!”
摄图站起身来,将一旁的酒器拿起来,一饮而尽,随后便丢弃在了一旁。
他几步走到了老翁的面前,低下头来。
“多谢告知,我定然会如实告知可汗,让他不要忘了盟友的相助。”
他说完,便急匆匆的领着随从离开了此处,只留下了这些周人,茫然的站在了原地。
一个略微年轻些的人骂道:“张公,早知如此,倒不如不来,让他们在这里交战就是了,没想到,这厮这般胆怯.”
那老翁却眯起了双眼,脸色凝重。
“突厥可汗的诸子,有勇无谋,只知道逞凶斗狠,唯独这厮不太一样.若是能拉拢过来,不失为我大周好鹰犬。”
那后生不悦的说道:“如此胆怯,怎做鹰犬?”
“他退却是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足,木杆可汗只给了他两千骑士.麾下的其余从众,皆是刚刚归顺的蠕蠕人,他要领着这些人去跟贺拔呈作战,贺拔呈能打得他全军覆没”
“退了也好,保存些实力,往后或许还能用得上。”
“无论怎么说,反正突厥人已经是被得罪了,与东贼之间,再无缓和的可能,以阿史那燕都的性格,绝对不会善罢甘休,也算是天大好事。”
“速速准备信鸽,我们也得尽快撤离。”
“唯!!”
“杀!!!”
漫山遍野的骑兵发动了冲锋,只是一瞬间,仿佛整个辛山都颤抖了起来。
栅栏倒下,毡房发出哗哗声响。
牧民们惊恐的探出头来,看着远处那如潮水般的大军朝着自己淹来。
他们惊呼着,骑马逃离。
四处传来了哭喊声,怒吼声。
有骑士当即列阵,准备借助栅栏和拒马来进行反击。
下一刻,骑士洪流冲进了牙帐,在最前冲阵的骑士们全副武装,就连他们胯下的骏马,此刻都是披着重重的甲胄,他们几乎如那山峰一般,高大且坚固,牧民们以弓箭反击,那些箭矢三三俩俩的挂在骑士的甲胄上,却完全不能影响对方的速度,当洪流卷进了牙帐的时候,整个牙帐瞬间被摧毁!!!
骑士们犹如黑色的浪花,高高卷起,在一瞬间将牙帐击的粉碎,那些士卒们只是刚刚举起了长矛,下一刻,便被那黑色洪流所淹没,再也发不出声响。
他们从牙帐的左侧一路汹涌而去,摧毁着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,栅栏被撞翻,毡房被撕毁,似是没有什么能挡得住这些骑兵的冲锋,骏马的每一次落蹄,都会发出巨大的声响,当数万骑兵同时冲锋,那声响响彻天际,犹如炸雷,牧民们绝望的开始往后逃离,可片刻之后又被那洪流所吞噬。
刘桃子冲锋在最前,浑身覆盖着重甲,手持马槊,青狮也披上了甲胄,乍一看,就像是一座小山,他甚至都不必挥动武器,只是纵马往前冲锋,一个又一个敌人惨叫着倒下,随即被马蹄所踩碎,变成烂泥。
战鼓阵阵,旌旗随着洪流而前进。
从两侧又冲出了轻骑,手持短弓,开始追杀那些逃离者。
牛羊惊恐的四处乱跑,他们所居住的圈早已被摧毁。
宁静而祥和的牙帐,此刻皆是一股末日的气息。
当刘桃子率领骑士们从牙帐的左侧一路杀到右侧时,他方才勒住了缰绳。
牙帐极大,整个便是一座由无数毡房所形成的城市。
可当刘桃子转过身来的时候,远处却看不到这座城市了。
所有的东西都被推翻,被踩碎,一切都成了烂泥,贴在地面上,甚至看不出半点凸出来的东西,在他们身后,只留下了一处平坦的平原,平原上是木头,人,还有动物的碎片,他们被交织起来,在地面上平坦的铺开,整个牙帐就像是被‘压路机’飞速推过,便是连废墟都不曾留下。
轻骑兵们四处追击,牧民们跳下马,跪在地上请降。
漫山遍野的牛羊骏马四散而逃,轻骑们怪叫着,将这些牲畜们驱赶到一起。
刘桃子皱起眉头,丝毫没有取胜的喜悦。
他们这一战,完全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,甚至都没有看到一个披甲的敌人。
莫非是绕道去攻打自家后路了??
与此同时,在数十里之外,摄图纵马站在高坡上,聆听着远处的动静。
他又嗦了口酒袋,脸色极为平静。
一骑士站在他的身后,看着远处,脸上满是愤怒。
“可惜了我们这两年的心血该死的齐人,今日毁我一牙帐,日后定然以十倍报之!”
摄图嗤笑了一声,“有甚可惜的?”
“当初我就曾告诉叔父,应该将此处的牧民迁徙到北边去.周和齐交战,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?何必急着凑上去呢?”
“离远点,看着他们互相殴打,争着抢着来孝敬我们,请求我们相助我们就看着,若是谁快不行了,就去帮他一把,让他们继续打,这不是很好吗?”
“可我那叔父却不听我的,非要将手伸到这里,让二虎争夺变成了三方对立.只给了我两千人,说是让我防御周,齐.呵,两千人去防御他们双方??”
摄图抿了抿嘴,收住了更加过分的话。
他轻声说道:“我这位叔父,作战虽然勇猛,可根本不在乎局势,刚愎自用,自恃勇武,听不得劝谏.”
“算了,回去吧,趁着周人的使者还没将叔父唬住,得快点过去劝劝他.他本来就想要跟着周人来攻打齐人,这次,只怕是真的要动手了。”
“本可以双吃,他却非要将我们绑到周人的车上.”
年轻的摄图仰起头来,眼神格外的复杂。
“走吧。”
骑士们埋头前进,气氛却格外的压抑。
众人板着脸,不安的看着周围,呼吸声格外的沉重,忧心忡忡。
后头的骑士们驱赶着牛羊以及诸多俘虏,而刘桃子等人走在最前头。
这些人完全没有取胜的欢喜,队伍格外的沉默,只能听到那马蹄声,以及连绵不断的羊叫,更使人心烦意乱。
刘桃子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,贺拔呈死死咬着牙。
众人的不安来自于他们的胜利实在是太快,太容易。
哪怕是过去面对蠕蠕人的时候,他们都不曾如此轻易的取胜,可这一次,他们甚至连敌人都没有碰到,所反抗的都是些会射箭的牧民。
而在他们的认知里,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件事,有诈!!
姚雄看着周围众人,忽开口问道:“会不会是有人通风报信,突厥人害怕便跑了?”
田子礼瞥了他一眼,“你以为突厥人都如你这般?!”
“他们苦心经营了两年,怎么可能说跑就跑?就是要跑,也会带上所有辎重,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多呢?”
姚雄挠了挠头,“打不过还不许人家跑”
“勿要说了,派人再去后头看看吧。”
众人在紧张不安的氛围下继续前进,直到他们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后军,那不安的氛围方才被冲散了不少。
负责留守在后方的乃是白道戍主,被临时任命为军主,这人年纪不小,听闻过去参与过很多的战事,深得士卒们的拥戴。
双方遭遇之后,贺拔呈赶忙跟对方询问了情况。
而他们却并没有遭遇到袭击,无论是突厥人,又或者是伪周,都没有碰到,诡异的宁静。
他们只好按着原先的计划,一路朝着南麓继续前进,不自觉的便加快了速度,甚至都不在意是否会惊动奚人,直接从他们的领地上穿行而过。
他们通过了山口,再次回到了大齐,直到他们看到了远处的武川城池,众人方才反应过来,他们好像真的赢了?!
只是在片刻之内,队伍里的那种压抑氛围消失不见,骑士们纷纷高呼了起来,欢笑声响彻天际。
贺拔呈终于是松了一口气,他看向了一旁的刘桃子,神色相当的困惑。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?莫非是真的跑了??”
刘桃子轻轻点头,“大概如此,明知不敌,便领着精锐撤走,保全实力。”
贺拔呈忍不住感慨道:“这摄图好大的胆魄,两年的心血,说弃就弃.”
众人如此一路回到了武川,很快就得到了留守武川的众人热情的迎接,整个武川内外欢笑声一片,热情犹如火焰一般沸腾。
贺拔呈当即给了士卒们一天时日,让他们用以休息准备。
田子礼等人开始准备清点功勋,分发赏赐。
贺拔呈跟刘桃子等几个将领,此刻正在官署内商谈着接下来的事情。
“此番斩获,最好都赏赐下去。”
刘桃子看向了众人,而诸将则是纷纷看向了贺拔呈。
贺拔呈抿了抿嘴,“还是得拿出点东西给庙堂一个交代,若是都分发了,总不能光将得胜的消息传递回去吧?”
“还是老规矩,旌旗,战鼓,军械,还有那些俘虏,都可以送过去。”
贺拔呈擦了擦额头的细汗,“这次可不同啊,私发兵攻打突厥,若是交代不过去.”
“边镇兵,向来如此。”
刘桃子只一句话,便堵死了贺拔呈,贺拔呈只好点头,反正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,该怎么就怎么样吧,听天由命便是了!
而跟上次不同的是,此番并没有向庙堂分发捷报,只是派书信告知情况。
毕竟,这不是反击盗贼,也并非是奉君令出击,这就是边镇兵按着老习惯外出打了个野味而已。
而接下来,便是分发赏赐的阶段了。
所有随同出兵的诸将士,无论是冲锋的那些人,还是留守黑水的那些人,出征者皆有赏赐,当然,冲锋杀人的赏赐肯定会更高一些。
刘桃子亲自监督,让田子礼向全军分发赏赐,赏赐是直接从校场分发的,以免戍主之类吞掉。
所有出征的将士们,此刻皆是不敢置信,这场仗打得太过轻易,他们就只是赶路,然后一个冲锋,便结束了战役,完全没有遭遇抵抗,便带回来了大量的牲畜,赏赐或许不能让他们就此发家致富,因为出征者众多,故而将战利品分发之后,每个人到手的赏赐并不算太多。
但是,重要的是边镇的改变,自天保六年以来,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塞劫掠,也是第一次取得如此畅快的胜利,一战而定。
刘桃子并没有急着将诸将士们遣散,反而是令人在武川外再设营帐,将这些人都留在了武川。
在分发赏赐,犒赏大军之后,刘桃子便在武川开始了操练。
经过了一次集合出兵,这些来自诸镇诸戍的将士们终于有了些默契,虽然不多,刘桃子要做的,就是尽快让他们能变成一个整体。
大获全胜,领取了赏赐的将士们士气极高。
面对接下来这高强度的操练,也没有什么怨言,只是这军饷方面,却是依旧紧缺,只能盼着庙堂快些运粮。
晋阳。
大丞相府。
陆杳脸色苍白,手持文书,快步走到了书房前,通过窗户上的黑影,能看到高演正坐在里头。
陆杳看了看手里的文书,眼里是说不出的悲切,他深吸了一口气,方才行礼呼喊道:“陆杳拜见大丞相!!”
“进来吧。”
陆杳这才推门而入。
就看到高演坐在案前,手里拿着一份文书,满脸的迟疑不决,看到陆杳,他示意对方坐下来。
刚拿起手里的文书,他便看到陆杳手里也拿着一份。
高演问道:“出了什么事?”
陆杳缓缓将文书递给了高演,“大丞相是镇将军贺拔呈,他领着诸边兵出塞,摧毁了突厥人的南特勒牙帐,阿史那摄图领兵逃走,牙帐被毁,抄掠牛羊骏马十万余头”
高演的眉头跳了跳,拿起了文书,仔细翻看了起来。
看着高演那凝重的脸色,陆杳满头大汗,低着头,一言不发。
“贺拔呈没这胆量是刘桃子干的。”
高演忽开口说道,陆杳吓得赶忙跪倒,“大丞相”
“陆公,我又不曾问罪,何必如此?起来,且起来吧。”
高演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,将陆杳扶起来,让他坐在自己身边,以示亲近。
“镇兵外出抄掠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至于突厥人反复无常,得罪便得罪了吧,与他们交战也只是早晚的事情。”
高演仰起头来,眼里没有丝毫的惧怕。
“当初我兄长还在的时候,这些人击破蠕蠕,骄横得意,竟意图来犯,兄长出兵讨伐,在边镇打得他们溃不成军,四散而逃,从此不敢南望。”
“当下兄长不在了他们早晚会来试探,如此出击,他们倒是不敢轻易来犯了。”
陆杳赶忙点着头,“正是如此,那突厥可汗,看似鲁莽,实则狡诈,被文宣皇帝击破之后,便开始主动与伪周亲近,更是拟定婚约,以此互保此人派人靠近边镇,已有两年,所派的军队又不多,便是在试探大齐之虚实,当下主动出击,让他们知道文宣皇帝虽然不在,可他麾下的精锐依旧凶悍,想必也不是坏事.”
高演深深看了眼陆杳,又说道:“这件事不必告知群臣,倒是还有一件事,需要陆公来帮我出个主意。”
“大丞相请言之。”
“我想派遣使者前往玉壁,要求两国停战,恢复往来,互通贸易,你以为如何?”
陆杳大吃一惊,“大丞相,您这是??”
“当下我们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做,而伪周同样如此,我看,倒不如给双方时日,先将里头的事情办妥当,再跟他们决一胜负。”
陆杳抿了抿嘴,“大丞相言之有理。”
“那若是让刘桃子担任使者,前往玉璧,你以为如何?”
“啊?!!”
“万万不可啊!!丞相!!!”
ps:保定初,以孝宽立勋玉壁,置勋州,仍授勋州刺史。齐人遣使至玉壁,求通互市。———《北史·列传第五十二》
沙钵略(摄图)勇而得众,北夷皆归附之。沙钵略妻,宇文氏之女,曰千金公主,自伤宗祀绝灭,每怀复隋之志,日夜言之于沙钵略。——《隋书·列传第四十九》
老者大惊失色。
摄图平静的看了他一眼,“我打不过。”
老者赶忙说道:“特勒岂能不战而退呢?都不曾交战,怎么就知打不过?我当特勒是天下闻名的勇士,各部敬畏,不知竟是如此怯弱,只听闻敌人出兵,就想要逃离,可悲,可叹,想那伊利可汗何等的英雄,竟有这般的儿子!”
“老夫当真是看错了人.齐人孱弱,特勒竟还不如这些齐人!!”
听到对方的话,摄图笑了起来,“既是这般孱弱,你们怎么不打?”
老者一顿。
“想那当初的宇文可汗是何等的英雄,怎么他会有这样的部下?看着齐人从身边经过,却不敢发兵,莫不是想要借他们之手来收拾自家盟友?”
老者赶忙摇头,“特勒,岂敢,岂敢.”
他急忙改变了口吻,“您如今要是撤离,您这部下极多,只怕是没走出多久,就会被齐人追上,到时候,您就再也没有反击的能力了只能任由敌人宰割!”
“无碍,只要留下些东西,带着一部人离开就是了。”
“啊,特勒奉命来这里整顿蠕蠕诸部,当下诸部刚刚归顺,您就要放弃他们离开,如此有损可汗威名,只怕可汗不会饶恕了您,就算他饶恕了,蠕蠕诸部也不会再信任您,这几年的苦心,可都要白费.”
老者还在苦苦劝说,想要劝说对方主动应战,他甚至说道:“倘若特勒能出兵,我们也愿意出兵,断他们后路,夹攻齐人!!”
摄图站起身来,将一旁的酒器拿起来,一饮而尽,随后便丢弃在了一旁。
他几步走到了老翁的面前,低下头来。
“多谢告知,我定然会如实告知可汗,让他不要忘了盟友的相助。”
他说完,便急匆匆的领着随从离开了此处,只留下了这些周人,茫然的站在了原地。
一个略微年轻些的人骂道:“张公,早知如此,倒不如不来,让他们在这里交战就是了,没想到,这厮这般胆怯.”
那老翁却眯起了双眼,脸色凝重。
“突厥可汗的诸子,有勇无谋,只知道逞凶斗狠,唯独这厮不太一样.若是能拉拢过来,不失为我大周好鹰犬。”
那后生不悦的说道:“如此胆怯,怎做鹰犬?”
“他退却是因为知道自己实力不足,木杆可汗只给了他两千骑士.麾下的其余从众,皆是刚刚归顺的蠕蠕人,他要领着这些人去跟贺拔呈作战,贺拔呈能打得他全军覆没”
“退了也好,保存些实力,往后或许还能用得上。”
“无论怎么说,反正突厥人已经是被得罪了,与东贼之间,再无缓和的可能,以阿史那燕都的性格,绝对不会善罢甘休,也算是天大好事。”
“速速准备信鸽,我们也得尽快撤离。”
“唯!!”
“杀!!!”
漫山遍野的骑兵发动了冲锋,只是一瞬间,仿佛整个辛山都颤抖了起来。
栅栏倒下,毡房发出哗哗声响。
牧民们惊恐的探出头来,看着远处那如潮水般的大军朝着自己淹来。
他们惊呼着,骑马逃离。
四处传来了哭喊声,怒吼声。
有骑士当即列阵,准备借助栅栏和拒马来进行反击。
下一刻,骑士洪流冲进了牙帐,在最前冲阵的骑士们全副武装,就连他们胯下的骏马,此刻都是披着重重的甲胄,他们几乎如那山峰一般,高大且坚固,牧民们以弓箭反击,那些箭矢三三俩俩的挂在骑士的甲胄上,却完全不能影响对方的速度,当洪流卷进了牙帐的时候,整个牙帐瞬间被摧毁!!!
骑士们犹如黑色的浪花,高高卷起,在一瞬间将牙帐击的粉碎,那些士卒们只是刚刚举起了长矛,下一刻,便被那黑色洪流所淹没,再也发不出声响。
他们从牙帐的左侧一路汹涌而去,摧毁着阻挡在他们面前的一切,栅栏被撞翻,毡房被撕毁,似是没有什么能挡得住这些骑兵的冲锋,骏马的每一次落蹄,都会发出巨大的声响,当数万骑兵同时冲锋,那声响响彻天际,犹如炸雷,牧民们绝望的开始往后逃离,可片刻之后又被那洪流所吞噬。
刘桃子冲锋在最前,浑身覆盖着重甲,手持马槊,青狮也披上了甲胄,乍一看,就像是一座小山,他甚至都不必挥动武器,只是纵马往前冲锋,一个又一个敌人惨叫着倒下,随即被马蹄所踩碎,变成烂泥。
战鼓阵阵,旌旗随着洪流而前进。
从两侧又冲出了轻骑,手持短弓,开始追杀那些逃离者。
牛羊惊恐的四处乱跑,他们所居住的圈早已被摧毁。
宁静而祥和的牙帐,此刻皆是一股末日的气息。
当刘桃子率领骑士们从牙帐的左侧一路杀到右侧时,他方才勒住了缰绳。
牙帐极大,整个便是一座由无数毡房所形成的城市。
可当刘桃子转过身来的时候,远处却看不到这座城市了。
所有的东西都被推翻,被踩碎,一切都成了烂泥,贴在地面上,甚至看不出半点凸出来的东西,在他们身后,只留下了一处平坦的平原,平原上是木头,人,还有动物的碎片,他们被交织起来,在地面上平坦的铺开,整个牙帐就像是被‘压路机’飞速推过,便是连废墟都不曾留下。
轻骑兵们四处追击,牧民们跳下马,跪在地上请降。
漫山遍野的牛羊骏马四散而逃,轻骑们怪叫着,将这些牲畜们驱赶到一起。
刘桃子皱起眉头,丝毫没有取胜的喜悦。
他们这一战,完全没有遭遇任何的抵抗,甚至都没有看到一个披甲的敌人。
莫非是绕道去攻打自家后路了??
与此同时,在数十里之外,摄图纵马站在高坡上,聆听着远处的动静。
他又嗦了口酒袋,脸色极为平静。
一骑士站在他的身后,看着远处,脸上满是愤怒。
“可惜了我们这两年的心血该死的齐人,今日毁我一牙帐,日后定然以十倍报之!”
摄图嗤笑了一声,“有甚可惜的?”
“当初我就曾告诉叔父,应该将此处的牧民迁徙到北边去.周和齐交战,对我们不是很有利吗?何必急着凑上去呢?”
“离远点,看着他们互相殴打,争着抢着来孝敬我们,请求我们相助我们就看着,若是谁快不行了,就去帮他一把,让他们继续打,这不是很好吗?”
“可我那叔父却不听我的,非要将手伸到这里,让二虎争夺变成了三方对立.只给了我两千人,说是让我防御周,齐.呵,两千人去防御他们双方??”
摄图抿了抿嘴,收住了更加过分的话。
他轻声说道:“我这位叔父,作战虽然勇猛,可根本不在乎局势,刚愎自用,自恃勇武,听不得劝谏.”
“算了,回去吧,趁着周人的使者还没将叔父唬住,得快点过去劝劝他.他本来就想要跟着周人来攻打齐人,这次,只怕是真的要动手了。”
“本可以双吃,他却非要将我们绑到周人的车上.”
年轻的摄图仰起头来,眼神格外的复杂。
“走吧。”
骑士们埋头前进,气氛却格外的压抑。
众人板着脸,不安的看着周围,呼吸声格外的沉重,忧心忡忡。
后头的骑士们驱赶着牛羊以及诸多俘虏,而刘桃子等人走在最前头。
这些人完全没有取胜的欢喜,队伍格外的沉默,只能听到那马蹄声,以及连绵不断的羊叫,更使人心烦意乱。
刘桃子等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,贺拔呈死死咬着牙。
众人的不安来自于他们的胜利实在是太快,太容易。
哪怕是过去面对蠕蠕人的时候,他们都不曾如此轻易的取胜,可这一次,他们甚至连敌人都没有碰到,所反抗的都是些会射箭的牧民。
而在他们的认知里,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一件事,有诈!!
姚雄看着周围众人,忽开口问道:“会不会是有人通风报信,突厥人害怕便跑了?”
田子礼瞥了他一眼,“你以为突厥人都如你这般?!”
“他们苦心经营了两年,怎么可能说跑就跑?就是要跑,也会带上所有辎重,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多呢?”
姚雄挠了挠头,“打不过还不许人家跑”
“勿要说了,派人再去后头看看吧。”
众人在紧张不安的氛围下继续前进,直到他们遇到了前来接应的后军,那不安的氛围方才被冲散了不少。
负责留守在后方的乃是白道戍主,被临时任命为军主,这人年纪不小,听闻过去参与过很多的战事,深得士卒们的拥戴。
双方遭遇之后,贺拔呈赶忙跟对方询问了情况。
而他们却并没有遭遇到袭击,无论是突厥人,又或者是伪周,都没有碰到,诡异的宁静。
他们只好按着原先的计划,一路朝着南麓继续前进,不自觉的便加快了速度,甚至都不在意是否会惊动奚人,直接从他们的领地上穿行而过。
他们通过了山口,再次回到了大齐,直到他们看到了远处的武川城池,众人方才反应过来,他们好像真的赢了?!
只是在片刻之内,队伍里的那种压抑氛围消失不见,骑士们纷纷高呼了起来,欢笑声响彻天际。
贺拔呈终于是松了一口气,他看向了一旁的刘桃子,神色相当的困惑。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?莫非是真的跑了??”
刘桃子轻轻点头,“大概如此,明知不敌,便领着精锐撤走,保全实力。”
贺拔呈忍不住感慨道:“这摄图好大的胆魄,两年的心血,说弃就弃.”
众人如此一路回到了武川,很快就得到了留守武川的众人热情的迎接,整个武川内外欢笑声一片,热情犹如火焰一般沸腾。
贺拔呈当即给了士卒们一天时日,让他们用以休息准备。
田子礼等人开始准备清点功勋,分发赏赐。
贺拔呈跟刘桃子等几个将领,此刻正在官署内商谈着接下来的事情。
“此番斩获,最好都赏赐下去。”
刘桃子看向了众人,而诸将则是纷纷看向了贺拔呈。
贺拔呈抿了抿嘴,“还是得拿出点东西给庙堂一个交代,若是都分发了,总不能光将得胜的消息传递回去吧?”
“还是老规矩,旌旗,战鼓,军械,还有那些俘虏,都可以送过去。”
贺拔呈擦了擦额头的细汗,“这次可不同啊,私发兵攻打突厥,若是交代不过去.”
“边镇兵,向来如此。”
刘桃子只一句话,便堵死了贺拔呈,贺拔呈只好点头,反正都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,该怎么就怎么样吧,听天由命便是了!
而跟上次不同的是,此番并没有向庙堂分发捷报,只是派书信告知情况。
毕竟,这不是反击盗贼,也并非是奉君令出击,这就是边镇兵按着老习惯外出打了个野味而已。
而接下来,便是分发赏赐的阶段了。
所有随同出兵的诸将士,无论是冲锋的那些人,还是留守黑水的那些人,出征者皆有赏赐,当然,冲锋杀人的赏赐肯定会更高一些。
刘桃子亲自监督,让田子礼向全军分发赏赐,赏赐是直接从校场分发的,以免戍主之类吞掉。
所有出征的将士们,此刻皆是不敢置信,这场仗打得太过轻易,他们就只是赶路,然后一个冲锋,便结束了战役,完全没有遭遇抵抗,便带回来了大量的牲畜,赏赐或许不能让他们就此发家致富,因为出征者众多,故而将战利品分发之后,每个人到手的赏赐并不算太多。
但是,重要的是边镇的改变,自天保六年以来,这是他们第一次出塞劫掠,也是第一次取得如此畅快的胜利,一战而定。
刘桃子并没有急着将诸将士们遣散,反而是令人在武川外再设营帐,将这些人都留在了武川。
在分发赏赐,犒赏大军之后,刘桃子便在武川开始了操练。
经过了一次集合出兵,这些来自诸镇诸戍的将士们终于有了些默契,虽然不多,刘桃子要做的,就是尽快让他们能变成一个整体。
大获全胜,领取了赏赐的将士们士气极高。
面对接下来这高强度的操练,也没有什么怨言,只是这军饷方面,却是依旧紧缺,只能盼着庙堂快些运粮。
晋阳。
大丞相府。
陆杳脸色苍白,手持文书,快步走到了书房前,通过窗户上的黑影,能看到高演正坐在里头。
陆杳看了看手里的文书,眼里是说不出的悲切,他深吸了一口气,方才行礼呼喊道:“陆杳拜见大丞相!!”
“进来吧。”
陆杳这才推门而入。
就看到高演坐在案前,手里拿着一份文书,满脸的迟疑不决,看到陆杳,他示意对方坐下来。
刚拿起手里的文书,他便看到陆杳手里也拿着一份。
高演问道:“出了什么事?”
陆杳缓缓将文书递给了高演,“大丞相是镇将军贺拔呈,他领着诸边兵出塞,摧毁了突厥人的南特勒牙帐,阿史那摄图领兵逃走,牙帐被毁,抄掠牛羊骏马十万余头”
高演的眉头跳了跳,拿起了文书,仔细翻看了起来。
看着高演那凝重的脸色,陆杳满头大汗,低着头,一言不发。
“贺拔呈没这胆量是刘桃子干的。”
高演忽开口说道,陆杳吓得赶忙跪倒,“大丞相”
“陆公,我又不曾问罪,何必如此?起来,且起来吧。”
高演强行挤出了一丝笑容,将陆杳扶起来,让他坐在自己身边,以示亲近。
“镇兵外出抄掠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,至于突厥人反复无常,得罪便得罪了吧,与他们交战也只是早晚的事情。”
高演仰起头来,眼里没有丝毫的惧怕。
“当初我兄长还在的时候,这些人击破蠕蠕,骄横得意,竟意图来犯,兄长出兵讨伐,在边镇打得他们溃不成军,四散而逃,从此不敢南望。”
“当下兄长不在了他们早晚会来试探,如此出击,他们倒是不敢轻易来犯了。”
陆杳赶忙点着头,“正是如此,那突厥可汗,看似鲁莽,实则狡诈,被文宣皇帝击破之后,便开始主动与伪周亲近,更是拟定婚约,以此互保此人派人靠近边镇,已有两年,所派的军队又不多,便是在试探大齐之虚实,当下主动出击,让他们知道文宣皇帝虽然不在,可他麾下的精锐依旧凶悍,想必也不是坏事.”
高演深深看了眼陆杳,又说道:“这件事不必告知群臣,倒是还有一件事,需要陆公来帮我出个主意。”
“大丞相请言之。”
“我想派遣使者前往玉壁,要求两国停战,恢复往来,互通贸易,你以为如何?”
陆杳大吃一惊,“大丞相,您这是??”
“当下我们内部有很多事情要做,而伪周同样如此,我看,倒不如给双方时日,先将里头的事情办妥当,再跟他们决一胜负。”
陆杳抿了抿嘴,“大丞相言之有理。”
“那若是让刘桃子担任使者,前往玉璧,你以为如何?”
“啊?!!”
“万万不可啊!!丞相!!!”
ps:保定初,以孝宽立勋玉壁,置勋州,仍授勋州刺史。齐人遣使至玉壁,求通互市。———《北史·列传第五十二》
沙钵略(摄图)勇而得众,北夷皆归附之。沙钵略妻,宇文氏之女,曰千金公主,自伤宗祀绝灭,每怀复隋之志,日夜言之于沙钵略。——《隋书·列传第四十九》